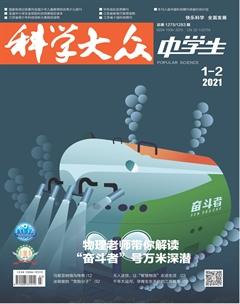暈車、暈船、暈機……為什么只有你這樣
海倫湯姆森



初中課本告訴我們,暈車與前庭和半規管有關。兩者都位于內耳,是感受頭部位置變動的位覺感受器,如果過度敏感,其主人可能就要承受暈車、暈船之苦。但這類極簡的介紹顯然欠缺深度,它能出現于中學課本也并非因為其原理早已被揭示,恰恰相反,暈車的生物學機制一直困擾著科學界。
科學界將暈車、暈船以及暈機等癥狀統稱為暈動癥。所謂的“暈”,指的是惡心想吐的感覺。交通工具的搖擺、顛簸、旋轉和加速運動都可能引起暈動癥,不過每個人的暈動閾值各有差異,有的人坐小轎車都暈,而有的人哪怕坐過山車都沒啥感覺。通常來說,坐船最容易使人產生暈動癥,浪大時,船上可能有1/3的人會拿出塑料袋嘔吐。
法國一家公司最新研發了一種防暈眼鏡,這款眼鏡有4個環:兩個框住眼睛,另外兩個分列頭部兩側,均填充有一半的液體,其流動方式與半規管內的液體相同。研發人員表示:戴上它,就好像將內耳的前庭系統復制入了你的視覺系統,有助于減少感覺沖突
前庭里的“坐標系”
除了人類,貓、狗,甚至各種鳥類和魚類都可能有暈動癥。事實上,只有不具備前庭系統的生物才能保證不暈。
內耳中的前庭系統主管頭部平衡運動,主要由橢圓囊、球囊和3個半圓形的半規管組成——其中,前半規管與后半規管間成直角,二者又與水平半規管互成直角,它們內部均飽含流體。
如果系統發生了朝任一方向的旋轉運動,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動作,這個“坐標系”內的流體即會發生位置改變,接著前庭系統會將此信息發送至兩個大腦區域——小腦和腦干。前者主管平衡和運動,后者負責將大腦與其他區域(包括引發惡心和嘔吐的區域)聯系起來。
此外,前庭系統還會把變化信號傳輸給眼睛,這幫助我們在移動頭部的過程中視野清晰。
關于暈動癥的因由,最老派的說法是前庭系統受到的刺激超出了可承受范圍。但如果此說法成立,為什么暈船的乘客返回陸地后仍會持續一段時間的惡心感?為什么很多動作夸張的勁爆運動(例如街舞)不會引起暈動癥?為什么同一個人在坐車和駕車時感受到的惡心程度相差懸殊?
鑒于此,有人提出了一個不那么老派的觀點——不同類型的感官信息間的沖突引發了暈動癥。
舉個例子,如果你坐車時看手機,手機屏幕會“告訴”你的大腦,你處于靜止狀態,但汽車的顛簸和轉彎會“告訴”你的前庭系統,你正在運動。視覺和位覺的沖突使大腦很難產生連貫的平衡感,惡心想吐的沖動由此產生。
然而,這種“感覺;中突”的說法也有問題。再舉個例子,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水手和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水手一同登上遠行輪船的甲板,他們收到的感覺信號一致,但經驗告訴我們,老水手的惡心感會更輕,因為他習慣了這些。換句話,人體可以通過訓練減輕暈動癥,但這顯然與感覺;中突理論相矛盾。
大腦的期待與實際的運動沖突
第三種說法出現了:眼睛和內耳間信號沖突不是根源,它們與大腦期望間的沖突才是。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者查爾斯-歐曼是該理論的支持者。他于1990年這樣闡釋自己的觀點:人體運動時,大腦會從預期的神經活動模式中減去實際的感覺輸入,剩下的就是“感覺運動;中突信號”。通常,這個剩余值很小。也就是說,大腦的預期和實際的感覺基本一致。但假如遭遇意外情況,例如你原本好好地在船上看書,可船只突然開始猛烈晃動,那此時你大腦的運動系統會做出糾正反應。如果你重新平衡了自己,沖突消失,就不會有什么問題;但如果沖突信號長時間持續,暈動癥就可能因此被觸發。
該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么人們不暈街舞卻暈船,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不暈船的水手卻可能暈車,更可以解釋為什么坐車的會暈而開車的卻不暈,根源就在于感官期望與實際環境的差距。
當你跳舞或開車時,你的大腦預期的就是這些運動,而你的實際感受也是如此,兩者基本一致,所以不會產生暈動癥。當老水手在漫長的航行途中習慣了船只的顛簸,他的大腦預期實際上就已經匹配了實際的晃動。但如果把他放到車上,感覺運動沖突信號就會很強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托馬斯-斯托弗里根在歐曼觀點的基礎上,提供了另一個思路:無法控制身體姿態是感覺運動沖突信號產生的直接原因。換言之,如果我們在坐船時能準確施展一套“平衡動作”,暈動癥即可被緩解甚至消除。他和同事也確實通過研究發現,乘船者是可以通過一些微妙動作維持身體平衡,進而減弱感覺運動;中突信號的。
此外,他還提出了一種解決暈車的簡單方法:這些動作的核心就是盡可能地增加自身寬度,就好比雜技演員手持長桿走鋼絲,寬度越大,穩定性越強,惡心感也就越小了。
歐曼等研究者的理論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但科學家更關心另一個問題——能夠支持該理論的神經元證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科學家都無法從腦科學層面解析暈動癥,直到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凱瑟琳-卡倫無意間的一個發現。她的團隊曾訓練猴子以特定方式移動進而獲得治療,有時,他們會破壞其運動,例如將重物放在猴子頭頂,使它們的大腦預期與實際頭部運動不符。出現這種情況時,猴子小腦中某些神經元的活動就會激增——常態下的它們并不活躍;而當猴子適應了這類別扭的運動后,神經元活動也會減弱。
歐曼給予了卡倫極高的評價:“當我看到她的成果時,我感到震驚。這些神經元是揭示暈動癥生物機制的關鍵。”不過他同時也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小腦區域通過神經元傳遞信號至腦干區域,從而引發惡心感,這些負責傳遞的神經元會不會就是卡倫等人觀察到變化的神經元呢?
這個問題留待后續研究解答。
暈動癥的性別差異
關于暈動癥,還有另一個關注度很高的問題:它為什么存在群體差異?例如,女性更容易暈船或暈車。
牛津大學學者米歇爾·特里斯曼曾這樣說道:“暈動癥帶給人體極大的傷害,如果它對我們沒有任何生存意義,那么,自然選擇應該早就消除了這個缺陷。”
在他看來,暈動癥是人類對毒物強烈反應的副作用:
人體需要一個探測有無毒素侵入的預警系統,而毒素往往會給人體帶來不平衡感。因此,主管平衡的位覺系統很可能會通過覺察不平衡感來判斷人體內是否出現毒素,然后將信息匯報給大腦。不幸的是,不平衡感不只由毒物帶來,任何能使我們失去平衡的事件都可觸發暈動癥。
從生存意義來看,女性的暈動癥閾值更低自有其道理:孕婦對毒素的高度敏感有助于保護胎兒,提高其存活率。
也有科學家提出了另一種解答:“男人和女人的體重分布不同。與身高相仿的男性相比,女性的臀部更輕,腳更小。此類差異的結果可能是女性的身體更不穩定,在進入無法匹配大腦預期的運動狀態時更難保持平衡。”
一些研究隊伍希望精確鎖定暈動癥相關基因。2015年,位于美國加州的一家遺傳分析公司面向約8萬人開展了全球首個全基因組暈動癥研究,最終找到35種相關DNA,包括與眼睛、耳朵的發育以及葡萄糖調節相關的基因。他們發現,擁有這些特定基因的女性受暈動癥困擾的比例是男性的3倍。
不過,目前科學家尚不清楚它們具體是怎樣影響暈動癥的。
文章來源:“世界科學”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