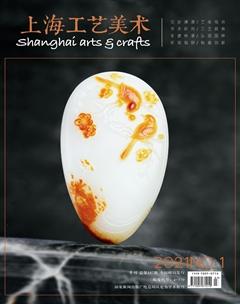蓮池鴛鴦紋與“滿池嬌”
王博宣

The lotus pond scenery, represented by Pattern of Mandarin Duck in Lotus Pond, is a commonly-seen decorative pattern on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of the Yuan Dynasty. It appears frequently and spreads in many places. In Ardebil Shrine in Iran and the Topkapi Sarayi Museum in Turkey, which are two important collectors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of the Yuan Dynasty, pattern of lotus pond can be found on all kinds of bowls, plates, vases and pots. In addition to Jingdezhen, Xinjiang and Gansu in China,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with pattern of lotus pond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Mongolia, India, Egypt,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以蓮池鴛鴦紋為代表的蓮池小景是元青花上常見的裝飾紋樣,出現頻率高,散布區域廣闊。在伊朗阿特比爾清真寺與土耳其托甫卡普·沙奈博物館這兩處重要的元青花收藏地中,蓮池紋可見于各式碗盤、瓶罐。此外,除我國景德鎮、新疆、甘肅,裝飾蓮池紋的青花器還被發現于蒙古、印度、埃及、菲律賓等地。
一、元青花蓮池鴛鴦紋的時代特征
蓮池與鴛鴦均是我國工藝美術中常用的裝飾題材,唐宋以降尤為盛行,而元青花上的蓮池鴛鴦紋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
首先,唐及北宋時的紋飾突出鴛鴦,而元代則呈現出蓮花與禽鳥并重的風貌。出土于何家村唐代窖藏的線刻鴛鴦紋銀盒,盒面上刻一對足踏蓮蓬的鴛鴦;鎏金鴛鴦紋銀盒,中心為一只振翅鴛鴦,四周環繞蓮瓣花結。在此二器中,蓮荷作為局部妝點出現。其次,唐宋時蓮花與鴛鴦的組合較為自由,而元代的蓮塘鴛鴦紋已經形成模式。元青花上的蓮池小景,作為中心的花葉將畫面分隔為對稱的二或四部分,鴛鴦棲身其間,構圖嚴謹,畫面均衡。這樣的蓮池小景圖案為元代獨有,成為元青花顯著的時代標記。
二、元青花蓮池鴛鴦紋的直接來源
劉新園提出的“元青花中大量出現的蓮池鴛鴦紋來源于元代織繡”是目前關于其來源問題的重要觀點之一。
矢部良明曾根據日本知恩院藏的一幅宋代蓮池水禽圖提出“元青花紋飾與南宋江南民間繪畫之間存在影響關系”。然而對比知恩院藏蓮池水禽圖與元青花蓮池鴛鴦紋,二者的直接相似之處并不明顯。或許蓮池小景紋樣在它的長期蓄積過程中從類似題材的江南民間繪畫中吸收了營養,但不能據此將之作為元青花蓮池鴛鴦紋的直接來源。
從形式上比較,有與元青花蓮池鴛鴦紋更加接近的實物存在。出土于集寧路總管府達魯花赤窖藏的一件刺繡素羅夾衫被認為與元青花蓮池鴛鴦紋有著莫大的聯系。劉新園認為:“其兩肩的蓮荷紋與胸前的鴛鴦與瓷器上的青花紋飾十分神似。不僅變形與夸張的手法相同,就連花葉的數量、構圖與留白都十分相似。”元代刺繡與青花紋飾的親緣關系,當是可以肯定的。
文宗朝奎章閣大學士柯九思宮詞將元青花池塘小景紋飾進一步與元文宗的御衣聯系起來:“觀蓮太液汛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繡作滿池嬌。”
其下自注:“天歷間,御衣多為池塘小景,名曰‘滿池嬌”。
集寧路繡羅夾衫花紋繁滿,不乏白鶴、鷺鷥等高級紋樣,很有可能就屬于達魯花赤本人。集寧路達魯花赤官秩為從三品,由蒙古人擔任,其輿服規格已接近帝王。既然這件夾衫紋樣與瓷器紋飾高度相似,那么文宗御衣上的花紋與瓷器紋飾相似也就不難理解了。
元青花上蓮池小景紋樣與高規格服飾紋樣的聯系還有一重佐證:只有景德鎮的青花瓷器上出現了刺繡紋樣的裝飾。景德鎮曾設有浮梁瓷局,至少直到元政府徹底失去對景德鎮地區的控制以前,當地瓷窯仍然承擔著對朝廷的瓷器需求“有命則供”的義務。元代官作坊產品的用料、造型、圖案、顏色等都有嚴格的限定,由此,景德鎮才能得到將作院的“樣制”。元代官造手工藝制品的設計由同屬將作院金玉府的畫局負責,極其相似的瓷器裝飾紋樣與刺繡紋樣很可能都產生于此。
至于青花紋飾與刺繡紋樣的相互影響關系,需要比較二者的出現時間。劉新園引明代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書》中列舉的明代御器廠瓷器紋飾名目,認為瓷器與文宗御衣刺繡紋樣同名“滿池嬌”,且出現大量蓮池小景的伊朗與土耳其藏青花瓷是文宗朝對伊兒汗國的賜賚瓷,則青花受刺繡影響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江西大志·陶書》的記載直接說明的是明代的瓷器紋樣,雖然能夠推測明代瓷器名目因襲自元代,但元代蓮池鴛鴦紋得名“滿池嬌”的具體時間仍不能確定。且“滿池嬌”的名稱在南宋已經出現。另外,馬文寬曾根據元廷與伊兒汗國之間使節來往的記錄與《島夷志略》中對太平洋、印度洋貿易地點和主要貨物的記載,推定海外這批青花瓷應當生產于元泰定年間。這樣,御衣紋樣與青花紋樣之間的直接影響關系就未可輕言斷定了。
三、蓮池鴛鴦紋的源流
元代的蓮池鴛鴦紋作為一種成熟的高水平紋樣不可能一夕之間突然出現。即便是由畫局的畫家們統一設計,它的問世必然也經歷了社會審美與藝術表現手法的長時間積累。
以蓮荷與禽鳥為主要構成元素的池塘小景自唐代起即成為花鳥畫和多種工藝美術門類中的常見題材,在宋代花鳥畫名家名作輩出的背景下,蓮池小景題材也大為普及。兩宋的絲綢、漆器、瓷器等手工藝紛紛采用此類圖樣。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給皂地金線盤花鴛鴦”;遼寧省博物館藏北宋紫地鸞鵲譜緙絲,織有鸞鵲、鴛鴦、荷花、鸂鶒、牡丹等圖案;另有宋代緙絲名家朱克柔的作品《蓮塘乳鴨圖》。瓷器中此類例子亦不少,如宋當陽峪窯白釉黑彩瓷枕、定窯白釉蓮池蕩舟盤、金定窯綠釉雕花蓮鴨紋枕。瓷器之外還有漆器,江蘇武進南宋墓出土的戧金黑漆盒上有一幅蓮池小景圖案。
這一時期的蓮池小景紋樣與元青花上者還有一定差異,但場景與構成要素已經初具雛形。以蓮花、鴛鴦,鸂鶒作為基本構成元素的池塘小景形成一種具有特定內涵與專名的裝飾紋樣——滿池嬌。在宋元畫風漸變的背景下,蓮池小景紋樣也由寫實轉向寫意。南宋末年的《蓮池水禽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與集寧路繡花夾衫之間的相似度已經相當高。
元青花上的蓮池小景與文宗御衣上的滿池嬌圖樣同出將作院畫局,而從池塘小景紋樣發展演變的過程來看,不論元青花中滿池嬌與御衣紋樣的先后關系如何,二者擁有共同的源頭。
四、蓮池鴛鴦紋的文化內涵
除了美好的形式、雅致恬然的氣質、對情感的寄托和對太平繁榮生活的象征外,蓮池鴛鴦紋還有著佛教內涵。
有論者指出,蓮池與鴛鴦都屬于佛教意象。蓮花被佛教視為清澄界域的標識,與凈土信仰中“蓮池化生”的內容都已為人所共知,鴛鴦對“佛、法不相離”的象征意義在《大般涅槃經》《佛說德光太子經》《大莊嚴論經》中都有提及。鴛鴦在我國古代有過三重象征意義:兄弟之誼;堅貞愛情的象征;西方凈土中喧唱佛法的靈鳥。南北朝佛教藝術傳入中國后,常常應用鴛鴦紋。隋唐時期,鴛鴦紋大量出現,如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鎏金鴛鴦團花紋銀盆、浙江杭州雷峰塔五代時期地宮出土蓮荷鴛鴦鴻雁紋銀墊等。宋遼時期鴛鴦紋的表現形式趨于多樣化,風格更加自由活潑,但仍能看出佛教痕跡,例如遼代“文忠王府大殿”供養祭器。這一時期世俗用品中的鴛鴦紋也有了更多運用,像宋定窯蓮荷鴛鴦紋碗,宋金蓮池鴛鴦紋有柄銅鏡、宋金各式蓮池鴛鴦紋瓷器等。“蓮”與“鴛鴦”結合的形式,既是自然生態的反映,也能看出佛教的影響。元代高僧梵琦的詩文中不乏詠鴛鴦的作品。像“款款好風搖菡萏,依依流水帶鴛鴦”、“風滿瑤臺水滿池,華開菡萏一枝枝。細聽鳧雁鴛鴦語,正是身心解脫時”等,無不說明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中,鴛鴦作為佛教意象是被廣泛認可的。
張昱的宮詞中也能透露一些這樣的線索:“鴛鴦鸂鶒滿池嬌,彩繡金茸日幾條。早晚君王天壽節,要將著御太明朝。”
佛教傳入以來,帝王誕日的儀軌往往受其濡染。魏太武帝誕生之節、唐玄宗天長節、后梁太祖大明節、后周太祖圣節、宋太祖長春節,均有道場、講經、散齋、護生之類慶祝活動。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又篤信佛教的元文宗,在誕日朝會這樣重要的儀軌上所穿的服裝具有佛教意義,顯然比只有藝術效果更具有合理性。
同理,把蓮紋與蓮池紋有“蓮池化生”的意義,蓮池白鷺紋象征佛教“白鷺池”,蓮池魚藻紋則與佛教雙魚紋有關。當然工匠們對這類紋飾的應用只需要有“雖不中不遠矣”的效果,紋樣在創作時也會糅合進畫家的個人理解,蓮池小景仍然是有著相似內涵的一組紋飾,其中以蓮池鴛鴦最為普遍。
在唐宋至元佛教盛行、元代凈土信仰回歸的社會背景下,這種解讀是可行的,但蓮池鴛鴦紋對于愛情的寄托和太平盛世的祈愿仍然不容忽視,畢竟它的表現形式也是脫胎于世俗藝術的。《古今注·鳥獸》云:“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死,故曰匹鳥。”孟郊有句:“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可見鴛鴦作為愛情的象征和佛教意象是自佛教傳入起便并行的。元代張翥《江神子·枕頂》中的描寫更加富于生活美感:“合歡花樣滿池嬌,用心描。數鍼挑。面面芙菜,閑葉映蘭苕。刺到鴛鴦雙比翼,應想像,為魂銷。巧盤金縷綴倡條,隱紅綃。翠妖嬈。白玉函邊,幾度墜鸞翹。汗粉啼紅容易涴,須愛惜,可憐宵。”
有著世俗與宗教的雙重寄寓,或許這也是以蓮池鴛鴦紋為代表的蓮池小景紋飾擁有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五、“滿池嬌”含義的演變
元青花蓮池水禽紋又可稱為“滿池嬌”,然而以“滿池嬌”為名的并不止瓷器紋飾,從“滿池嬌”所代指的諸般名物,也可窺知這一紋樣的發展變化。
首先,根據柯九思宮詞中的自注,已經可知“滿池嬌”指池塘小景。根據清人畫譜,北宋崔白有八幅滿池嬌畫作,只是不知這一名稱是當時已有還是后人所加,但其意義是確定的。
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南宋文獻中,指稱織繡紋樣。吳自牧《夢梁錄》中有“挑紗荷花滿池嬌背心兒”。南宋黃昇墓中出土的褐羅抹胸即運用了池塘小景,可佐證吳自牧的記載。如上文,在元代“滿池嬌”仍是織繡紋樣的名稱。雜劇《梅香騙翰林風月》中言:“這香囊兒上繡著一把蓮滿池嬌,更有兩個交頸鴛鴦兒。”“滿池嬌”在此處仍指織繡紋樣,但不知兩種紋樣是否繡在同一面,或許已經和其他蓮紋“一把蓮”混用了。
“滿池嬌”出現的另外一個大宗是首飾。元初呂師孟墓中出土一枚鏤空滿池嬌金霞帔墜。明代世情小說中,常見“金鑲玉觀音滿池嬌頭面”一類的首飾,在傳世容像中也能看到。明王璽家族墓出土一件文殊滿池嬌金滿冠,上部為文殊菩薩與二弟子像,“滿池嬌”即為下部的蓮花與慈姑。蓮花枝葉隨風宛轉,但其中已無鴛鴦等水禽。
“滿池嬌”也出現在了對食物的描述中。《金瓶梅》中提到一品“喜重重滿池嬌并頭蓮湯”,這里的“滿池嬌”是指湯面上漂浮的諸般美食。如此命名,也是取了“蓮(連)”的吉祥意頭。
到了清代,“滿池嬌”的詞義更加擴大,纏足時代的酒桌游戲中也有以之為名者。方絢講擲瓊行令:“凡色以紅為蓮花,其名有七……六紅曰滿池嬌。”究其原因,不過是此種游戲以小足弓鞋行酒,命名取“滿池嬌”中“蓮”的意象以指“三寸金蓮”罷了。
由上文可見,“滿池嬌”是對蓮池小景類紋樣的統稱。它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直至明清這一名稱還被使用。它所指代的內容,從織繡紋樣到青花紋飾,到首飾圖樣,到美食名稱,再到酒令游藝用詞……在它的傳襲過程中,“蓮池”或“蓮”逐漸成為其基本元素,甚至是在蓮池的具體形象消失以后,蓮花的美好寓意和蓮池所營造的風波裊裊、紅香軟玉、各色時鮮的印象仍然存在于人們的記憶當中。
結語
元青花上的蓮池鴛鴦紋與元代織繡紋樣有著密切聯系,它們之間有無直接的催生關系還未有結論,但二者的共同來源是唐宋遼金、尤其是南宋時的花鳥繪畫與工藝美術。南宋時具有特定內涵的“滿池嬌”概念形成,是以荷花、水禽、蜂蝶等為元素的紋樣范式。其中蓮池為表現的主題,最具代表性的是蓮池鴛鴦。此類紋樣所具有宗教和世俗藝術的雙重內涵賦予了它持久的生命。“滿池嬌”的名稱和形式在元代之后被傳襲下去,“蓮”的意象是演變中所保留的基本要素。
參考文獻:
〔1〕尚剛:《鴛鴦滿池嬌——由元青花蓮池圖案引出的話題》,《裝飾》,2008(S1)。
〔2〕馬文寬:《元代瓷器研究中幾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元文宗——圖帖睦爾時代之官窯瓷器考>一文內容與劉新園先生商榷》,《藝術市場》,2005(4)。
〔3〕劉新園:《元文宗——圖帖睦爾時代之官窯瓷器考》,《文物》,2001(11)。
〔4〕劉新園:《元青花特異紋飾和將作院所屬浮梁磁局與畫局》,《景德鎮陶瓷學院學報》,1982(1)。
〔5〕矢部良明:《令人注目的元代式樣的青花瓷器》,《元染付》陶磁大系41,平凡社,1974。
〔6〕藏經書院:《萬續藏經》第108冊,新文豐,1983(9)。
〔7〕[清]方絢:《采蓮船》,南陵徐氏隨庵鈔本。
〔8〕[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6)。
〔9〕[元]柳貫:《柳貫詩文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8)。
〔10〕[元]張昱:《石初集·張光弼詩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7)。
〔11〕[晉]崔豹:《古今注校箋》,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