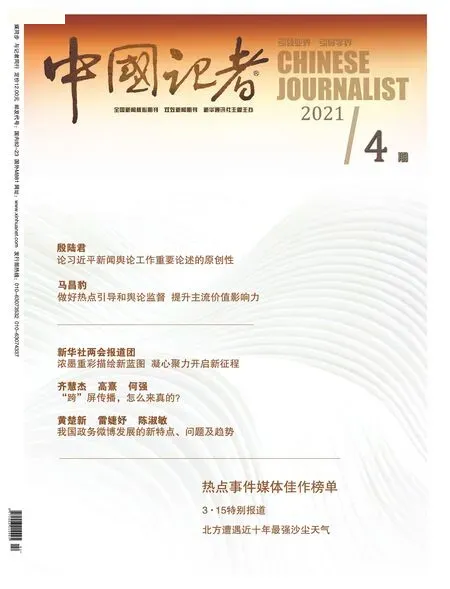郭超人新聞實踐的啟示
□ 邊江

郭超人(1934年—2000年)
郭超人是社會公認的名記者。他的新聞實踐起步于1956年10月從北京大學畢業后進入新華社,自愿申請奔赴條件十分艱苦的新華社西藏分社,在雪域高原工作生活了14年。這14年中,他以大量報道反映了西藏百萬農奴的解放,報道了中國登山健兒兩次征服世界高峰,其中《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報道“一戰成名”,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思想深度和寫作技巧方面受到新聞同行的好評,人民日報稱其“傳達了時代的最強音”。攀登希夏邦瑪峰的報道社會影響雖比前者略為遜色,但從報道角度總結,無論采訪、構思和寫作,都比前一次更加成熟。再就是他參加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的報道,采訪深入扎實,寫作也比較講究,“以輕松活潑的文字和具體生動的畫面表達了豐富的政治內容。”
1970年春,郭超人調任陜西分社,在這里度過了他稱之為“步履艱難”的8年。面對當時極其混亂的政治局面,他“決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調查研究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以求得真理性的認識。”他先后對關中平原、陜北高原、陜南山區三種不同類型的地區,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社會調查,分別寫出了《關中調查》(一組6篇)《延安紀事》(一組7篇)《安康見聞》(一組6篇)三組共計10萬字的系列調研稿。他還走遍大江南北,采寫了9000字的長篇通訊《馴水記》。
1978年,郭超人調到四川分社,“展現在我眼前的不僅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也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在這里過了難忘的4年。”在撥亂反正的歷史大變革中,他參加了一些重大事件的采訪報道和一些專題的社會調查,如《掃除唯心的階級估量》《四川涪陵山區調查》《歷史的審判》等。并走上分社領導崗位。
1983年1月,郭超人奉調北京,先是擔任新華社秘書長,隨即任新華社黨組成員,1984年起先后任新華社副社長、黨組副書記。1992年11月任新華社黨組書記、社長,直至2000年6月15日病逝在工作崗位上。郭超人生前先后選編出版了《西藏十年間》《向頂峰沖刺》《萬里神州馴水記》《郭超人作品選》《喉舌論》等新聞專著。
作為一名記者,郭超人無疑是成功的典范。他的珠峰登頂報道,一舉成名天下傳;他的三秦重點調研,針針見血真功顯;他的重頭稿馴水記,引吭高歌成名篇;他的新聞寫作經驗,心血凝就多璀璨;他在新華社掌舵期間,真抓實干領頭雁。郭超人的新聞采寫實踐,有許多突出特點和成功經驗,值得新聞界同仁認真學習和發揚光大。這些特點和經驗至少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畢生熱愛黨的新聞事業,這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紅線
郭超人把畢生心血和聰明才智都奉獻給了新華社,奉獻給了黨的新聞事業。他把新聞報道真正當作“安身立命之本”。當記者,他把圓滿完成采訪報道任務放在第一位;擔任分社領導以至當了新華社的“一把手”,他花費氣力最大的就是如何千方百計抓好報道業務。即便冗務纏身,他還惦記著采訪寫作,“渴望還有補救的時候”。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不久,一所大學的新聞系給郭超人寄來了一張調查表,上面開列了一連串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人不能當記者?什么樣的人能當記者?什么樣的人能當好記者?當時郭超人回答了三句話:“多數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不能當記者;多數人能想到、能做到的,你也能想到、做到,你能當記者,但可能是一般的記者;唯有多數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你想到了、做到了,才可能當一個好記者。”郭超人以他的新聞實踐證明,他是一個好記者,更是一個令人心服口服的中國名記者。如果沒有對新聞事業的摯愛,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
二、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武裝自己、提高自身基本素質
何為新聞采訪寫作的“訣竅”?郭超人認為:提高新聞采訪寫作水平,最重要的“訣竅”,莫過于加強記者自身的基本建設,莫過于在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思想感情、精神風貌上下功夫,概括起來說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質。這是比學習采訪方法和寫作技巧更為重要的問題。搞好新聞采訪寫作,還有一個“訣竅”,就是要不斷掌握和增強記者的基本功。這是決定記者工作成敗和寫作技巧高低的基礎。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也可以算得上“訣竅”,就是在采訪寫作時一定要擺脫狹隘眼界的束縛,跳出就事論事的藩籬,盡可能站在縱觀社會全局和歷史發展的高度上,把握和反映奔騰前進的時代精神。
當然,在談記者的基本素質時,僅僅講思想感情、講理想情懷是不夠的,還必須強調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武裝自己。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我們在復雜紛繁的社會現象中,一針見血地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質,寫出準確無誤的新聞報道來。曾與郭超人在陜西分社一起工作過的老記者王煌彥說:超人同志之所以成長較快,后來還成為新華社社長,這與他刻苦學習,并經歷過艱苦鍛煉分不開。“我親眼見過郭超人同志學習馬列全集做過的百萬字筆記,所以我見到超人同志在寫稿時嫻熟、準確運用馬列經典一點都不奇怪。”
三、掌握深入調研的真功夫,堅持“四勤”
“記者是在新聞實踐中磨礪出來的。新聞無處不在,但需要你邁開雙腿,到產生新聞的第一現場去發現、去感受、去采訪;需要你戴著眼睛去觀察,帶著耳朵去傾聽,帶著嘴巴去詢問,帶著思考去求證,帶著真誠去記錄,帶著責任去傳播。”這是郭超人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對記者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的思考,宛若與新時代的“四力”要求山鳴谷應。郭超人堪稱新聞工作者增強“四力”的典范。
新聞界的同志習慣地把記者分成兩類,一類是“窮記者”,一類是“富記者”。這個“窮”“富”,是指記者直接掌握客觀實際的材料多寡而言的。有的記者寫完指定的稿子以后,便“窮”到口袋里空空如也。可有的記者就不然,他隨時隨地像海綿吸水似的去占有各種材料,完成一篇篇報道以后,腦子里還有豐富的儲存。不當“窮記者”,要當“富記者”,除了堅持不斷地進行專題調查研究外,還要學會經常性地積累材料。
郭超人《在寫作技巧的背后》一文中寫道:“20多年來,我的挎包里經常裝著三種筆記本子,一種作采訪筆記,一種是生活雜記,還有一種是思考摘記。生活雜記內容豐富,包括山川風物,傳聞軼事,突出的印象,有趣的人物,生動的場景,等等。總之,記錄下自己觀察、接觸到的一切。”據資料顯示,郭超人在采寫關中、延安、安康三組調研和采寫《馴水記》時,每次調查的原始記錄均達到30萬字以上。
1973年5月,郭超人與陜西分社記者王長寬、姜卯生到關中的渭南、咸陽、西安、寶雞等地進行調查研究,訪問了一些地縣負責同志和有實踐經驗的農村干部群眾,考察了一些具有不同特點的先進典型,經過認真討論,寫出了一萬五千多字的關中調查匯報材料,打印后正式上報分社進行研究。其后經過進一步深入采訪,郭超人與分社同事何奇、姜卯生于1974年初,合作寫成一組六篇近3萬字的《關中調查》。這組調研稿一反“文革”時期空話套話連篇的文風,本著“綜合宜少,典型宜多”的精神,以面上和點上的翔實事例及數字比較,分析了關中地區農業生產的歷史、現狀、存在問題和發展潛力,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引起陜西省和各地縣的重視。
曾任延安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的師銀笙同志說:“郭超人當年在基層采訪,從來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扎扎實實深入民眾之間,與許多人結成肝膽相照的朋友。我在《延安報》工作時,曾和他一起在志丹縣采訪了一周時間,除了深入鄉村,還到不少治山治水的工地直接采訪。我給本報寫了3篇長通訊請他指教,他語重心長地指著堆在他桌上的一大摞資料對我說:‘你應掌握更多東西,別急著完稿……’我看了他的采訪筆記,不僅有采訪對象的記錄,還抄錄了《志丹縣志》,歷年的糧食產量、農田進度甚至20多年的氣候情況,怪不得他每晚都睡得很遲,一周時間光筆記就記了十幾萬字。時間不久,《人民日報》刊登了他寫的長篇通訊《馴水記》,有關志丹的文字也只有區區300多字,他的行動使我真切感受到做一名合格記者就得練就‘拾到籃里都是菜’的過硬功夫。看到如此大的差距,趁他又一次來延安的機會,我邀請他給我們報社編輯部的同志講了新聞采訪課,他從登珠峰說起,怎樣研究世界登山史,怎樣提煉主題,怎樣運用材料……讓大家醍醐灌頂,受用終生。他的這次講課經整理后,成為我們報社培養記者、通訊員的重要教材。”
四、堅持真理,敢講真話
郭超人曾有名言:“記者筆下有財產萬千,筆下有毀譽忠奸,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人命關天”。選擇做記者,就是選擇了奔走和忙碌,選擇了勇敢和責任,選擇了為別人作嫁衣,為歷史做記錄。無論何時何地,責任不可丟棄,操守不可廢置。他說“我堅信不疑的是,凡屬實事求是的新聞報道會經受住時間的檢驗,會透過歷史的塵埃,從不同側面反映出時代的風貌,記錄著社會的進程,顯示自己獨特的生命力。”
郭超人正是抱著這種負責的態度,恪守職責,為新聞的真實負責,為筆下的每一個字負責。當年在《延安見聞》中,他針對延安工作明明落后于全國的發展形勢,但延安的一些領導同志卻仍沾沾自喜、感覺良好,認為在延安講“落后”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與“延安這個革命圣地的光榮地位相比”,撇開這些政治條件,“延安在革命和生產上是過得去的”。郭超人經過認真調查,用事實和數據,從糧食生產、多種經營和群眾經濟狀況以及農業機械化等方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延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在糧食生產問題上,一些同志總是以1949年的延安糧食總產為基數進行對比,但在戰爭剛過背景下的1949年,延安的糧食產量遠低于歷史上的平均水平;從按人口平均生產糧食的數量上說,即使以1949年為基數,延安20多年來的糧食增長速度也很有限;如果把延安24年分成四個階段來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全區人均給國家貢獻的糧食絕對數量很小,而且呈現出一個逐年下降的趨勢。同時,新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統計資料表明,延安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問題一直未能很好解決;植樹造林沒有抓緊抓好;延安農村群眾的經濟收入偏低,部分群眾的生活還有很大困難;農業機械數量增加快,但使用效率很低。他在《關中調查》《安康見聞》中,也分別指出了存在的購“過頭糧”及個別地方“瞞產”等問題,并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看法和建議。

□ 20世紀70年代,新華社陜西分社記者郭超人、王長寬、張廷干、景杰敏(自左至右)在延安采訪時留影。
五、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曾與郭超人一起參加《關中調查》的老記者姜卯生說,我們幾個人當時分工前往關中的西安、寶雞、咸陽、渭南及所屬縣區進行采訪調研,超人同志除完成他所包的地縣外,還主動前往西北大學查閱關中農業歷史資料,并請一些知名專家開了座談會,把一些重要內容寫進了稿中。超人同志是一個非常能吃苦的人,他不僅稿子寫得好,還在單位當時每周的生產勞動中干在前邊。我至今記得老郭穿著舊軍裝,率先爬上房頂打掃樹葉的景象。我曾笑說老郭你這名字起得太厲害了,超人同志笑著回答:“力爭上游嘛!”

□ 1992年10月13日,黨的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右一)、總編輯南振中(左一)參加小組討論。(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攝)

□ 為紀念新華通訊社新聞攝影部成立40周年,題為《征程紀實》的攝影展覽1992年4月1日在北京開幕。郭超人(左二)在觀看影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攝)
師銀笙回憶說,超人同志1970年調來陜西后,就把重點放到延安,每年都多次來延,采寫了許多重頭報道,他和延安的干部群眾特別是新聞工作者結下深厚情誼。他對革命圣地有濃烈的感情,為延安的貧困而揪心,為群眾的淳樸而動情,經常帶領基層通訊員深入采訪,腳印走遍延安的山山水水,采寫了不少干部、工人、農民,常常秉燭疾書,不少報道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可以不夸張地說,延安的通訊隊伍是在超人同志的親自培育下逐漸成長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后,超人同志加入延安人民自動祭奠的行列,“四人幫”之流下令不許公開報道,他含淚寫了4篇材料,冒著危險向中央反映了民情。超人同志對延安的朋友確實像親人一樣。一次我去新華分社,他親自下廚炒了家常豆腐等幾個菜招待我。
趙志祥是從陜北的一個縣委通訊干事,逐步成長為延安地委通訊組干事、地區報刊記者,后來調入新華社陜西分社,并成為分社副社長的。他說,當年郭超人、馮森齡及多位新華社記者來到延安,帶著我們采訪,合作寫稿,幫助我們成長。我曾經跟著超人同志到宜君、黃陵等縣采訪,同吃同住同采訪,他言傳身教,使我獲益匪淺。
李彬同志曾在延安從事和負責新聞宣傳工作十多年。在此期間,他認識了常來延安采訪的新華社記者郭超人,多次為他采訪提供過服務,并合作采寫過稿件。20世紀70年代,延安在經歷干旱水災等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后,建國二十多年了還長期處于發展停滯貧困落后狀態。不少干部群眾和知識青年,想不通看不慣,就把怨氣撒在過去曾經的老英雄老模范身上,說什么“只吃老本”“不立新功”“落后難免”等。有一次郭超人來延安,住在南關招待所,我和他談心,交換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一語“點破機關”:為什么不反躬自問?我們丟掉了什么?不正是當年毛主席當年提倡、陜甘寧邊區政府樹立起來的這些英模人物身上閃光的東西?這體現著延安精神呀!他特別強調說:“延安精神的重建,是改變延安老區面貌的根本所在!”于是,我們倆如數家珍般回顧了延安幾位健在的老英雄、老模范的事跡,這些大都作為素材詳細記錄在超人同志的采訪本上,后來見之于他的新聞報道中。
郭超人同志離開我們已經20年了。但他的精神長存,他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鼓舞著我們新聞人不懈努力,勇往直前。
【注釋】
[1]郭超人作品選[M].新華出版社,1999.
[2]郭超人作品選[M].新華出版社1999.
[3]郭超人作品選[M].新華出版社1999.
[4]郭超人作品選[M].新華出版社1999.
[5]郭超人.中青年記者經驗談[M].希望出版社,1987.
[6]郭超人.在寫作技巧背后,新華社采編經驗選萃[M].新華出版社,2000.
[7]惠小勇,黃毅.淺談郭超人西部新聞實踐之“四力”[J].中國記者,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