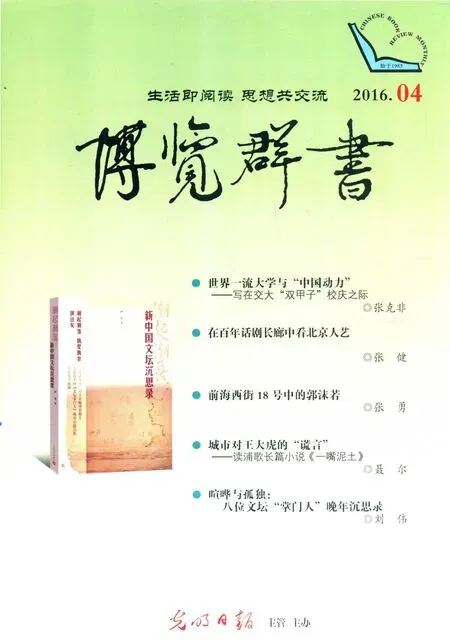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杜威五大講演》與中國現代化
李媛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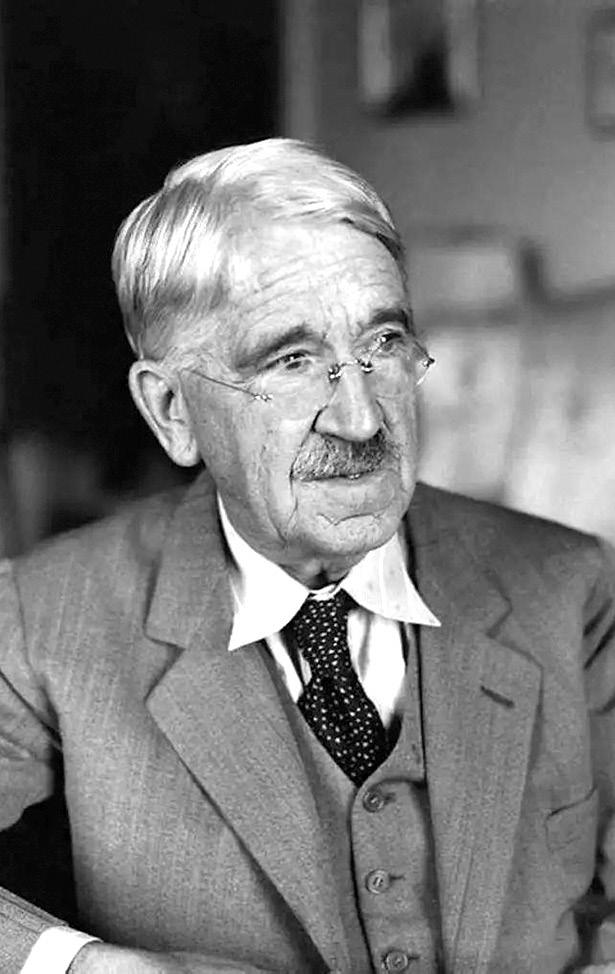
20世紀初的中國,時局動蕩,云詭波譎,新舊力量沖突、中外思想碰撞異常劇烈而復雜,中國正在內憂外患中迎來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現代轉型。一個時代的變遷,需要新的信念、新的思維、新的方法的驅動。此時,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先驅者,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創者約翰·杜威的訪華,無疑是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教育界甚至是政界的一大盛事。
壹
杜威于1919年5月1日(一說4月30日)到達中國,4天之后,“五四”運動爆發。這次運動的起因是抗議巴黎和會將戰敗的德國在華租地轉給日本,但很快就從民族抗議活動發展成思想文化運動。原定于1919年夏天回國的杜威夫婦,一再推遲歸期,據其女兒的回憶:“人們在中國為了建立一個統一而獨立的民主國家而進行的斗爭的吸經力,使他們改變了他們想在1919年夏天回美國的計劃。”
杜威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場運動中所蘊含的革命力量,他以極大的熱情關注著中國的社會變革,在發表在《亞洲》雜志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訴西方人:“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中國人為爭取民族獨立、反抗列強壓迫的斗爭,既讓杜威深深感動,又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杜威不僅是作為一個中立的旁觀者地觀察一個磨難中的國家怎樣沉淪或奮起,而是作為一個參與者,投身于推動中國政治重建和思想轉型的歷史進程之中。
杜威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來到中國,于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離開中國,歷史時段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在華活動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在中國的兩年多時間,杜威夫婦的足跡遍及了中國的11個省份(除北京、上海外,還包括河北、遼寧、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共做了二百余場演講,主題包括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西方思想史、倫理學等。這些演講曾在《晨報》《新潮》《申報》《新教育》等報刊上發表,最終結集為《杜威五大講演》。在杜威離華前,這個演講集就曾重版了十余次,風靡一時,之后又多次再版。這些演講在思想界引起熱烈的反響,在江蘇教育會所講“平民主義的教育”,“聽者之眾,幾于無席可容”;在廣東高師的講演,到場近千人,“座無隙地”;在杭州的演講,“到者不下兩千人”;在北京尚志學校的演說,“雖揮汗如雨,而聽眾素靜無一離坐者”。正如賀麟所言:“在現代西方哲學各家各派中,對舊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應該首推杜威。”此時的中國,風云激蕩,山雨欲來。歷史的局中人并不能預見未來,但他們有非常強烈的渴望,即接受新知,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在晚清之后所遭遇的一系列政治革命的失敗,彰顯出思想革命和知識革命的必要性。西方各派思想學說在中國大地上粉墨登場,又逐漸散去。殊為難得的是,在思想界內部紛爭嚴重、學術派系林立的情況下,杜威的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各方認可。無論是以胡適、蔡元培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還是以梁啟超、梁漱溟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改良派,以及以孫中山、陳獨秀為代表的革命派,都認同杜威的學說。究其原因,一是杜威在華演講中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理念正符合“五四”時期的時代潮流,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種能使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用西方科學的精神,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杜威恰逢此時來華傳道授業,自然受到普遍歡迎。二是杜威對中國問題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與同期來華演講羅素相比,杜威的學說更為平實易懂。并且,羅素哲學專注數理邏輯,并不擅國際政治,一問及中國改革方案時,就閃爍其詞,前后矛盾。而杜威在深入細致地觀察中國實際的基礎上,設身處地提出諸多解決方案,切中肯綮,更符合中國人的現實需求。三是杜威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有諸多契合之處。如,杜威在中國被稱作“西方的孔子”或“二孔子”,蔡元培先生曾指出:“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此外,杜威的實用主義精神與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以及身心不二的哲學主張也頗有相通之處。
貳
杜威親身見證了“五四”運動,這場運動雖不是時時直接在演講中提起,卻是杜威在中國演講的潛在背景和問題意識所在。他在演講中不斷回應這些問題:什么是真正的愛國?未來的中國要建立什么樣的國家、什么樣的政府、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才是個體與國家的良性關系?作為長者和師者,他如此評價學生運動的利弊:利在更為深切明了政治、教育、商業的情況,培養了公共利益和團結互助的精神;弊端在于愛國心切,往往感情用事,難以專業讀書,在教育方面遭受損失。對此,他的建議是:
愛國心也要有智理作用。因為情緒是靠不住的,還要理性的觀念去利導他,糾正他,才能真正造福國家。要是率意妄行,不但無益,恐怕有害呢!
他建議青年人不要消極排外,而應該去做積極的事業,即推廣教育,改良體育,發達實業,提倡國貨,或增進平民的生產和消費力。其目的在于增進國家和社會公共秩序的穩定。因此,必須胸懷更遠大的目標,有目的、有方法、有決心。
杜威主張,研究中國,首先要從問題出發。他剖析了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辛亥革命的相對不成功是由于這樣的事實:政治變革超越了知識上和道德上的準備,這種政治革命只能是形式上的、外部的。因此,在名義上的政府革命兌現之前,需要有理智的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需以思想革命為先導。同時,政治必須與生活鉤聯,政治革命之所以失敗,因為它未觸及生活構想,而生活構想控制著社會。那么,如何進行理智的革命?其一,在立場上,不尚空談,知行合一。杜威是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這派哲學源于實驗室哲學,認為任何哲學命題的有效性,都需要通過實際經驗中的結果來驗證:“一盎司經驗所以勝過一噸理論,只是因為在經驗中,任何理論才具有充滿活力和可以證實的意義。”重行動,而輕不切實際的空談,這是實用主義的基本精神取向。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這種實證理念與實干精神的輸入是至關重要的,它對于當時思想界空疏浮泛的風氣提供了一劑良藥。其二,在方法上,科學思維,具體解決。杜威認為,科學的價值,在于其方法,對于中國而言,需要打破籠統的、抽象的、理想的方法,而專注于個體的、特別的、事實的方法。杜威呼吁中國人“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機會,而要用科學的智識來指揮一切,向導一切”。在科學精神和方法的指導下,運用理性,尋求對問題的具體解決和修正方案。其三,在目標上,團結行動,實現共和。杜威指出,中國人素來重家族主義與部落思想,公共精神較為缺乏,反映在政治領域,則是黨派思想強于國家觀念。他認為,“政治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組成一個國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對于中國而言,如何建立真正的共和國?杜威的回答是:欲養成共和國之精神,有兩大要素:“第一要素為愛自由”,“第二要素為共同動作”。前者是對于一個具有自主行動力和主體性的個體的要求,后者則是號召在精神團結和一致行動基礎上形成組織力。這些言論,可謂振聾發饋,充滿了真知灼見,在20世紀初的中國引導了一場思想、教育和政治理念的啟蒙,這場思想洗禮和觀念革新在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叁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很多先驅者都曾對杜威在中國的演講內容報以密切關注。1919年7月,周恩來擔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期間,就在“創刊號”上把杜威的實驗主義稱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1920年10月,杜威在蔡元培等人陪同下到長沙講演,毛澤東被特邀為此次演講的記錄員;1921年4月,陳獨秀在廣州以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親自主持杜威的演講會。李大釗、瞿秋白、惲代英等人也都在信件、日記中提及過杜威的學說。1919年9月,毛澤東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列出需要研究的問題71類,其中包括杜威教育學說如何實施問題。1920年3月,毛澤東到黎錦熙處,專門討論了近代哲學派別(柏格森、羅素和杜威)問題。6月7日,在致黎錦熙信中,又寫道:“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只這三科。哲學從‘現代三大哲學家起,漸次進于各家。”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人對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接受與信仰,是在廣泛了解西方各家各派學說,并吸收其合理因素基礎上的理性選擇。杜威在中國的演講,一方面引領中國人從舊思想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以科學理性喚醒民主意識,客觀上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事實上,杜威思想與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有諸多殊途同歸之處,這在1919年在新文化陣營內部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這場論爭的背后,是兩個哲學流派或指導思想的爭論。李大釗代表的是馬克思主義學說,胡適代表著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這場論爭不僅在學理層面展開,也關系到中國政治道路的選擇,因此備受矚目。然而,這場論爭絕非后世教科書所描述的那般刀光劍影、針鋒相對,在基本立場上二者并無根本分歧。胡適并不是反對“主義”,而是反對用抽象的“主義”遮蔽了對具體問題的關注。他說:
我并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后,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李大釗也并非空談主義,認為學理是研究具體問題的工具: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
由此可見,李大釗與胡適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并無分歧,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二者并行不悖,其差異在于側重點的不同。事實上,杜威本人也強調目標指引和路線方法具有同等重要性:
吾們對于現制度要去解決具體的問題之外,還須有一點能指導全體的觀念。譬如航海,有了羅盤,一定還要有地圖。
恰如這場論爭所昭示的,其背后的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與杜威的實用主義之間,雖然批判的對象不同、針對的論敵不同、采用的方法論不同,最終的目標卻是不謀而合。從思想淵源看,馬克思與杜威的思想均受惠于黑格爾哲學;從理論訴求看,都認為哲學不應采取旁觀者的姿態,而應保持介入現實的參與性;從方法路徑看,都通過獲得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改造,來尋求確定性;就精神實質看,都體現了鮮明的人道主義關懷,即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最終目標。杜威在華演講中,有很多觀點和立場都與馬克思不期而同。例如,杜威指出,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實則是兩個社會的沖突。用馬克思的話說,是階級之間的沖突。杜威在演講中集中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壓迫,提出為什么工人不肯用力,因為他們覺得做工是為生計逼迫的,因此沒有興趣,不是故意搗亂,便是糟蹋搗亂,消極抵抗。可以看到,杜威有一種強烈的反對不公、反抗強權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批判意識,這與馬克思主義在價值立場上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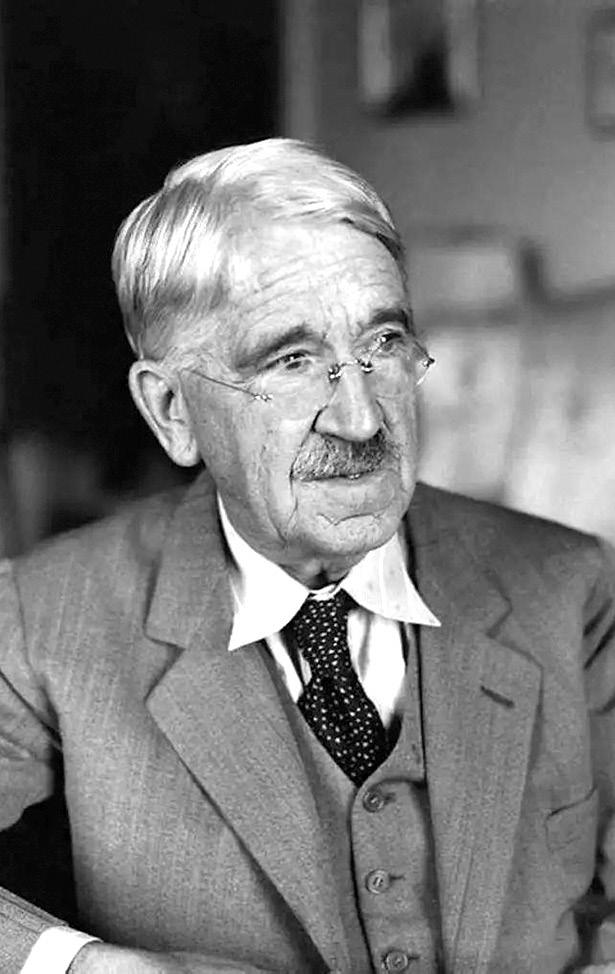
毫無疑問,杜威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之間也存在明顯差異。在哲學立場上,杜威堅守一元論,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二元論為前提。杜威強調經驗第一性,而馬克思強調實踐第一性。杜威不倡導革命的方式,希望通過個體經驗的完善來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馬克思則探求通過社會制度的激進變革尋求根本性的解決。杜威的影響力主要在知識精英和青年學生中,并未滲透中國社會的底層,而馬克思主義則走向民間,在勞工群眾中進行革命動員。這些差異,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得到接受,而實用主義未能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原因。在國家命運危在旦夕、時局內外交困的嚴酷環境下,已不允許中國人繼續溫和、漸進地改良,而是需要一種具有號召能力和戰斗品格的指導思想來凝聚意志,指明方向。
肆
今日的中國已經走過血雨腥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塵埃落定之時,重讀《杜威五大講演》,會發現其中的很多觀點依然具有特殊的超前性和啟發性,熠熠生輝,發人深省。
其一,立足現實,走中國本位的發展道路。20世紀初,對于中國而言,最大的問題是應該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杜威的回答是,中國未來的道路,不是復制西方,也不能效仿日本,而要立足自身,走更良性健康的現代化之路。杜威希望中國可以免除西方社會政治的弊端,吸取其長處。因此,未來的中國“不單去輸入模仿,要去創造,對于文化的危險有所補救,對于西洋社會的缺點有所補益,對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貢獻”。同時,“中國不能求助于日本式的西方化版本,而要走進給予以西方道德和思想以靈感的泉源。這樣的求索并不是為了獲得自己往后用來仿造的模式,而是為了獲得借此可用來更新自己制度的觀念和思想的本錢”。從本原性的文明源頭吸取資源,推動自身的觀念重塑和制度創新。杜威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看到,如果允許中國人去完成他們自己的經濟目標,那么可以想象,他們會設計出一種比如今困擾著西方國家的那個方案更好的方案。今天的中國確乎走著一條不同于西方,卻又異常成功的現代化之路,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選擇和替代性方案。
其二,積極揚棄,客觀理性地看待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杜威在中國的演講中,系統梳理了西方自由主義啟蒙思想發展脈絡,深入剖析了西方自由與民主的本質,提出自由與平等并非并行的,西方社會出現經濟和勞動領域的不平等,恰恰是由于自由太甚。例如,表面上是基于雙方自由意志訂立的契約,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建立在平等能力的基礎之上,因而造成了極端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在西方大國雄霸世界之時,杜威卻始終對西方文明懷有一種隱憂,而在中國則看到了其道德目標和社會理想實現的可能性,這種理想的實現需要根據國情對西方自由民主傳統的積極批判與揚棄。
其三,古為今用,在現代化轉型中需要重新挖掘傳統的價值與資源。在杜威來華演講期間,恰是新文化運動高歌猛進之時。如何看待中華文化?如何保存其固有之優點?如何學習西方?如何有效吸納,而不失其本根?在保國保種的壓力之下,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普遍對傳統文化持質疑甚至拋棄的態度,杜威清醒地指出:
幾千年的經驗背著走不動固然不好,然而經驗也有許多好處,含有許多人本觀念,也可用新的方法來整理一下,應用到社會科學方面去。
在杜威看來,凡是站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可靠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系統的思想和信仰。這套思想信仰是整體性的,全盤打破,將使一個民族失去根脈,無以在世界立足。
其四,融匯貫通,謀求中西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杜威在演講中對比了東西文化的差異:
東方思想更切實更健全,西方思想更抽象更屬于智理。……西方倫理根據個性,東方倫理根據家庭。……西方倫理尊重個人利權,東方倫理蔑視個人利權。
但比較的目的不是論其短長,而是在相互理解之后的取長補短、融匯貫通。杜威認為:“現在文化的新問題不是往前走去環繞地球的問題,而是東西文化怎樣互相接近怎樣互相影響的問題。”杜威認為,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中國文明在歷史上一直是多元性與普遍性共存的取向,對于異質性因素采取包容態度,兼收并蓄、合而統之。杜威在中華傳統與世界文明發生激烈碰撞之時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兼容并包的特質,并提出了文明匯通的希冀與期待。這對于當今這個文明沖突、零和博弈思維盛行的世界,是一種有力的矯正;對于新時代中國的文明崛起,則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