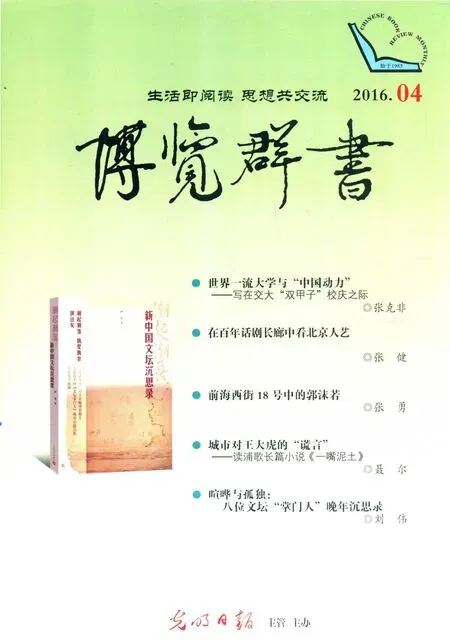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盛世危言》對(duì)毛澤東的影響
劉悅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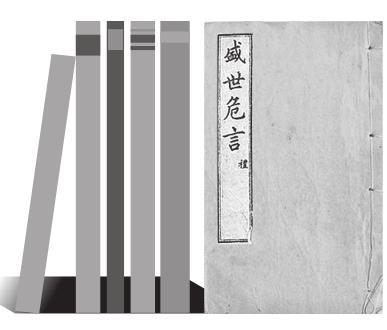
毛澤東一生嗜書如命,古今中外,經(jīng)史百家,軍事科技,閱讀范圍非常廣博,其中有些書對(duì)他產(chǎn)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如他自陳馬克思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考茨基《階級(jí)斗爭》、柯卡普《社會(huì)主義史》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是毛澤東青年時(shí)代的事情。而在他的少年時(shí)代,也有一本可以說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的書,這就是清末實(shí)業(yè)家、維新思想家鄭觀應(yīng)的《盛世危言》。
毛澤東家境尚可,因此小時(shí)候能夠上學(xué)讀書,學(xué)習(xí)了基本的文化知識(shí)。但是家境也沒有富裕到可以讓他一直自由讀書的程度,因此在學(xué)習(xí)了基本的文化知識(shí)后,他的父親便讓他回家干農(nóng)活了,這一年他13歲。但是,求知欲強(qiáng)烈的毛澤東已經(jīng)放不下對(duì)書本的熱愛和對(duì)知識(shí)的追求。30年后,在延安的窯洞里,毛澤東饒有興味地向斯諾講述了他少年時(shí)代讀書求學(xué)的經(jīng)歷。他對(duì)斯諾說,他在干農(nóng)活的同時(shí),“還是繼讀書,如饑似渴地閱讀凡是我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但“經(jīng)書除外”,這讓他父親很生氣,“他希望我熟讀經(jīng)書,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時(shí),由于對(duì)造在法庭上很恰當(dāng)?shù)匾?jīng)據(jù)典,使他敗訴之后,就更這樣了”,于是,為了讀書,“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到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xué)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bào)、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見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董樂山譯)。
人們在多年后回憶早年特別是童少年時(shí)期的事情時(shí),能回憶起的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對(duì)他影響非常大的事情。《盛世危言》這本書是毛澤東從他的表兄文運(yùn)(詠)昌處借的。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毛澤東早年手跡,就包括毛澤東給文運(yùn)昌還《盛世危言》等書的還書便條,全文如下:詠昌先生:
書十一本,內(nèi)《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叢報(bào)》損去首頁,抱歉之至,尚希原諒。
澤東敬白。
正月十一日。
據(jù)考訂,這張便條是1915年2月24日毛澤東由長沙回韶山過春節(jié)期間寫的,說明這本書在毛澤東處達(dá)七八年之久。之所以會(huì)有這張便條,據(jù)說是文運(yùn)昌知道毛澤東嗜書如命,怕他不還,說:“相公借書,老虎借豬,所以要先打條子后拿書。”故而毛澤東借書要打借條,還書也有便條,當(dāng)然也可能是毛澤東因?yàn)闀袚p壞為了表示歉意才寫的這張便條。不論如何,這張便條為少年毛澤東借讀過《盛世危言》提供了確鑿的證據(jù)。
毛澤東從文運(yùn)昌處借的書,還有馮桂芬的著作《校邠廬抗議》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bào)》等書刊,但是他對(duì)斯諾憶當(dāng)年時(shí)只單單提到了《盛世危言》,而且還清晰地記得書中的主要內(nèi)容,可見這本書給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和對(duì)他的影響之大。
《盛世危言》對(duì)少年毛澤東的影響,至少有兩個(gè)方面。
一是開闊了他的眼界,為他打開了一個(gè)嶄新的世界,使他對(duì)西方國家何以民富國強(qiáng)、欺凌中國,中國何以民窮國弱、屢屢挨打有了一定的認(rèn)識(shí),對(duì)鄭觀應(yīng)提出的富國強(qiáng)兵、抵御外侮的主張和辦法心有戚戚,所以他才“非常喜歡”這本書。受這本書的影響,毛澤東開始成為一個(gè)熱切希望改變國家貧窮落后面貌的愛國的改良主義者。
二是重新燃起了他繼續(xù)求學(xué)的愿望,他對(duì)斯諾回憶說:“《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復(fù)學(xué)業(yè)的愿望。我也逐漸討厭田間勞動(dòng)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duì)這件事的。為此我們發(fā)生了爭吵,最后我從家里跑了。我到一個(gè)失業(yè)的法科學(xué)生家里,在那里讀了半年書。”這一年毛澤東16歲。之后他父親決定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去當(dāng)學(xué)徒,可就在這時(shí),“我聽說有一個(gè)非常新式的學(xué)堂,于是決心不顧父親反對(duì),要到那里去就學(xué)。學(xué)堂設(shè)在我母親娘家住的湘鄉(xiāng)縣。我的一個(gè)表兄就在那里上學(xué),他向我談了這個(gè)新學(xué)堂的情況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經(jīng)書,西方‘新學(xué)教的比較多。”“在這所新學(xué)堂里,我能夠?qū)W到自然科學(xué)和西學(xué)的新學(xué)科。”這個(gè)表兄就是文運(yùn)昌,這所新式學(xué)堂就是東山高等小學(xué)堂,毛澤東想到這所新式學(xué)堂學(xué)習(xí)“自然科學(xué)和西學(xué)的新學(xué)科”,無疑也是受了《盛世危言》的影響。這一年毛澤東17歲。從此,這個(gè)走出韶山?jīng)_的少年一發(fā)不可收,在求學(xué)和求知的路上越走越遠(yuǎn),從東山高等小學(xué)堂到湘鄉(xiāng)駐省(長沙)中學(xué)堂,再到湖南全省高等中學(xué)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xué))、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xué)校,再到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中心北京大學(xué),在這過程中接觸到越來越多的新思想新學(xué)說新理論,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一個(gè)改良主義者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堅(jiān)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盛世危言》之所以對(duì)少年毛澤東會(huì)產(chǎn)生如此大的影響,自然是緣于這本書的新鮮內(nèi)容和思想傾向。
《盛世危言》的作者是鄭觀應(yīng)。鄭觀應(yīng)(1842—1921),本名官應(yīng),字正翔,號(hào)陶齋,別號(hào)杞憂生,晚年自號(hào)羅浮偫鶴山人,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鄭觀應(yīng)16歲時(shí)應(yīng)童子試,沒有考中,即奉父命放棄了科舉考試之路,遠(yuǎn)游上海,棄學(xué)從商。他早年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買辦,不僅積累了財(cái)富,更積累了經(jīng)營、管理現(xiàn)代工商企業(yè)的經(jīng)驗(yàn)。19世紀(jì)70年代被李鴻章攬入門下,從此躋身于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備受李鴻章的重用,歷任上海機(jī)器織布局幫辦、總辦,上海電報(bào)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漢陽鐵廠總辦和商辦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等重要職務(wù)。
鄭觀應(yīng)并不只是一個(gè)追逐利潤和財(cái)富的商人、實(shí)業(yè)家,更是一個(gè)愛國的維新思想家。他在從事于實(shí)業(yè)的同時(shí),非常關(guān)心國家的命運(yùn),他自號(hào)“杞憂生”,正體現(xiàn)了他對(duì)國家命運(yùn)的擔(dān)憂。進(jìn)入近代以來,西方列強(qiáng)用堅(jiān)船利炮轟開了中國閉關(guān)鎖國的大門,迫使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這些不平等條約為依據(jù),以堅(jiān)船利炮為后盾,對(duì)中國進(jìn)行全面的侵略和滲透。對(duì)此,鄭觀應(yīng)痛心疾首,“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為探索自強(qiáng)御侮之方,他積極了解西方的富強(qiáng)之道,“學(xué)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都人士交接,察其習(xí)尚,訪其政教,考其風(fēng)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究心泰西政治、實(shí)業(yè)之學(xué)”。在他看來,“茍欲攘外,亟須自強(qiáng);欲自強(qiáng),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xué)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將自己的觀感、思考筆之于書,刊布于世,期望引起國人對(duì)國家命運(yùn)的重視和對(duì)自強(qiáng)之道的探索。他著述甚多,主要有《救時(shí)揭要》(1872)、《易言》(1880)等,而《盛世危言》(1894)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
如果說,《救時(shí)揭要》主要是揭露西方資本主義列強(qiáng)侵略中國的各種罪惡行徑,反映了他對(duì)西方列強(qiáng)的義憤和痛恨,那么,《易言》則開始提出抵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方法,即改變傳統(tǒng)做法(“易”即改變),向西方學(xué)習(xí),發(fā)展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鄭觀應(yīng)把《易言》稱作《救時(shí)揭要》的續(xù)篇。《盛世危言》則是鄭觀應(yīng)維新思想的集大成,標(biāo)志著鄭觀應(yīng)改良主義思想走向成熟。所謂“盛世”,不過虛晃一槍,或者暗含譏諷,重點(diǎn)則在“危言”,即警醒國人之言,當(dāng)時(shí)很多人就直接以“危言”稱該書。
鄭觀應(yīng)主張向西方學(xué)習(xí),在方法論上與洋務(wù)派是一致的。但是,在學(xué)習(xí)內(nèi)容上,卻超出了李鴻章等洋務(wù)派。在他看來,西方先進(jìn)的堅(jiān)船利炮、鐵路電線、聲光化電固然要學(xué),但這些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還應(yīng)該學(xué)習(xí)西方的“政教制度”,用他自己的話說:“治亂之源,富強(qiáng)之本,不盡在船堅(jiān)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yǎng)得法,興學(xué)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nóng)學(xué),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shè)電線,薄稅斂,保商務(wù),使物暢其流。”他是最早注意到西方國家富強(qiáng)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的中國人之一,批評(píng)洋務(wù)派只學(xué)習(xí)西方的軍事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是舍本逐末:“余平日歷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zhèn)洹S庞跁海撜谧h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難臻富強(qiáng)。”他明確指出:“政治關(guān)系實(shí)業(yè)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shí)業(yè)萬難興盛。”具體到經(jīng)濟(jì)上,鄭觀應(yīng)還是主張與西方列強(qiáng)進(jìn)行“商戰(zhàn)”的代表人物。
《盛世危言》造端宏大,包括附錄在內(nèi)共約200篇文章,內(nèi)容十分豐富,從目錄中即可見一般,諸如學(xué)校(2篇)、西學(xué)、議院(2篇)、自強(qiáng)論、公法(即國際法)、通使、交涉(2篇)、條約、汰冗、革弊、商戰(zhàn)(2篇)、商務(wù)(5篇)、鐵路(2篇)、電報(bào)、郵政(2篇)、銀行(2篇)、開礦(2篇)、練將、練兵(2篇),如此等等,既有布新,也有改舊、除舊,目的只有一個(gè),就是“富強(qiáng)救國”。可以說,《盛世危言》是當(dāng)時(shí)一個(gè)全面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化方案。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此前一直接受傳統(tǒng)教育,課上讀的是“經(jīng)書”、課外讀的是《精忠傳》《水滸傳》《西游記》等舊小說的少年毛澤東,在看到這些文字時(shí)會(huì)是怎樣地感到新奇、興奮和激動(dòng)。一個(gè)嶄新的世界展現(xiàn)在他的面前,引導(dǎo)他邁上繼續(xù)求學(xué)、求知的道路,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作為鄭觀應(yīng)最重要的著作,他對(duì)《盛世危言》十分重視,不斷修訂。1894年成書時(shí)是5卷本,1895年修訂為14卷本,1900年再次修訂為8卷本,盡管卷數(shù)增加又減少,但整體篇幅是一直增加的。除鄭觀應(yīng)親手修訂的3個(gè)版本外,坊間還有很多其他的版本。《盛世危言》在當(dāng)時(shí)是暢銷書,發(fā)行量相當(dāng)大,這也是生活在農(nóng)村的少年毛澤東能夠讀到這本書的原因。我們現(xiàn)在難以確定當(dāng)年毛澤東讀到的是哪個(gè)版本,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年毛澤東讀到了這本書,并深受這本書的影響,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這是毛澤東個(gè)人之幸,更是中國之幸。因此,我們不能不對(duì)鄭觀應(yīng)這位維新思想家和《盛世危言》這部他的代表作三致敬意焉。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xué)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