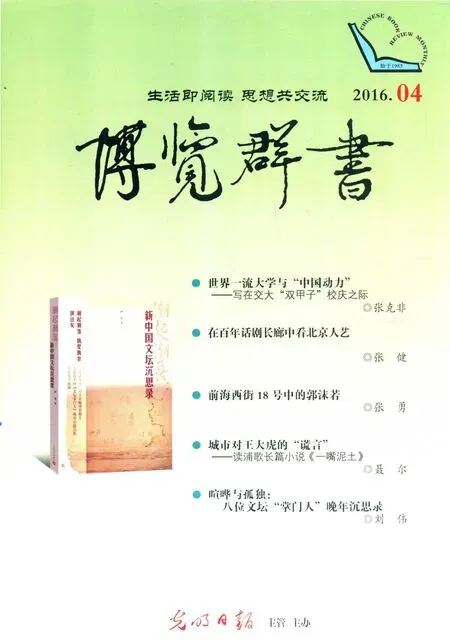在此一窺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
葉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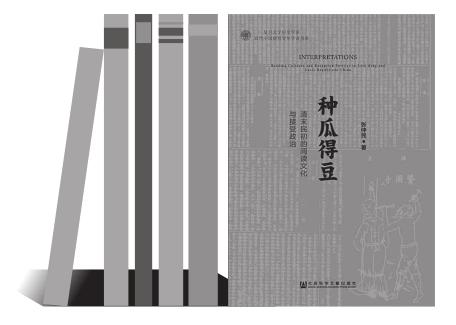
近代以來(lái)的閱讀史是張仲民博士的持續(xù)興趣,此前已有《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wèi)生”書(shū)籍研究》(上海書(shū)店出版社2009年版),近期又有《葉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當(dāng)然我更看重的,還是這部《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的題目都是我饒有興趣的,在“清季啟蒙人士改造大眾閱讀文化的論述與實(shí)踐”“‘淫書(shū)的社會(huì)史”“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在地化”之外,三章接受史的內(nèi)容是我尤其關(guān)注的,即分別關(guān)注黑格爾、古騰堡、世界語(yǔ)在近代中國(guó)的閱讀與接受。
壹
文學(xué)領(lǐng)域的接受史,往往更多關(guān)注受者的主體意識(shí),所謂“文學(xué)中的影響關(guān)鍵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選擇,受者自身才決定取舍。”將其推演到文化領(lǐng)域,似乎也無(wú)不可。在這部書(shū)里,自然要考察作為現(xiàn)代中國(guó)在場(chǎng)的國(guó)人主體意識(shí),此處就以黑格爾接受史為例,我們來(lái)看看張仲民是如何來(lái)觀察這位德國(guó)哲人巨像在清民之際的接受狀況的,作者交待:
本章首先關(guān)注黑格爾哲學(xué)在清末中國(guó)的譯介情況,利用包括報(bào)刊文章、西洋史著作、人物辭典、學(xué)案、哲學(xué)譯著在內(nèi)的多種材料,揭示黑格爾哲學(xué)在清末中國(guó)更為多元和復(fù)雜的呈現(xiàn)情況,同時(shí)重點(diǎn)考察黑格爾哲學(xué)為時(shí)人所閱讀和接受的情形,并以章太炎對(duì)黑格爾哲學(xué)的解釋和批評(píng)為例,從接受政治角度討論黑格爾哲學(xué)作為思想資源為其使用的情況,以及這種使用的思想史意義。
因?yàn)榇饲耙延袟詈印⑧嚢矐c專(zhuān)著《康德、黑格爾哲學(xué)在中國(guó)》(首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出版,如此再作文,則必須別出手眼。果然并未讓人失望,作者從蔣介石、毛澤東這樣的政治精英的黑格爾興趣入手,追溯歷史,條分縷析,包括從學(xué)術(shù)史角度指出賀麟的失誤,在前人基礎(chǔ)上考證史實(shí)、修訂補(bǔ)缺,確實(shí)很有貢獻(xiàn)。但相較于系統(tǒng)地考辯史實(shí),讓我感到饒有興味的自然是,作者將個(gè)案選擇留給了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轉(zhuǎn)型期的重要學(xué)人,雖然并未能成為具有陳寅恪那樣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xué)人典范,但意義仍極為重要。他曾自詡以溝通協(xié)調(diào)“華梵圣哲之義諦,東西學(xué)人之所說(shuō)”為務(wù),其鵠的也不可謂不高,而如何落實(shí)到實(shí)踐層面,在知識(shí)結(jié)構(gòu)上真正融入梵印文化的根基,則大是難題,但考諸史實(shí),他確實(shí)曾努力向?qū)W,符合一個(gè)學(xué)人的純粹學(xué)術(shù)倫理觀。如謂不信,其弟子周作人(1885-1967)記錄的留日時(shí)代與老師章太炎一同學(xué)習(xí)梵文的經(jīng)歷可以為證:
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師也即到來(lái)了,學(xué)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兩個(gè)人。教師開(kāi)始在洋紙上畫(huà)出字母來(lái),再教發(fā)音,我們都一個(gè)個(gè)照樣描下來(lái),一面念著,可是字形難記,音也難學(xué),字?jǐn)?shù)又多,簡(jiǎn)直有點(diǎn)弄不清楚。到十二點(diǎn)鐘,停止講授了,教師另在紙上寫(xiě)了一行梵字,用英語(yǔ)說(shuō)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對(duì)太炎先生看著,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聽(tīng)了茫然。教師再說(shuō)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這才省悟,便辯解說(shuō),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師似乎聽(tīng)?wèi)T了英文的那拼法,總以為那是對(duì)的,說(shuō)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這梵文班大約我只去了兩次,因?yàn)橛X(jué)得太難,恐不能學(xué)成,所以就早中止了。
這段回憶非常重要,因?yàn)檫@反映出那代知識(shí)精英求知于世界的胸懷氣魄與具體路徑。更重要的是,作為一代國(guó)學(xué)宗師的章太炎,他的梵文學(xué)習(xí),更表現(xiàn)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里的“華梵二元”的重要關(guān)系,這是特別值得揭示的。不僅對(duì)印度文化如饑似渴,對(duì)西學(xué)也同樣認(rèn)真對(duì)待,譬如這里的化用黑格爾資源。在留日期間,是他對(duì)西學(xué)系統(tǒng)接觸的階段,所謂“既出獄,東走日本,盡瘁光復(fù)之業(yè)。鞅掌余閑,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shū)”。
關(guān)于黑格爾,作者在書(shū)中如是寫(xiě)道:
由日本渠道得來(lái)的黑格爾哲學(xué),可能加上嚴(yán)復(fù)、馬君武等人詮釋過(guò)的黑格爾哲學(xué),在經(jīng)過(guò)章太炎進(jìn)行了一番加工、改造后,自然已大非黑格爾哲學(xué)的原貌(原貌本就難求),而是融合或者說(shuō)混雜了老莊學(xué)說(shuō)、佛學(xué)、無(wú)政府主義、社會(huì)進(jìn)化論、日本因素、西方哲學(xué)等思想的結(jié)果。然而,這種融合與混雜,實(shí)際上正反映了章太炎是在以“六經(jīng)注我”的態(tài)度借黑格爾哲學(xué)等,甚至不惜賦予其原無(wú)之義或歪曲其原有之義,來(lái)闡發(fā)自己的政治主張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
這段分析頗為精到,值得展開(kāi)討論。一則我們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黑格爾及黑格爾哲學(xué)的東漸過(guò)程,乃是一個(gè)復(fù)雜僑易過(guò)程,是由眾多學(xué)人參與的接力賽,至少我們可以區(qū)分為留日、留英、留德學(xué)人等不同取徑和管道。章太炎的“六經(jīng)注我”策略,更使得這種知識(shí)輸入變成了一種絕非僅是單向度“西學(xué)凱旋”的面相,而成為了一種富有內(nèi)涵的“異文化博弈”過(guò)程,如果不是簡(jiǎn)單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話,那也確實(shí)存在某種“創(chuàng)造性對(duì)抗”的傾向。當(dāng)然如此立論,并非敢于忽略原像的規(guī)定性意義,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一代大哲的黑格爾,其理論體系具有摧枯拉朽的席卷之力,影響極為深遠(yuǎn)。但我們也要注意到,黑格爾本身思想的形成就是一個(gè)借鑒多種外來(lái)知識(shí)資源而強(qiáng)勢(shì)創(chuàng)生的過(guò)程,這其中就包括對(duì)中國(guó)古典知識(shí)的解讀和誤讀。所以,往后追溯,就必然發(fā)現(xiàn),即便作為大學(xué)者的個(gè)體也還不能窮盡思想的源頭,還有更高的一種核心力量存在,那就是觀念。觀念作為一種生命力更為久遠(yuǎn)、更具規(guī)定性意義的存在,具有超越性的價(jià)值,如此我們就消解了主體,追向更為廣闊的交叉系統(tǒng)和立體結(jié)構(gòu),也就呈現(xiàn)出了一個(gè)闊大的僑易空間。
貳
雖然章太炎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問(wèn)根基深厚,對(duì)佛教哲學(xué)也用力很深,但當(dāng)時(shí)他能與其他傳統(tǒng)學(xué)者區(qū)別開(kāi)來(lái),以莊子“齊物論”為基礎(chǔ),建立自己獨(dú)特的思想體系,很大程度上在于章太炎對(duì)包括黑格爾哲學(xué)在內(nèi)的西方哲學(xué)、西方思想的研讀與批判,盡管其中不乏誤解和誤用,但也難以掩蓋一個(gè)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大思想家的戛戛獨(dú)造之處,乃至他在對(duì)東西新學(xué)進(jìn)行批判性吸收與發(fā)揮過(guò)程中的主體性。
作者在書(shū)中寫(xiě)的這段話乍一看去有些矛盾,又強(qiáng)調(diào)其西學(xué)資源的重要,又表彰其本土大家的獨(dú)造,那么究竟想表達(dá)什么呢?其實(shí)在我看來(lái),這正是應(yīng)了陳寅恪那句話,“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lái)之學(xué)說(shuō),一方面不忘本來(lái)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隨著時(shí)代的進(jìn)步,文化的融合,知識(shí)的交流,完全閉關(guān)自守是不可能的,也是無(wú)法應(yīng)對(duì)挑戰(zhàn)的,但如何在進(jìn)入全球化與現(xiàn)代性的大格局中又始終堅(jiān)守自己的本位立場(chǎng),卻是一個(gè)極具難度的問(wèn)題,陳寅恪提供了基本思路,而這一點(diǎn)其實(shí)在前賢如章太炎、王國(guó)維等身上已經(jīng)有所體現(xiàn),是與他們的思想和實(shí)踐一脈相承的。事實(shí)上,章太炎以“俱分進(jìn)化論”來(lái)反對(duì)黑格爾式的進(jìn)化論確實(shí)也是很見(jiàn)功力的,所謂“不破不立”,同時(shí)也是“不受不立”,一方面要接受對(duì)方的有效知識(shí)資源,另一方面也能擺脫對(duì)方的既定框架(當(dāng)然是出于學(xué)理,而非無(wú)中生有),建構(gòu)起自身的理論邏輯來(lái)。當(dāng)然,這其中的誤讀、誤解、誤用,也需要仔細(xì)加以辨析,并不可隨意置評(píng)。
當(dāng)初黑格爾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閱讀和接受,其實(shí)也充滿了這種“誤會(huì)”,黑格爾在論述道家思想的時(shí)候,就大量引用了法國(guó)漢學(xué)的始作俑者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的論述:
據(jù)雷繆薩說(shuō),“道”在中文是“道路,從一處到另一處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體、原理的意思。綜合這點(diǎn)在比喻的形而上的意義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進(jìn)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與基礎(chǔ)。“道”(理性)的成立是由于兩個(gè)原則的結(jié)合,像易經(jīng)所指出的那樣。天之道或天的理性是宇宙的兩個(gè)創(chuàng)造性的原則所構(gòu)成。地之道或物質(zhì)的理性也有兩個(gè)對(duì)立的原則所構(gòu)成。地之道或物質(zhì)的理性也有兩個(gè)對(duì)立的原則“剛與柔”(了解得很不確定)。
在這里,我們看出主流思想家的致思之路,就是對(duì)邊緣學(xué)科的征引和依賴(lài),因?yàn)椴蝗绱藷o(wú)以支撐他們的世界敘述和整體建構(gòu)。畢竟,知識(shí)是一個(gè)系統(tǒng)性結(jié)構(gòu),必須通過(guò)層層疊疊的細(xì)部知識(shí)的累聚,才可能逐漸覆蓋起一個(gè)整體性的大廈。如此,則漢學(xué)家的意義凸顯出來(lái),即他們不是簡(jiǎn)單的異域(此處特指中國(guó))知識(shí)的工作者,而是通向本土主流思想家的重要橋梁。正是借助漢學(xué)家的通道,黑格爾對(duì)中國(guó)的基本元典都有所了解:
中國(guó)人存有許多古書(shū)和典籍,從中可以了解它的歷史、憲法和宗教。吠陀和摩西紀(jì)傳是類(lèi)似的書(shū)籍,荷馬史詩(shī)同樣如此。中國(guó)人把這些書(shū)稱(chēng)為“經(jīng)”,作為他們一切學(xué)術(shù)研究的基礎(chǔ)。《書(shū)經(jīng)》包含著歷史,敘述了古代帝王的政府,并且發(fā)布了由這個(gè)或者那個(gè)帝王制定的命令。《易經(jīng)》由許多圖形組成,被看作是中國(guó)文字的基礎(chǔ),也被視為中國(guó)深邃思想的基礎(chǔ)。因?yàn)檫@部書(shū)是從一元和二元的抽象化開(kāi)始的,然后敘述了這些抽象思想形式的具體存在。最后是《詩(shī)經(jīng)》。這是一本各種格律的、最古老的詩(shī)歌的集錄。古時(shí)候,一切高級(jí)官吏都必須帶著他們地區(qū)當(dāng)年寫(xiě)作的所有詩(shī)篇去參加年節(jié)。坐在科場(chǎng)中央的皇帝是這些詩(shī)篇的評(píng)判員。凡是被賞識(shí)的詩(shī)章均得到公眾的贊同。除了這三部特別受到敬重并得到深入研究的經(jīng)典著作外,還有其他兩部不太重要的典籍,即《禮記》(也叫作《禮經(jīng)》)和《春秋》。《禮記》記述了習(xí)俗和對(duì)皇帝以及官吏的禮儀,并有附錄《樂(lè)經(jīng)》,專(zhuān)門(mén)論述音樂(lè)。《春秋》是孔子所在的魯國(guó)的史記。這兩部書(shū)是中國(guó)歷史、風(fēng)俗和法律的基礎(chǔ)。
這些信息雖然不盡正確,但可以讓我們看到黑格爾對(duì)中國(guó)元典的了解情況和自己的獨(dú)特理解。譬如對(duì)于《易經(jīng)》,黑格爾多次提及:
《易經(jīng)》里畫(huà)著某些表示基本形狀和基本范疇的線條,所以這部書(shū)也被稱(chēng)為命運(yùn)之書(shū)。這些線條的組合被賦予某種意義,預(yù)言就以此為基礎(chǔ)被演繹出來(lái)。或者把許多小棍扔到空中,根據(jù)它們降落的方式來(lái)預(yù)先決定命運(yùn)。凡是我們認(rèn)為是偶然的東西以及自然的聯(lián)系,中國(guó)人都試圖用巫術(shù)來(lái)推導(dǎo)或者實(shí)現(xiàn)。所以這里也表現(xiàn)了他們的愚昧無(wú)知。
這種似乎輕松推出的結(jié)論,顯然是既不嚴(yán)謹(jǐn)也無(wú)道理的,所以難怪錢(qián)鍾書(shū)就曾批評(píng)黑格爾說(shuō):“無(wú)知而掉以輕心,發(fā)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tài)慣技,無(wú)足怪之。”這也同樣是我們?cè)诿鎸?duì)大哲時(shí)需要注意的面相。但至少我們必須承認(rèn)的是,作為大學(xué)者的黑格爾,求知視域是廣博的,他在那個(gè)時(shí)代就注意到邊緣學(xué)科如漢學(xué),還是法國(guó)漢學(xué)家的工作,并援以為自身的知識(shí)資源,能體現(xiàn)出那代德國(guó)古典知識(shí)人的心胸和氣象;當(dāng)然具體到具體認(rèn)知過(guò)程和水平,這需要另行討論。這或許遠(yuǎn)離張君是著的范圍,但之所以對(duì)這一面相稍作補(bǔ)充,乃基于知識(shí)聯(lián)通的理念,因?yàn)槲覀兯鎸?duì)的是一個(gè)整體的世界,所謂“一旦某些知識(shí)統(tǒng)一到一定的程度,我們就可以了解我們是誰(shuí),以及我們?yōu)槭裁磿?huì)在這里”。如果我們引入僑易史的視角,即考察作為僑易主體的黑格爾及其哲學(xué),是如何通過(guò)翻譯、閱讀、接受等過(guò)程由“西學(xué)輸入”轉(zhuǎn)向“中國(guó)創(chuàng)造”,甚至再進(jìn)一步牽連出黑格爾乃至德國(guó)古典精英的中國(guó)知識(shí)場(chǎng),或可有更為精彩的發(fā)現(xiàn)。
叁
影響研究固然重要,但僅僅就影響論影響不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目的,更重要的還是如何能追本溯源,窮其問(wèn)題之根本,即回到元觀念的“梁柱架構(gòu)”,在問(wèn)題的起始處進(jìn)行追問(wèn),尋求“致思之源”,這或許才是學(xué)者的真正使命。所以,我們考察黑格爾進(jìn)入現(xiàn)代中國(guó)的歷程,觀察其閱讀史、接受史、影響史、變易史等,也是與時(shí)代語(yǔ)境密切相關(guān),嚴(yán)復(fù)雖首發(fā)其聲,馬君武等人繼而跟進(jìn),章太炎更在思想上有所發(fā)覆,所以不同渠道的留學(xué)人對(duì)引進(jìn)西學(xué)(哪怕是不同的國(guó)族對(duì)象)是非常重要的,而其路徑也值得區(qū)分。所謂“從全球范圍內(nèi)的現(xiàn)代進(jìn)程來(lái)看,把特殊主義由一種文化論說(shuō)轉(zhuǎn)化為國(guó)家行動(dòng)的原則并帶來(lái)多重后果的實(shí)驗(yàn),首先是在德國(guó)完成的。德意志現(xiàn)代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西方現(xiàn)代性不具普遍性,德意志應(yīng)當(dāng)走自己的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xué)》中所強(qiáng)調(diào)的日耳曼文化的使命,正是從這個(gè)意義上可以更為深刻的理解。日后賀麟、王玖興等持續(xù)接力,開(kāi)展了非常重要的黑格爾著作漢譯史工作,甚至連德語(yǔ)文學(xué)的學(xué)人如陳銓也介入了這個(gè)過(guò)程。其弟子輩梁志學(xué)又薪火相繼,繼續(xù)推動(dòng)《黑格爾全集》的漢譯工程。這其中涉及黑格爾東漸的復(fù)雜的翻譯、紹介、閱讀、接受與形變,甚至是博弈、創(chuàng)生、循環(huán)等,都是非常有意思與有意義的現(xiàn)象,是否僅僅就是“種瓜得豆”,還待細(xì)加探究。但張仲民所實(shí)踐的這條閱讀史研究的實(shí)證路徑,無(wú)疑是非常有價(jià)值的,值得充分肯定。
此外,雖然作者考證已非常詳盡,但仍難免偶有疏失,譬如將Li Qiang注成Li Qing。而全書(shū)沒(méi)有索引,查找使用起來(lái)未免不便。當(dāng)然瑕不掩瑜,作為一部由若干深度個(gè)案研究而組成的閱讀史著作,此書(shū)的學(xué)術(shù)推進(jìn)意義是顯而易見(jiàn)的,值得仔細(xì)玩味。
(作者系同濟(jì)大學(xué)特聘教授,文化史與文化哲學(xué)博士生導(dǎo)師,兼人文學(xué)院院長(zhǎng);全國(guó)歌德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僑易》學(xué)術(shù)集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