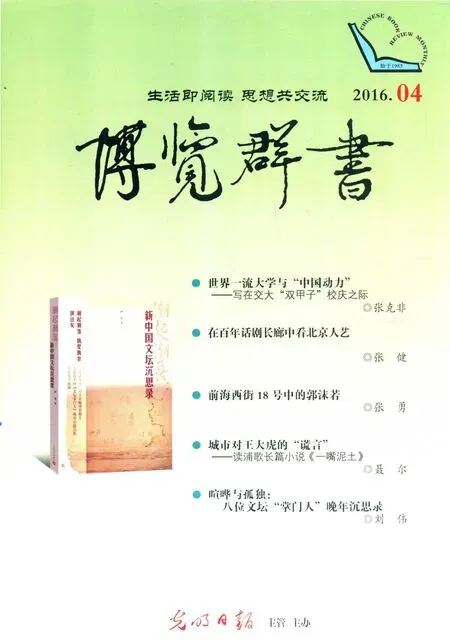在《創(chuàng)造周報》的背后
泉涌

1923年5月1日《創(chuàng)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中就發(fā)出了《創(chuàng)造周報》出版的預(yù)告,這預(yù)示創(chuàng)造社同人們又要以新的面貌出現(xiàn)于讀者的面前。《創(chuàng)造周報》是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主要刊物之一,它在1923年5月到1924年5月整整一年的時間里,用52期思想論說贏得了廣大青年讀者的注意。這份刊物究竟在當(dāng)時火到何種程度呢?“《創(chuàng)造周報》一經(jīng)刊發(fā)出來,馬上就轟動了全社會,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四馬路泰東書局的門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擠滿,從印刷所剛搬運來的油墨未干的周報,一堆一堆地為讀者搶購凈盡,訂戶和函購的讀者也陡然增加,添人專管這些事。”
在《創(chuàng)造周報》創(chuàng)辦伊始,時為創(chuàng)造社三駕馬車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dá)夫是將它與《創(chuàng)造》季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它創(chuàng)刊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借助其周期短、篇幅小的特點以彌補《創(chuàng)造》季刊不足以反映時局重大變化,以及季刊中的文章引起的一些論爭也常常不能得到及時答辯的缺憾,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就定位于刊發(fā)以具有“短、平、快”特點的思想評論、文藝批評為主,而創(chuàng)作和翻譯則退居為其次。《創(chuàng)造周報》的發(fā)行量一直維持在3000—6000之間,在當(dāng)時普遍注重創(chuàng)作的情況下,以翻譯和評論為主的《創(chuàng)造周報》能夠有這樣的銷售業(yè)績已經(jīng)十分不容易了,這從另一方面足以看出前期創(chuàng)造社所造成的巨大社會影響,借此前期創(chuàng)造達(dá)到了它的全盛期。
壹
如果仔細(xì)翻閱《創(chuàng)造周報》我們能夠明顯地感覺到,相較于《創(chuàng)造》季刊等當(dāng)時文壇上的重要期刊來講,它并沒有什么特殊的編輯策略,版面的設(shè)計相當(dāng)簡單,編排也非十分考究,內(nèi)容上的錯誤相對于《創(chuàng)造》季刊來講只能說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那么多年青的讀者對之趨之若鶩呢?創(chuàng)造社給我們最鮮明的印記無疑是其以郭沫若、成仿吾、郁達(dá)夫三人為核心的同人作家群體,《創(chuàng)造周報》共出版52期,共有文章201篇,在這些文章中郭沫若有72篇、成仿吾有30篇,郁達(dá)夫有13篇,他們?nèi)齻€人的文章總數(shù)大約有三分之二,不僅如此他們還輪流編輯,爭作頭一篇文章,這也是他們創(chuàng)辦同人雜志的初衷和目的。
所謂的同人雜志,就是由趣味相投的作家集合在一起,但他們又不是結(jié)黨營私,而是相互支持,互通有無,就共同關(guān)注的某個問題發(fā)出同一種聲音,對別人的責(zé)難迅速作出相同的回應(yīng)。同人雜志的好處是目光遠(yuǎn)大,胸襟開闊,但它也有非常致命的弱點,那便是缺乏穩(wěn)定的財政支持,并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變故,當(dāng)即“人亡政息”。以郭沫若、成仿吾、郁達(dá)夫三人為核心的同人雜志——《創(chuàng)造周報》就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些特點,特別是作為核心之核心的郭沫若與《創(chuàng)造周報》更是形成了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通過考察《創(chuàng)造周報》中郭沫若所發(fā)表論文的數(shù)目及文章的類型便可以明顯地看出郭沫若與《創(chuàng)造周報》的密切關(guān)系。郭沫若的文章一直持續(xù)到第40期以前,而且僅僅就在第20期沒有發(fā)表文章外,8、11、12、13、15、28、29、34、35、36、37、38、39期是1篇文章外,其余的都在兩篇以上,而成仿吾、郁達(dá)夫都沒有能夠發(fā)表如此數(shù)量的文章。而在41—52期中僅僅就41、42、47與52期有1篇文章出現(xiàn)。這較之前40期有了天壤之別。
從文章的內(nèi)容與體裁來看,前40期郭沫若的文章主要是發(fā)刊詞、翻譯、詩歌、論說、通信、答辯、小說創(chuàng)作、雜感、寓言、介紹、研究、隨筆等體裁的文章,而40期后的《周報》中郭沫若在有限的4篇文章中,僅僅就是3篇小說與1篇通信而已,與前一階段十幾種體裁相比,有了相當(dāng)大的變化。
從文章所涉獵的范圍來看,前40期主要的關(guān)鍵詞是國家、藝術(shù)、革命、創(chuàng)造等等,而后期的3篇小說創(chuàng)作完全可以等同與郭沫若自我生存軌跡地生動寫照。從這也似乎在預(yù)示著郭沫若在1923到1924年間的心路歷程。
郭沫若的這些個人的行為與《創(chuàng)造周報》的興衰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40期左右恰恰是《創(chuàng)造周報》由輝煌的頂點走向衰退直至停刊的開始。而《創(chuàng)造周報》創(chuàng)辦這52期也即是1923年5月到1924年5月這段時間內(nèi),恰好也記錄了郭沫若由日本回到國內(nèi)從事文學(xué)活動由極力吶喊到無奈返回日本的整個心路的歷程。一個人的命運的抉擇與一份刊物的興衰發(fā)生了如此緊密的聯(lián)系,這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
郭沫若與《創(chuàng)造周報》建立起一種良性的連貫性,即版面之間的連續(xù)性。版面連貫性應(yīng)主要強調(diào)本體性整體性和時間性整體兩個層面,特別是內(nèi)容豐富、版面構(gòu)成元素復(fù)雜的期刊,策劃者尤其要注意利用圖片等手段吸引讀者的視點,使讀者閱讀時有連續(xù)翻閱下去的沖動。
在《創(chuàng)造周報》的前42期中,僅僅就第20期和第40期中沒有郭沫若的文章外其余的每期都至少有郭沫若的文章出現(xiàn),其中有5期中有3篇文章,有20期中有2篇文章。而《創(chuàng)造周報》每期中包括通信、啟示等非創(chuàng)作性的部分在內(nèi)最多的也就5篇文章,這樣看來郭沫若至少在前42期絕對是《創(chuàng)造周報》作家同人的核心。但是,從第43期到第52期終刊的10期內(nèi),郭沫若僅僅只在第44期和第47期發(fā)表了兩篇小說以及第52期的一封通信。
郁達(dá)夫的13篇文章中的12篇也大多集中于前24期,而剩余的1篇則出現(xiàn)在第46期上。成仿吾的30篇文章中有13篇出現(xiàn)于前18期中,10篇出現(xiàn)于后10期中,而僅僅有7篇文章出現(xiàn)于從第19期到第42期的23期刊物之中。從第47期起郭沫若離開上海去了日本,《創(chuàng)造周報》就交由成仿吾來編輯和主編,因此在后10期中成仿吾的文章突然增多就不足為奇了,而從《編輯余談》我們可以清晰的體味出成仿吾也是在勉力而為之,只是為了完成歷史的使命而已。
這樣看來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郭沫若前期的編輯,就不會有《創(chuàng)造周報》的成功,而郭沫若的離去對于它的影響是致命的,這兩者之間唇亡齒寒的關(guān)系便顯而易見了。
貳
辦刊物難,辦周報類的刊物更難,主要的原因是如下:
每星期就要見面一次,更貴精而不貴多,要使讀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處,每篇看完了都覺得時間并不是白費的。要辦到這一點,不但內(nèi)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動最經(jīng)濟的筆法寫出來。要使兩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義,敵得過別人的兩三萬字作品。寫這樣文章的人,必須把所要寫的內(nèi)容,徹底明了,徹底消化。然后用敏銳活潑的組織和生動雋永的語句,一揮而就。這樣的文章給予讀者的益處顯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讀者省下了許多搜討和研究的時間,省下了許多看長文的費腦筋的時間,而得到某問題或某部門重要知識的精髓。(《韜奮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05)
《創(chuàng)造周報》能夠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主要的是他們就擁有了這樣一位“寫文章的人”——郭沫若。
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周報》上刊發(fā)的文章不僅數(shù)量眾多,而且內(nèi)容精煉,富有強烈的戰(zhàn)斗性和鼓動力。《我們的文學(xué)新運動》是郭沫若刊發(fā)在《創(chuàng)造周報》第3號的一篇重要的論述文,文章開篇他便吹響了戰(zhàn)斗的號角,直陳“中國的政治生涯幾乎到了破產(chǎn)的地位”,“我們暴露于戰(zhàn)亂的慘禍之下,我們受著資本主義這條毒龍的巨爪的揉弄”,進(jìn)而就呼吁到“我們要如暴風(fēng)一樣喚號,我們要如火山一樣爆發(fā),要把一切的腐敗的存在掃蕩盡,燒葬盡,迸射出全部的靈魂,提呈出全部的生命”,“我們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彈來打破這毒龍的魔宮”,“要打破從來的因襲的樣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現(xiàn)”。我想就是今天的讀者閱讀完這些激昂的字句后,也會迸發(fā)出熱火灼燒的情感,更何況在“五四”新文學(xué)發(fā)生的歷史現(xiàn)場呢?
難能可貴的是,郭沫若不是就僅僅只刊發(fā)《我們的文學(xué)新運動》一篇戰(zhàn)斗檄文,類似這樣的充滿火藥味的批評文字幾乎貫穿了《創(chuàng)造周報》的始末。如《藝術(shù)的評價》《神話的世界》《批評——欣賞——檢察》《自然與藝術(shù)》《藝術(shù)家與革命家》《文藝上的節(jié)產(chǎn)》《瓦特·裴德的批評論》等一系列文章,正是郭沫若的這些文章,《創(chuàng)造周報》一下子便抓住了充溢著青春叛逆激情的“五四”青年的內(nèi)心,使他們成為《創(chuàng)造周報》狂熱的擁躉者,“青年作者的投稿不斷增加,刊物的影響不斷擴大。每到星期六,總有不少讀者在泰東書局的店頭等候新出版的《周報》。案頭上堆積得厚厚的新刊物很快就賣光了”(《鄭伯奇研究資料》,山東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P116),《創(chuàng)造周報》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他們走向文化戰(zhàn)斗中心的舞臺。
叁
郭沫若通過《周報》奉獻(xiàn)給讀者最好的禮物就是對于尼采的著作《查拉圖司屈拉如是說》的譯介。正如郭沫若在翻譯之前說:
尼采的思想前幾年早已影響模糊的宣傳于國內(nèi),但是他的著作尚不曾有過一部整個的 翻譯。便是這部量有名的《查拉圖司屈拉》,雖然早有人登了幾年的廣告要移譯他,但至今還不見有譯書出來。我現(xiàn)在不揣愚昧,要吧他從德文原文來移譯一遍,在本周報尚逐次發(fā)表,俟將來全部譯竣之后再來匯集成書。
這部書的翻譯一直持續(xù)到第39期,譯到第二部第四節(jié)為止。而且郭沫若在第30期《創(chuàng)造周報》也即郭沫若將此書第一部翻譯完成之后,專門撰寫了一篇題目為《雅言與自力——告我愛讀〈查拉圖拉屈拉〉的友人》的文章。在此文章的剛開始部分郭沫若說:
我把《查拉圖拉屈拉》的第一部譯完之后,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是難解,要求我以后加些注譯。仿吾也勸我在繼譯第二部之前,不妨先把尼采的思想,或者《查拉圖拉屈拉》全書的真諦,先述一個梗概,以便利于讀者。我在這一兩禮拜來便停止了移譯的工作,想依仿吾的勸誘,先把我對于《查拉圖拉屈拉》的見解略述出來以當(dāng)注譯,但我再四忖度,在一種著作,或者一人的主要作品,尚未全部介紹于讀者之前,便先把該作品或該作者的思想加以評究,這在授受兩方,不僅是勞而無功,而且會生意外的障礙。
…… ……
我是一面鏡子,我的譯文只是尼采的虛像;但我的反射率恐不免有亂反射的時候,讀者在我鏡中得一個歪斜的尼采像以為便是尼采,從而崇拜之或反抗之,我是對不住作者和讀者多多了。一切的未知世界,總要望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勞力去開辟,我譯一書的目的是要望讀者得我的刺激能直接去翻讀原書,猶如見了一幅西湖的照片生出直接去游覽西湖的欲望。我希望讀者不必過信我的譯書,尤不必伸長頸項等待我的解釋呢。”(《創(chuàng)造周報》第30號)
由此也顯示了郭沫若對《創(chuàng)造周報》廣大讀者的尊重,和以讀者為重的濃厚責(zé)任心。
為了滿足讀者更高層次文化閱讀的需要,郭沫若還發(fā)表了一系列學(xué)術(shù)研究論文,如《中國文化之傳統(tǒng)精神》《論中德文化書》《讀梁任公〈墨子新社會之組織法〉》《惠施的性格與思想》《整理國故的評價》《古書今譯的問題》《國家的與超國家的》《天才與教育》等。觀點清晰、深入淺出是郭沫若以上論文的共同特點,提出明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途徑更是郭沫若文章的特色,他在論述有關(guān)國家主義的概念時,就鮮明地提出:
我們中國本來是國家觀念很淡漠的國家,在十幾年前,軍國主義正在世界上猖獗的時候,有許多人士很以此為可恥,而大提倡愛國。好在我們素來的傳統(tǒng)精神,是遠(yuǎn)的目的是在使人類治平,而不在家國。我們古代的哲人教我們以四海同胞的超國家主義,然而同時亦不離棄國家,以國家為達(dá)到超國家的階段。
通過這樣的論述,就把復(fù)雜的國家主義闡釋的清晰明了,讀者也能領(lǐng)悟理解。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對于讀者的重視,這也是《創(chuàng)造周報》為什么能夠贏得讀者關(guān)注的一個重要原因。
郭沫若與《創(chuàng)造周報》互相成就了彼此,郭沫若決定了《創(chuàng)造周報》的興衰成敗,而《創(chuàng)造周報》也因其強大的傳播效力,使郭沫若橫刀躍馬于“五四”新文壇,迅速成為了一顆閃亮的文化巨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郭沫若紀(jì)念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