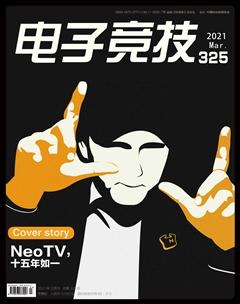注定失敗的電競教育?
楊直
看起來,電競教育走進了一個死胡同。
已經有許多自媒體報道了“第一批”電競專業學生的窘境。網管、賣電腦……經過了幾年的學習,大部分人都沒能進入類似賽事內容公司、俱樂部等心儀的電競企業。
從教育部將電競認證為一種專業,到2017年的專業熱,再到2018年的電競教育熱,幾年過去了,電競教育沒能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可能很多人會問,問題出在哪?
宏觀地看,電競教育由幾部分構成,大體上遵循現在已有的體系,包含了學歷教育、職業教育、短期技能培訓、選手培養等等。
其中,學歷教育、職業教育都有著成熟的體系。每個專業的開設、建設都有既有的、可借鑒的路徑,有被驗證了的、科學化的規律支撐。在這方面,不管是專業的設立,還是學科的建設、專業的發展,只要已有的成熟專業相比,我們就會得到如下結論:任何以商業為主要目的,忽略規律,想要加速或者省略這個過程的人,無論其組織專業者,還是參與學習相關專業的人,都注定失敗。
而選手培養,大體上類似于傳統體育的運動員培養。現階段,電競的選手培養仍然談不上“培養”二字,更像一種“大海撈針”式的存在。戒網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今天,我們不妨把討論的重點放在貼近應用場景的短期技能培訓上。這是一種更貼近認知的電競教育。完全由市場上的用人需求驅動,教育目標瞄準了業務操作層面的專業技能。
決定了這種短期技能培訓生源狀況的原因無外乎內部和外部兩種。外部的原因即是勞動力市場的供需情況,內部的原因則在于這種培訓是否有價值。
先說結論,外部環境是否變得更糟是一個無法確定的問題。的確,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里,電競賽事大多“如約”舉行。但疫情仍然對電競產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一些小而獨立的電競企業破產,一些大型的電競企業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員。
但這并不能說明整個市場的情況。一個不太準確的描述是,只要賽事甚至是相關落地活動的密度在增長,電競企業就仍然存在不小的用人需求。區別在于,這種需求是即時的,還是潛在的。
而且,如前文所述,這種用人需求很不穩定。用一個例子簡單解釋,一個結論是,牛市里,金融企業會“不惜成本”的大量招聘,但在熊市里,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裁掉很多人。這種明顯隨著市場變動而變動的用人需求,放在電競企業身上,依然成立。
理論上看,每一個被關聯的企業都會為一個賽事配置一定的人力。當超過了一定界限時,企業就得雇傭新的員工。理想的情況下,可以將企業視為由一個個小團隊組成。每個賽事對應一個或幾個團隊。

2020年,因為疫情的確一些賽事或者活動的線下落地密度下降了,于是一部分人被裁掉了,但一旦外部條件回歸正常,賽事內容公司很可能招聘回同等數量甚至更多的人。
再考慮到勞動市場上的博弈,所以我們才說,很難說用人需求緊縮了。另一個更直觀的例子是,很多企業仍然在不間斷地進行小規模的招聘。
因此,問題很可能出現在電競教育——也就是短期技能培訓本身。
因為發展時日尚短,電競產業確實長久以來存在著人才缺口。雖然這催生了電競教育,但并不意味著產業會給這種試驗性的教學買單。正如越來越多從業者承認,起碼到目前為止,電競都稱不上是一個高門檻的行當。
只要稍微拆解電競本體,就能理解這個結論。
首先,我們要把游戲從電競里拆出去。雖然電競培訓設置了很多這方面的課程,但起碼在“專門設計一款電競游戲”成為現實之前,電競專業的學生和這部分工作都不搭邊。
剩下的就是電競賽事了。
負責賽事策劃、執行的賽事內容公司一直是產業里的用人大戶,但問題在于,這部分需求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目前從內容上看,大部分電競賽事被拆成開幕式和比賽兩部分。負責前者的通常是一個上百人的大團隊,其中大部分人來自于傳統內容制作機構,比如電視臺。從結果看,或者說起碼這些招聘機構認為:不懂電競沒關系,只要帶著過硬的專業技術,邊做邊學就行。
而且,內容制作本身是一個極其依賴實踐的專業技能,大部分人都處在邊干邊學的狀態里。傳統的內容制作本身也有與之相匹配的專業,比如導演系。那么那些專門培訓專業技能的電競學校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
其實,這些所謂的電競學院大多由從業者發起。他們往往結合自身的從業經驗傳輸自己“悟出來”的專業技能,他們本身也是學院的“招牌”。但問題在于,這些人并不具備相應的專業背景。如果是企業內部的培訓,這種形式的教育也許還有意義,但如果是針對大眾開設的培訓班,那么必然是立不住腳的。
這些培訓能教會學生過硬的專業技術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看上去就只有負責賽事的團隊需要電競專業的學生。這確實是和電競專業最對口的崗位,但很遺憾,用人數量很少。當下某業內頂級賽事內容公司,支撐其上百人內容團隊的是一個只有10多個人的賽事部門。
那么在內容之外呢?賽事的運營、商業化似乎都需要大量的人。但一個簡單的邏輯是,這部分崗位都和負責開幕式的團隊一樣,用人需求不會被“電競”框定。
對于媒體、俱樂部等其他產業鏈上的環節,我們就不贅述了,基本上和賽事內容公司符合相同的邏輯。
說回今天的核心問題,電競專業的迷茫恰恰來自于其自身。或者更確切地說,源于推動其發展的人。
籠統稱呼上的電競教育被看好的原因,并非因為它事實上作為一個可以被教授的專業存在。而是它可以利用電競教育的噱頭賺快錢。
我們不否定電競學歷教育、職業教育、選手培養等人才培養方式的探索,但這種探索的出發點一定是對的,且一定是符合現代教育自身的運行邏輯的。

學歷教育基于學科自身的發展程度,總結出學生需要具備哪些理論知識,如何設置更科學的進階式培養……2017年的時候,雜志曾經討論過“電競專業”應該以何種方式存在。一種是獨立的專業,另一種則是依附在已有專業下,成為一個方向。
雜志之所以提出后者可以成為一個嘗試的方向,考慮的恰恰是電競教育可以借助已有學科成熟深厚的根基。
同樣,職業教育需要的是對職業清晰的認定,教授必備的職業技能、職業守則,在學習的過程里,幫學生設計清晰的職業路徑……
而選手培養更要科學化,不然只是在浪費一個個年輕人的未來。
探索電競人才的培養和教育本身沒問題,問題出在那些有教育行業背景,明知規則卻置若罔聞的人,也出在那些將教育單純視為一門生意的電競從業者們。
最后,也奉勸一些想進入電競領域的年輕人。把興趣變成職業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結果也不一定盡如人意。不管電競教育最后以何種方式存在,起碼在未來的幾年內,它都將被迫停留在摸索建設的階段,從各個方面看,它都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