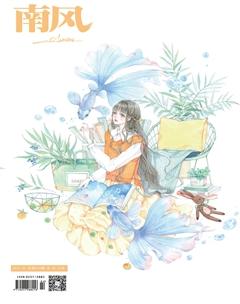寫給父親母親的情詩
作者簡介
惠子,本名覃儒方,苗族,1963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詩刊》、《人民文學》、《民族文學》、《星星詩刊》《山花》等全國50余家核心期刊發表詩歌作品1000余首,著有詩集《孤獨的石榴》、《最后的我》、《紫色咖啡》、《惠子抒情詩選》四部,有作品入選《中國詩歌年鑒》《中國當代漢詩年鑒》《星星詩刊·四十年詩選》等30種選本,偶有獲獎,有作品翻譯成英、日等多種文字,現就職于貴州省扶貧辦
編者按:
在惠子的字里行間中,聞得到泥地里綻放的親情,望得見金黃稻穗里勞作的父親,聽得見靜謐夜光中母親的歌謠。詩詞間無不喚醒著那份早已沉睡的血脈情感,記住那份叮嚀,記得那份來世也報不完的恩情,在這情人節將至的二月,通過作者筆下的思念、緬懷,別讓一切成憾,給父母說聲感謝,說聲辛苦。
我喜歡在飛機上看書,而且多半看的是閑書。因此,每次出差我都會在包里放上一本詩歌雜志。這個習慣已堅持了二十多年,且二十多年不輟。因為每一次的出行我都會在雜志的某一頁或某幾頁密密麻麻寫上一些分行的文字,而后將這些文字串成一首首美麗的詩行。
也許因為工作的關系,平時沒有更多的時間讀書,也許純粹是懶惰使然,但一上飛機,我就像選手進入賽場,會迅速進入一種亢奮狀態,而一旦拿上書本,我則旋即進入一種鳥語花香而又與世隔絕的狀態,靈魂收斂起來,專注于閱讀,專注于一粒粒充滿靈性的文字,她們會帶你去你之前完全無法預知的領域,去見你想見的人,看你想看的花,嘗你想嘗的果。無論菩提,無論因果,無論對錯。一任窗外喧囂,白云蒼狗,而我心寂然,獨自住進書里、句里、詞語里,或如老僧入定,枯坐如木,或如童子般天真,只是掩了心門,將欣喜隱藏于心,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就這樣下來,幾經輾轉,幾首或幾組習作就成了。然后連同雜志一起放進書架的某個角落,或三兩月,或半年,或一載,待徹底忘卻,復將其翻將出來,再過上一遍,或增或減,或留或棄,一首,幾首,或幾組習作就這樣成了。有時倒回來看,自己都要給自己點贊。甚至在心里嘀咕:老覃真是太有才了!怎么會有那么多奇思妙想?這不是神來之筆嗎?自嘲之后復自滿,自滿之后復自信。
就這樣,在我逾三十年業余寫作生涯中,在我已經在國內外上百家報刊雜志刊發的1000余首(組)中,毫不夸張地說,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旅途中的產物。而自從有條件乘飛機以后,飛機則成了我主要的創作場所。印象深的有兩次,這兩次是一悲一喜,復悲復喜,讓我終生難忘,甚至改變了我某些生活習慣。
一次是2010年春季赴新加坡南洋大學培訓,時間長達一個半月。在這一個半月的時間里,被新加坡濃郁的熱帶風情、海天一色的城市景色以及干凈、活力、法治、蓬勃向上的城市國家形象所吸引,相繼草成16首(組)隨筆型的詩作,在從新加坡返回廈門的途中,我一直在修改、過濾、篩選,總的對這幾組充益熱帶風情的清新淡雅的小詩頗為滿意。孰料,樂極生悲,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碰到了刪除鍵,所有的心血瞬間附之東流。在那一瞬間,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手腳。到底怎么了?怎么就鬼使神差地碰到了刪除鍵呢?那不是還有個確認鍵嗎?我的神一樣的手指又是如何碰到的呢?一切都來得太突然,而一切又都像設計好了一樣。我突然間像被施了魔法被定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詞:完了,完了,完了。待我回過神來復去找尋根本就不存在的"恢復鍵"企圖恢復,顯然一切都是徒勞。回到遵義,我火急火燎找到若干家手機修理店,甚至電腦專家,連比帶劃,一遍一遍復述作品丟掉的過程及訴求,無奈,企圖"恢復"的愿望終成泡影。為此,我對手機、電腦這種現代的書寫工具"愛屋及烏"地恨之入骨,甚至痛恨發明電腦及手機輸入法的人,咕噥說這個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電腦!
還有一次發生在最近。2016年4月1日,我從貴陽去北京出差。一上飛機,我照例將隨身攜帶的《星星詩刊》2016年第三期上半月刊翻閱起來,翻著翻著,我大腦里突然涌現出逝去的母親的形象。可能正好是頭天晚上夢見母親的緣故,我一口氣在《星星詩刊》內頁寫下了《我總在月白風清的夜晚喊母親回家》和《吊母親》兩首。寫完,意猶未盡,飛機仍在空中疾馳。這時,一束陽光透過機窗玻璃穿進來,很真實地照在我臉上,仿佛母親的目光和叮嚀。于是,我繼續在《星星詩刊》的另一內頁寫下了《懷念》一首。剛好落筆,客艙中傳來空乘小姐甜美的聲音:各位旅客,歡迎您選乘天河聯盟南航客機,謝謝您的支持,祝您愉快,希望下次旅途再會。于是,我迅速折轉到后面的行李架上拿起行李,隨著裹挾的人流走下飛機舷梯。當走出機場,步入機場大廳,我忽然想起涂有詩歌草稿的《星星詩刊》和一支閱讀用的紅筆落在了座位上。我迅疾折返找到機場工作人員,詢問能否返回機上尋找?工作人員明確告之不行,只能到機場失物招領處查詢。我火急火燎跑到實物招領處,手腳并用,繪聲繪色向工作人員描述失物遺失情況。工作人員隨即與該機乘務員聯系,得到的回復是:查無此物!發了一會呆,我不甘心,又將丟失的情景重新描述一遍,再次懇請工作人員幫助查找,并愿意支付相關傭金云云。結果:仍然是石沉大海。回到賓館,我又反復多次電話詢問,答復還是"沒有找到"。我絕望,自責,懊惱,無助。我遷怒于機場工作人員的不負責任,遷怒于國人劣根性的"順手牽羊",甚至遷怒于同事好心的位置的"調來調去"。遂寫"罪己詔":要長記性,要有耳性,凡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以示警醒!
是日晚,我把自己交給了不眠之夜。像第一次一樣,我試圖通過回憶、搜索,將失去的詩行找回來,結果當然仍是徒勞。"自信人生二百年"和記憶力超群的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找回一些記憶的碎片,充其量是一些"像詩"的句子。詩歌不是記憶的復制,而是靈感的產物,是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遇到的對的事物和對的語言。記憶可以找回來,而靈感是轉瞬即逝。就像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人永遠也不可能產生兩次相同的靈感。所以,當第二天機場工作人員告知我那本寫有我詩稿的雜志找到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種失而復得的快感讓我一瞬間出現了虛脫的感覺。少頃,我才緩過神來,居然有杜甫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那種狂喜,直嚷嚷:此刻有詩當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那幾首小詩是這樣寫的。
我總在月白風清的夜晚喊母親回家
我總在月白風清的夜晚喊母親回家
因為母親走的那天晚上
月光白得刺眼 天上的星星
就像一叢又一叢波斯菊
圍繞在母親身旁
母親那天走了就再沒有回來
老屋還在 老墻還在
那被磨得光光的灶臺 妝臺還在
那株母親親手栽植的梨花
年年都開成一面鏡子照得見人
我總在月白風清的夜晚喊母親回家
就像小時候母親拖長嗓子
喊我們幾姊妹回家吃飯
我也拖長嗓子喊我的母親
那些竹子就和著月光在風中搖曳
群山就開始回應:母親 母親 母親
那些螢火蟲就開始在風中舞蹈
那些月光被撕成一片片
像是思念 祝福 又像是憂傷
吊母親
我就這樣想你 漫無目的
不一定是在黃昏
有時在早晨 有時在傍晚
更多的時候
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刻
我想你的時候
我就讓思念的野馬
翻過一座山 又一座山
來到你的墳前
看芳草萋萋
看野花怒放
聽百鳥爭鳴
這是一塊風水寶地
是你生前勞作的地方
日出而作 日沒而息
只是這一次你實在太累了
睡過去 就再也沒有醒來
懷 念
母親一走
我就老了
老成父親的樣子
父親一走
我就成了孤兒
成了五十歲的孤兒
我想跟母親說說話
我看見母親墳頭的草又綠了
我想跟父親說說話
我看見父親的長煙斗
仍在老屋的那個角落 閃著火苗
我終究什么也沒有說
一任 草
枯了又黃
花 開了又謝
屋檐 青了又綠
我母親一晃已去逝六年有余,六年來,母親的音容無時不在我腦際縈繞。母親剛走的那半年,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與她在夢里相見。以后,雖然見面的次數隨著時光的流逝逐漸遞減,但母親慈祥的面容還是時不時在我夢中出現。為排遣憂思,我相繼寫出了《母親》《母親祭》《又見母親》等數十首專寫母親的詩以示對敬愛的母親無限的憂思和懷念。
我的思緒總是在母親和父親之間輾轉。老父親離開塵世已近兩年,兩年來他老人家滄桑的面龐總是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父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實巴交的農民,斗大的字不識一筐,然而,他硬是用他孱弱的雙肩支撐起了這個有著數十口人的大家,并讓我們七兄妹在那段極其艱難的歲月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能長大成人,給了我們回報社會的機會。然而,父親一個小小的甚至有些卑微的訴求我們卻沒有能夠滿足他。這件事我有絕對的話語權,但當父親提及此事的時候,我卻是裝聾作啞,甚至把自己置身事外。每每想起父親一生唯一一次給我們提出的這個小小的請求卻未能如愿,我總是如鯁在喉,肝腸寸斷。于是,順著這個思緒,在北京返回貴陽的飛機上,我即興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父 親
我唯一沒有能夠滿足你心愿的
是你需要一個女人
一個可以跟你說說話的女人
你說出那個想法的時候已近黃昏
你第二次說出這個想法的時候
黃昏已逼得很近 甚至
屋檐上已經有了很濃的夜色
我沒有像其他親人那樣提出反對意見
我只是假裝沒有聽見
后來你再已沒有提及此事
只是煙抽得比以前更猛
咳嗽也越來越重
覺睡得越來越早
時不時一個人對著大山發呆
只有小狗形影不離地陪伴著你
它陪你說話 陪你曬太陽
偶爾 也翻過籬笆
陪你看天邊的落霞
小狗成了你的女人 你的兒女
成了替我們盡孝的 姊妹
終于有一天 你和小狗
你和那只黢黑的陪伴你經年的小狗
一起融入了更深的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