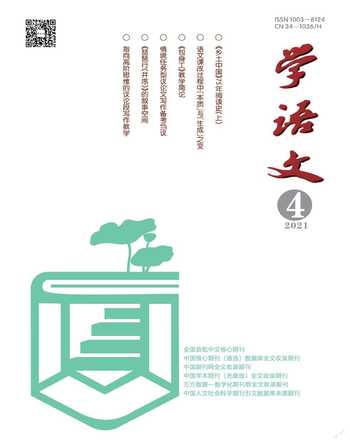感受視聽美感,體驗時空變幻
吳昊 王欣欣
摘要:穆旦《我看》是首次進入中學語文教材的新詩,閱讀難度相對較大。從視覺與聽覺美感的結合以及時間與空間的變幻兩方面來指導學生細讀,可以取得較好的效果。細讀法可以廣泛應用到中學新詩教學中去,從多角度對新詩進行鑒賞,逐漸提高學生閱讀新詩的能力。
關鍵詞:穆旦;《我看》;中學生;現代詩細讀
*本文系2020年廊坊師范學院校級教育教學改革項目“新文科背景下的‘專題式新詩教學研究”(項目編號:K2020-17)階段性成果。
統編本語文教材九年級上冊第一單元為“活動·探究”單元。該單元為學生提出的主要任務是自主閱讀教材中的現代詩,體驗詩歌的感情基調與意象,并通過小組互動或與教師交流的方式,加深對現代詩的認識。通觀該單元所收錄的現代詩作品,穆旦《我看》屬首次進入中學語文教材,閱讀難度相對較大。故本文嘗試結合穆旦生平與創作經歷,從視聽美感、時空變幻的雙重角度來細讀該詩,并試圖以此詩為例為中學生提供細讀現代詩的方法。
一、視覺與聽覺的美感
《我看》這首詩的題目就向讀者暗示了主題指向:通過抒情主體“我”的眼睛去“看”。“我”看到了怎樣的一幅圖畫呢?閱讀前兩節,讀者最直觀的感受或許就是詩中充滿一系列與“自然”有關的意象,比如“春風”“青草”“飛鳥”“晴空”等。這些意象本身就給人以生命的氣息,而作者穆旦在動詞的使用、意象的組合方面又頗為用心,使讀者能夠更深刻地感受到動態的視覺美。例如在第一節中,穆旦用一個“揉”字,就刻畫出了青草在春風中起伏的場景,并巧妙地將擬人、比喻兩種手法相結合,把青草的“低首又低首”比作“遠水蕩起了一片綠潮”,強化了視覺的“動”。在第二節中,“我”的視角從低處轉向天空,看到了“飛鳥”被“吸入”深遠的“晴空”,看到了“流云慢慢地紅暈”。“紅暈”還和第一節的“綠潮”形成強烈的色彩對比,使得畫面感更為強烈。
值得注意的是,《我看》中的畫面感并不是穆旦的憑空想象。這首詩創作于1938年6月,此時距離“七七事變”已近一年,穆旦跟隨清華師生經過艱苦跋涉,到達云南。因昆明的西南聯大校舍尚未完全建好,穆旦等師生只好暫居蒙自。在蒙自,穆旦參加了“南湖詩社”,他經常在湖邊漫步,湖邊的風景,便成為他寫《我看》的靈感:
有多少次,在課余,在南湖邊堤岸上,穆旦獨自漫步,或者與同學們一起走走,邊走邊愉快地聊天,時不時地發出笑聲;或者一天清早,某個傍晚,他拿著一本英文書—惠特曼《草葉集》或者歐文《見聞錄》(W. lrving:The Sketch Book),或別的什么書,到湖上靜靜地朗讀……這些就是他寫這首詩的背景。自然風光融入心靈,他那么巧妙地描繪了南湖景色。[1]
南湖的美好景色使西南聯大的師生暫時與戰爭相隔絕,也使得穆旦20歲的年輕心靈得到撫慰。他在南湖發現了“風景”,并將其寫入詩中。穆旦常被認為是一位“現代”詩人,但從《我看》這首詩來看,穆旦的作品其實并不缺乏“中國性”。因為《我看》中的“風景”書寫,對視覺氛圍的營造,正是對中國古典詩歌“詩畫”傳統的承襲。并且,穆旦對動詞的巧妙運用,也近似于古典詩歌的“煉字”。
《我看》還富有聽覺美。這首詩共五節,前四節每節四句,偶數句句尾押韻,比如第一節中“草”和“潮”押韻,第二節中“里”和“地”押韻,第三節中“畫”和“發”押韻,第四節中“息”和“逸”押韻。第五節共六句,第二句尾字“游”與第四節尾“流”押韻,第五句尾字“里”和第六句尾字“熄”押韻。這樣的音韻設置,使詩歌讀起來朗朗上口,并具有爆發力,讓讀者感受到詩句間蓬勃的青春力量。此外,穆旦還善于運用語氣詞和標點符號,詩中多次出現“哦”,但后面承接的標點符號卻大不相同:第一個“哦”出現在第三節開頭,后面承接逗號,隨后的語句是“逝去的多少歡樂和憂戚”,語意與語氣詞、標點的結合,給人舒緩的閱讀感受;而第三節開頭的“哦”承接第二句“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畫”而來,后面使用感嘆號,加重了語氣。這樣,同一節中便出現輕、重兩種語氣的交替,大大增強了詩句的節奏感。第六節中也有類似的運用,第一句中連用兩個“去吧”,皆以逗號承接;“哦生命的飛奔”,“哦”后面不加標點,使語氣顯得緊湊,也體現出“生命的飛奔”的急促。
由上所述,穆旦《我看》體現出穆旦作品的“感官性”特點:詩句中呈現出的視覺與聽覺的美感,來源于穆旦青春心靈的直觀體驗;同時,視覺和聽覺的效果,又有助于讀者更深入地走進穆旦的心靈世界。
二、時間與空間的變幻
除了視覺與聽覺的美感,《我看》還能讓讀者感受到時間與空間的變幻。第一、二節所涉及的場景主要為空間的變幻,由平視的“青草”轉向仰視的“飛鳥”。第三、四節主要描寫了時間的變幻。首先,詩句中的一系列時間標志詞,形成了今昔對比,如“逝去的多少歡樂和憂戚”與“多少年來你豐潤的生命”形成對比,“遠古”與“如今”形成對比等,使讀者跟隨穆旦的視線,不斷地回顧過去,又不斷地審視現在。
然后,這兩節中的今昔對比還體現在“我”與“你”的關系中。教材中提示學生思考:這里的“你”指什么?如果聯系第一、二節對自然風景的描繪,就可以知道第三、四節中的“你”指代大自然。大自然是永恒的,從久遠的過去一直延伸至現在,于是“我”只能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畫。雖然“遠古的哲人”曾向“你”舒出“詠贊的嘆息”,但“他生命的靜流”也只能“隨著季節的起伏而飄逸”。由此可見,相對于古老的大自然,人類的存在只是短暫的一瞬,大自然“豐潤的生命”與人類“生命的靜流”形成對比,“永在寂靜的諧奏里勃發”與“隨著季節的起伏而飄逸”形成對比。
既然穆旦意識到人類在無限的自然面前是渺小的,那他又將作何反應呢?第五節給出了答案。這是全詩的總結,也是全詩的升華。這一節中又出現了“你”,但這里的“你”已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抒情主體“我”的化身。這一節中的“生命”也不再是隨季節的起伏而“飄逸”的“靜流”,而是在“飛奔”“漫游”中化靜為動,呈現出自身的活力與生機。不僅如此,在第五節中,作為抒情主體的“我”與作為客體的自然合為一體,古老而永恒的自然與人類的對立已經消除,實現了時空的融合。正如詹丹所說:“那種在自然中湮滅主體的古典的歡樂和憂戚,那種把主體的感情投向自然的‘枉然舉動,此時不知不覺地隱退了。自然不再是人化的自然,人也不再是需要一味贊詠自然的人。那種貫串自然的生命力,也同時充盈著人的身體和靈魂。”[2]“我”熱情地擁抱自然,并跟隨著自然的節奏一起前行:“讓歡笑和哀愁灑向我心里,像季節燃起花朵又把吹熄”。作為一個20歲的青年人,“我”的青春生命在詩句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尤其是“季節燃起花朵”一句,給予讀者閱讀的快感。
《我看》呈現出的時空變幻,以及“我”與“你”之間人稱的變換,在穆旦后續的作品中仍然有所體現。在教學時,可以推薦學生閱讀穆旦的另一首詩《春》(作于1942年2月),進一步體會穆旦詩作中時空變幻、人稱變換的魅力,并感受穆旦對生命意識的張揚。
三、細讀法在中學生現代詩閱讀中的應用
上文以穆旦《我看》為例,論述了現代詩細讀法的兩個角度:視聽美感、時空變幻。前者可視為直觀的審美體驗,后者則涉及客觀的審美分析。由此來看,現代詩細讀法并不神秘。雖然因為年齡、閱歷等原因,中學生的閱讀能力相對有限,但只要掌握了細讀法的一些竅門,中學生也可以像專業詩歌研究者一樣,能夠獨立閱讀現代詩作品,并形成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審美判斷,成為“理想讀者”。
在傳統的詩歌閱讀中,“知人論世”法顯得尤為重要,很多詩歌解析文章的開頭都會先介紹詩人的生平背景,并引導學生通過詩人生平了解詩歌內容。但問題在于,自主欣賞詩歌需要獨立的審美體驗,一味依賴“知人論世”法,顯得有些刻板。并且,如果在不熟悉詩人生平、又不允許查資料的情況下(例如考試),“知人論世”法就會失去效用。因此,“知人論世”法可以視為細讀法的重要補充,但無法替代詩歌細讀。
如前文所述,細讀一首詩,第一眼看到的是標題。有時,標題已經揭示了全詩的主題,但也存在大量標題與主題無關的現代詩。所以,通讀全詩是十分有必要的。細讀現代詩可從多個角度入手,比較常用的有:一、查找詩歌中的核心意象,分析意象在詩歌中的作用;二、朗誦詩歌,感受詩歌的音韻特點(節奏、押韻、標點運用等);三、理清詩歌的結構層次,分析上下文的邏輯關系;四、找出閱讀過程中印象最深的詞語或句子,然后進行解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風格的作品,采用的細讀方法也不盡相同;幾種方法可以綜合使用,也可以只用一種方法,使用順序也較為自由。
有些中學生剛接觸現代詩,擔心“誤讀”,以至于和“正確答案”“詩人原意”“教師解讀”等“權威”不一致。其實,對于許多現代詩而言,“詩無達詁”或許是常見的現象。多種解讀視角的并存顯示了現代詩詩意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以及詩人思維和經驗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意圖在詩歌中找到“定論”的做法也許是不必要的[3]。并且,在如今語文教育改革的時代背景下,中學生閱讀現代詩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取得更高的分數,而是為了培養自己的文學情懷,提高人文素養。教師也要“以學生為中心”,允許學生在閱讀現代詩時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而不是強求學生與自己的觀點一致。此外,學生在閱讀現代詩作品時可以多與同學交流,在討論中碰撞靈感的火花。如果學生學有余力,多讀一些詩學鑒賞文章、著作,如洪子誠《在北大課堂讀詩》、孫玉石《新詩十講》、段從學《新詩文本細讀十三章》等,對深入掌握現代詩細讀法是大有裨益的。
從現代詩細讀的角度來說,穆旦《我看》其實還有更多讀法,這也體現出現代詩細讀的可能性與魅力所在。一方面,教師要更新原有的教學觀念和方法,引導學生掌握詩歌細讀法;另一方面,在教師的鼓勵下,學生要大膽提出自己對于現代詩歌作品的見解,并嘗試形成書面文字,進而自主閱讀、創作詩歌。可以說,現代詩細讀法的推廣,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1]趙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記穆旦,并憶西南聯大》,《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76-177頁。
[2]詹丹:《〈我看〉和看“我”——讀穆旦一首詩的札記》,《語文學習》2019年第3期。
[3]吳昊:《當代詩歌細讀的可能性——讀洪子誠〈在北大課堂讀詩(修訂版)〉》,《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2期。
(作者:吳昊,河北省廊坊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王欣欣,河北省廊坊師范學院文學院2018級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
[責編張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