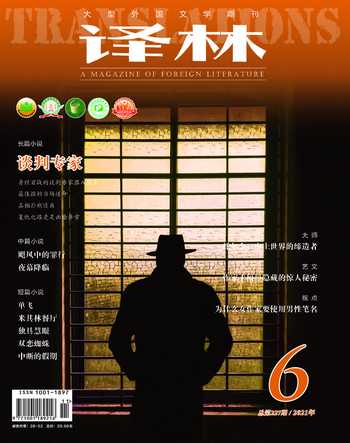鳥 人
〔英國〕亞歷克斯·奈特

“我想這會是一出好戲,懷亞特。”
富蘭克林可以看到山上的大房子慢慢露出了輪廓。晨霧在人們不經意之間逐漸消散,天空開始出現一片片迷人的深藍。今天天氣不錯。
懷亞特似乎很享受早餐,富蘭克林并未打擾它,而是走到矮墻旁,把望遠鏡和報紙挪到一邊,然后坐下,拿出保溫杯。他正往蓋子里倒咖啡,突然感覺有什么東西一閃而過,于是趕緊停下,拿起望遠鏡,對準街邊的一棟建筑。原來是這個家伙。只見一只蝗鶯優雅地落在三樓窗臺上。常聞其聲,難見其形。
富蘭克林笑了笑,放下望遠鏡,抿了一口咖啡。有些燙嘴,他不禁做了個怪相。以前瓦萊麗準備干糧時絕不會出現這種問題。食物的溫度總是剛剛好。她是如何做到的,富蘭克林漫不經心地想著。肯定是放在那里,等到一定時間再打包。這僅僅是一件日常瑣事,他想過要去問她,卻從未真正開口。她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人們總是這樣安慰他。
街上傳來一聲大喊“小心點”。兩個穿西裝的人在新開的國王酒店門前臺階上笨手笨腳地鋪地毯,旁邊一個騎自行車的快遞員差一點撞到他們。地毯是紫色的,這讓富蘭克林想到了羅馬將軍身上的披風。他正在觀察,突然看見一輛小貨車從街道那邊開過來,車身印著連體字“異想天開”。剛才大喊的那個人一邊擦手一邊用懷疑的目光看著司機,然后點點頭,朝酒店北側的巷子打了個手勢。
酒店的屋頂花園里,人們忙著布置婚禮現場。金先生的兒子等會兒就到,新娘想必緊隨其后。
富蘭克林喝著咖啡,仔細閱讀《紀事報》的體育版。小憩結束后,他擰上保溫杯蓋子,站起身來,全然不顧膝蓋的傷痛。
“怎么樣,懷亞特?吃完了是不是特別精神?”
他看了看懷亞特吃剩下的東西,這只解凍的老鼠身上能吃的都吃了。于是,他把剩下的殘渣清理干凈。
霧氣已經散盡。他朝北看去,太陽照在老工廠窗戶上,閃閃發光。此情此景讓他想起那些不在身邊的朋友。斯科蒂·諾瓦克得知他為滿足興趣愛好花大價錢在房頂上租了個像樣的私人場所,下巴都驚掉了。伙計們都稱他為“鳥人”,有時候干脆直接叫他“鳥兒”。他從不介意。畢竟,這些都是昵稱。
瓦萊麗聽到這些外號,頓時哈哈大笑,“恐怕還有更難聽的。”像往常一樣,她又說中了。
她走了,現在看來他和懷亞特也將離去,離開這個他和瓦萊麗住了54年的家。
幸好瓦萊麗在走之前還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擔心的事。租金管制之下,哪怕只有微薄的養老金,富蘭克林一樣可以在這里安居,還能保證懷亞特有凍老鼠吃。但金先生的律師卻別有用心。另一座氣派的大樓將在這里拔地而起,就像街對面的那座一樣。
對面酒店的屋頂花園里已有賓客聚集,他們身穿初夏盛裝,看起來華麗時尚。穿著黑色禮服的服務生忙著給客人端上香檳和餐前小吃。一扇鮮花做成的拱門已經搭好。他在想新大樓建成之后,這里是否也會建一座花園。或許懷亞特可以來逛逛。
早晨過得輕松愉快。現在太陽已經有點曬人,富蘭克林想把外套脫下來。
“你會想念這個老地方嗎?懷亞特,”他問道,“我們的新住處也是很棒的。”
這只猛禽好像是在瞪著他,目光比平時更加犀利,狹長密閉的鼻孔微微張開。
“哦,別這樣,懷亞特。瞧這一樁樁的,都是好事。”他戴上鹿皮手套,伸出前臂,讓懷亞特站上去。
他在心中暗暗贊嘆著這只靚鳥。他養過四只新西蘭隼,懷亞特是脾氣最壞的,但也是最漂亮的。眼睛呈藍綠色,尖喙如拋光木頭一般精致細膩。背部有深色的羽毛,深得幾乎發黑,在靠近肚子的地方變成淡灰色,然后變成純白色,如同逐漸消散的晨霧一般。
“準備好了嗎?”
對面屋頂花園里,婚禮已接近尾聲。富蘭克林拿起望遠鏡,朝人群掃視。他看到“異想天開”的兩個馴鳥師站在大家看不見的地方,只為給人們一個大大的驚喜。
司儀面帶微笑,仰起頭向客人致辭。由于距離太遠,富蘭克林聽不清,但他知道大概意思。
戒指在哪里?
那枚戒指。那枚重14克拉的鉆戒,《紀事報》社會版有過詳細報道。
說時遲,那時快。
一對灰林鸮從屋頂兩個角落飛出,向上猛沖30英尺,接著急速下降,在空中交會,畫出一個心形。然后馬上分開,側身飛行,在眾人一片歡呼聲中沖向那對幸福的新人。
突然,天空閃過一道黑白相間的光,將帶有戒指的那只鸮攔截。
眾人倒吸一口涼氣,接著新娘一聲尖叫。
片刻之后,懷亞特爬升到一定高度,從街對面飛了回來,爪子上有個金燦燦的東西,在朝陽下閃閃發光。
七分鐘后,幾輛警車率先抵達,但富蘭克林早已帶著懷亞特坐進自己的車里,從容地行駛在聯合大街上,開往一個更好的地方。
(王聞: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郵編:44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