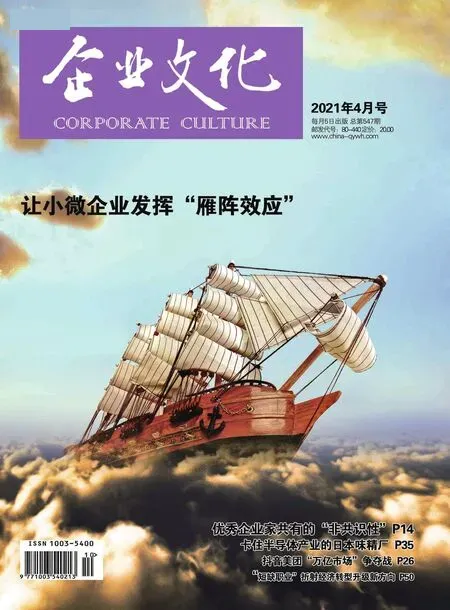年齡不能成為就業的攔路虎
春節過后,招聘就業市場暖流涌動。探訪各類招聘活動,發現不少企業招聘都要求“年齡限35 歲以下”,有的甚至提出“員工90 化”。進一步調查發現,當下很多用人單位仍然熱衷于收割“青春紅利”,靠青壯年人力資源參與同質化、低水平市場經營競爭。這種狀況,導致“35 歲+”與“40 歲、50 歲階段”人群成為“就業困難人群”,部分職場人士面臨失業、家庭收入下滑等困境。
相關專家認為,我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退,“35 歲失業”疊加“中年危機”,容易加劇職場“打工人”的擔憂和焦慮,不僅構成就業“年齡歧視”,更是對人力資源的浪費揮霍。建議通過各種措施引導“人盡其才”“人盡其用”,守護就業這個“最大的民生”問題。
“35 歲+”就業難
“裸辭”的37 歲IT 員工王海文,在春節之后,信心滿滿走上了“再就業”之路,“之前的單位工作環境不太適合我,早就想換工作。十多年的工作經驗,找個工作應該不難吧?”讓王海文沒有料到的是,看了很多就業網站、跑了多個面試,原本認為自己最有優勢的工作經驗,卻因為年齡“超標”,成了就業途中的“攔路虎”。很多單位直接寫明“限35 歲以下”,面試原本還聊得挺好,一問年齡就“秒拒”。10 多年的技術經驗,在35 歲的年齡面前,竟然一文不值。

“35 歲職場榮枯線”現象,幾乎在各個就業場景下都存在。公務員考試,大多要求35 歲以下;在企業招聘中,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除了特殊職位另作要求,大多數招聘也都限定了35歲以下;一些互聯網公司近幾年在優化人力資源結構時,也將35 歲確定為一個分界線,甚至部分公司明確要求“員工90化”。“35 歲職場榮枯線”已經成為職場人士望而生畏的一道“坎”。在金融行業工作的李敬表示,“跳過幾次槽,但隨著逼近35 歲,現在的公司盡管也有各種不如意,但已經不敢再跳了,再難再累也只能忍著。”在一些企業,“35 歲+”員工還可能面臨受排擠、邊緣化。”一位白領表示:“公司有個怪象,35 歲后離職的員工一個接一個。直到我自己到了這個年紀,才明白為什么。35 歲的員工,大多有老有小,生活瑣事多,身體機能下滑。但公司給你的任務有增無減,來自領導的直接壓力日益倍增。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公司不裁你,你也只能選擇主動走人。這樣,公司還省了一筆違約補償金”。一位外企員工說,“職場上我見過不少‘35 歲+’的員工一言不合就跳槽的,但大部分的境況越跳越不如前,普遍都會遇到收入下滑甚至斷檔的問題。35 歲之前就要考慮跳槽到那些工作環境合適的單位,不然就來不及了。”
年齡紅線
一位互聯網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說,年輕人有干勁、有精力,對工薪要求低,對上升空間期待值高,生活和家庭的牽絆少,創新創業意識更高,對工作的適應力、可塑性更強,自然更受到企業的青睞。企業看重員工的年齡結構,認為其是公司成長性、創新性、活力值的體現,并把這個納入對人力資源的考核目標,對于有選擇余地的公司來說,“小于35 歲”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對于很多單位來說,如果你沒有無可替代的競爭力,年滿35 歲即被視為已經觸碰了“年齡紅線”。在很多公司人力資源負責人看來,年滿35 歲的人就是“生活瑣事多”“工作精力有限”“身體健康有風險”的代名詞,從而不得不面臨“招聘不考慮,提拔靠邊站”的尷尬之境。人力資源管理師朱麗亞說。
“35 歲+”面臨的就業難題也和目前經濟結構、轉型發展水平直接相關。當前相當一部分企業的發展運營模式雷同,業內競爭激烈,而對高經驗值、高技術性、低工作強度的勞動力需求偏低,在人口紅利尚能滿足的情況下,企業自然愿意偏向用工作時長更長、薪資期待更低的低齡員工來替代高齡員工,“青春紅利”在就業上的優勢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朱國瑋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1 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20 年2月-9 月,在智聯平臺投遞簡歷的35 歲-49 歲中高齡求職者同比增長13.5%,增速約為35 歲以下求職者的兩倍。問卷調查顯示,在35 歲以上的求職者中,有近一半因收入下降而從中高收入群體降至低收入群體。
多位受訪者都表達了這一“無奈”,人不會永遠年輕,但永遠有人年輕。當你25 歲和35 歲的人做同樣的事時,你是“人力資源”;當你35 歲和25 歲的人做同樣的事時,你是“人力成本”。
歧視待破除
中國長期以來的人口紅利,讓企業用工習慣了“掐尖”的用人方式和超時超量的工作強度,但“35 歲職場榮枯線”實際折射了單位用人理念的誤區,即注重勞動力“便宜、好用”,而忽視產業轉型升級背后所需要的人力支撐、資源經驗儲備。這樣的用人導向,很容易陷入產業、用工‘內卷’惡性循環。”朱國瑋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的研究報告指出,“35 歲+”人群就業渠道、選擇更窄,收入更低,而這類群體有家庭有房貸,一旦失業,家庭財務狀況會變得十分脆弱乃至惡化,容易引發區域性銀行按揭貸款違約等連帶風險。還有專家擔憂,如果35 歲的人會遭遇就業困難,那么40 歲、50 歲的人,要在職場上找到舒適感就更是一道難題。這就像推倒了多米諾骨牌,“35 歲現象”可能加劇就業市場中的“40、50”待業現象,不同階段的就業年齡歧視,最后構成了反對延遲退休的現實阻力。
破除就業“中年歧視”。朱麗亞認為,隨著近年來出生率的逐步降低、市場勞動力供給的減少,用工難情況在低質量就業崗位開始凸顯,并呈現慢慢向高質量就業崗位蔓延的趨勢。在未來一段時間,用工難、用工荒將進一步加劇,因此破除“年齡歧視”“中年歧視”,重構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參與率,大力開發中老年人力資源,倡導“人盡其才”應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越來越重要的就業、招聘、用人導向。
立法制度保障。多位專家建議,在人口紅利逐漸消退的背景下,為了讓我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有必要對目前大行其道的就業年齡歧視做出禁止性的規定。事實上,很多國家都有反年齡就業歧視立法,比如一些國家對40 歲以上任何年齡段者給予平等就業保護,同時允許了一些特殊場合的年齡限制。
加大市場培育力度。35 歲并不意味著職業創造力的終結,反而是經驗能力充分沉淀的成熟時期,各行各業應更注重員工職業生涯規劃,充分認識和利用中高齡員工的特點和優勢,打造適合各年齡層融合發展的企業文化,營造友好的“人才流轉”就業市場氛圍。
為中高齡就業者“賦能”。朱麗亞認為,“35 歲+”群體就業的最大壓力不在于找不到工作,而在于找不到符合期待值的工作,陷入“高不成來低不就”的困境。對此,政府應加強引導培訓,賦予中高齡求職者更多技能,拓寬其再就業、創業之路。中高齡求職者也更應保持終身學習、積極更新觀念技能,憑扎實的工作能力立于職場“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