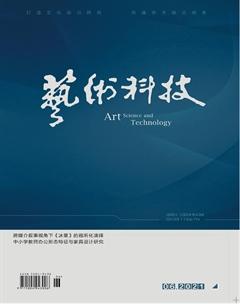跨媒介敘事視角下《冰菓》的視聽化演繹
關童 殷俊
摘要:在輕文學、輕小說作品原創IP動畫化的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難點是如何將書面文字表述轉化為視聽語言并對其進行呈現,如何通過視聽化手段將原作中人物的內心獨白、情感性描述展現在觀眾面前,如何簡潔明了地表述、強化矛盾沖突,推動劇情發展以捕捉觀眾眼球是這一過程中需要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輕文學;《冰菓》;跨媒介敘事;視聽化
中圖分類號:J9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6-00-03
《冰菓》是由日本京都動畫公司于2012年發行的電視動畫,改編自日本推理小說家米澤穗信的原作“古典部系列”小說,原作相比同類輕文學、輕小說作品具有較強的文學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動畫化的難度更高,因此將其作為跨媒介敘事改編的典型例進行剖析也更具意義。
1 輕文學、輕小說及其動畫化現狀
輕文學、輕小說如今已不是一個飽受成見的文學類型,它具有多重價值,這一方面體現在其多元的世界觀設定和價值內核,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其具有較高的商業價值。青年群體作為ACGN(動畫、漫畫、游戲、小說)文化圈的主力消費軍,他們對于輕文學、輕小說的關注度有增無減,此類作品也成為二次元文化中極為重要的創作來源。
1.1 輕文學的定位及特征
輕文學(ライト文蕓)是日本小說分類的一種,主要受眾是年輕人,此類作品文筆詼諧,閱讀輕松,有很強的娛樂性,但同時結構和文字均不乏嚴謹性、能令人回味、引發思考,兼具傳統文學作品的特征[1]。而對于與輕小說類似的輕文學,目前出版界還未對其有明確的定義,這使得輕文學與輕小說之間的界定十分曖昧。臺灣天聞角川將輕文學作品與輕小說作品進行了分類,輕文學作為一個類別被劃分在與“輕小說”同級的“書籍”欄目范圍內。目前看來,通過對輕文學與輕小說進行差異化比較的方法說明輕文學更具直觀性和說服力。簡單來說,輕文學較之輕小說更具文學性,行文結構更具嚴謹性,口語化程度更低。榎本秋在《輕小說文學論》中論述了輕小說具有的5個特征,其中的兩點特征——較多地使用漫畫、動畫風格的插圖,以及含有fantasy(幻想)要素,是輕文學作品不一定具有的。但即使是根據這樣明確的特點對作品進行劃分,依舊會有作品處于中間地帶無法被定義,而隨著作品數量的劇增以及題材的多樣化,作品類別之間的界限也會愈加模糊不清。通過榎本秋對輕小說特點的描述以及出版社對輕文學作品的定義,“古典部系列”小說顯然更適合劃分在輕文學作品類別下。因此,作為輕文學的“古典部系列”小說的動畫化更具代表性,探討以其為代表的文學作品的跨媒介敘事手法也更具價值。
1.2 輕文學、輕小說動畫化現狀
動畫產業同影視產業一樣,需要有優秀的劇本內容作為保障。如今原創動畫劇本處境尷尬,而將高人氣、高銷量的文學作品作為劇本則能吸引穩定的觀眾群[2]。日本輕文學、輕小說類作品的銷量5年間持續增長[3],可見其人氣潛力之大,許多輕文學、輕小說作品都被改編成了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漫畫、動畫、真人電影、游戲等,實現了作品的跨媒介傳播。如《涼宮春日的憂郁》《文學少女》《無頭騎士異聞錄》等知名動畫作品均是由輕文學、輕小說作品改編而來的;于2020年1月開始連載的電視連續動畫《虛構推理》也是由同名輕小說作品改編制作,而原作于2015年就進行了同名漫畫連載,截至動畫化決定時原作出版發行量已達200萬冊。如今,大量動畫作品都經歷著這種跨平臺模式的改編路徑,受眾也從讀者發展為觀眾群,進而成為更加廣泛的消費群體。
2 跨媒介敘事的作品忠誠度
2006年美國學者亨利·詹金斯首次提出“跨媒介敘事”理論,他將“跨媒介敘事”定義為“一個跨媒介故事橫跨多種媒介平臺展現出來,其中每一個新文本都對整個故事做出了獨特而有價值的貢獻。其理想形式是每一種媒體出色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4]。“古典部系列”小說有別于常規意義上的推理小說,案件調查多是由千反田愛瑠(以下簡稱千反田)的好奇心驅動,推理的目的在于挖掘人物行為動機,而不是表層的事件現象,情節變化起伏平緩,這給動畫化的視聽呈現增加了難度。約翰·M·德斯蒙德和彼得·霍克斯在《改編的藝術:從文學到電影》中使用“緊密型”“松散型”以及“居中型”定義文學作品及其改編影視的一般關系。其中“緊密型”改編有《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影視化,在原作擁有龐大粉絲量的情況下,原作者J.K.羅琳要求必須高度還原原作,演員和配音都要自己經手挑選,由此引發了“原著黨”的歡呼,影視作品完成了對原作口碑的延續。而部分影評人則冷眼觀之,認為這種“緊密”造成了電影的死板,使電影失去了靈動性。按此分類方法,《冰菓》同樣可以被視為緊密型改編,原著中的絕大部分敘事元素都被保留了下來,沒有過多的填充,對原著的忠誠度非常高,也沒有因跨媒介的轉變失去作品的生命力。
“古典部系列”小說作為輕文學作品,書中并沒有出現輕小說作品中常見的與人物、場景相關的插圖,所以動畫化的視覺呈現非常考驗制作方與觀眾觀看預期的契合度。觀眾接受一部新作品,必然包含著與之以前接受的作品相對比而進行的審美價值檢驗。對于已有的文學作品的動畫化,一方面要考慮有過原著閱讀經歷的讀者對于文字的描述有著不同的理解,動畫化后的作品是否能夠在其文學作品的審美上得到認可;另一方面還要顧及沒有讀過原著的部分觀眾對于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是完全基于動畫制作方的設計和掌控的,這些都會影響到作品后續的口碑建設,因此動畫化改編要對原著的忠實度進行合理控制。
動畫劇集中,正劇的時長通常為20分鐘左右,因此,動畫制作方在既要考慮情節時長的問題,還要考慮劇情的劇集分割的情況下,往往會對原著內容進行刪減和補充。刪減的方法可大致分為刪減角色、刪減場景、刪減情節。在動畫《冰菓》中運用得較多的方法是對次要情節進行刪減以歸整劇集,從而在不影響情節的前提下加快敘事節奏。同樣,內容的擴充、改編也必然會帶來新的敘事。例如,動畫第7話《初見真身》中對原作結局進行了改編,由原著中兩姐妹“仍然存在隔閡”改為兩人“關系緩和”,故事的結果使千反田對這種血緣紐帶的渴望得到肯定和印證,呈現給了觀眾一個更圓滿美好的故事結局。縱觀原作者米澤穗信的作品不難發現,其作品中帶有微弱清冷的悲劇色彩,“古典部系列”小說也不例外。《冰菓》的故事發生于一個不發達的小鎮,男主角折木奉太郎(以下簡稱折木)的姐姐折木供惠是劇中唯一“走到外面的世界”中的角色,其他人或多或少都處于被環境、身世牽絆的狀態。而動畫劇集對這一話的改編,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原作的悲劇氛圍,滿足了部分觀眾對“圓滿結局”的心理預期,但從全劇精神內核的傳達角度來看,這樣的改編卻是有所損失的。由此可見,原創劇情中可能會存在原著作者與制作方對作品理解的偏差。
好的擴充則可以起到銜接劇情、塑造角色特征、深化主旨的作用。如《冰菓》的OVA(原創光盤動畫)《應持之物》是由米澤穗信進行故事創作、武本康弘編寫劇本的原創劇集,故事發生于TV版11集和12集之間,依舊是圍繞主人公四人的互動展開。主線劇情以一集為單元,由動畫前一個故事單元的“折木受挫”,到OVA的“折木供惠引路,部員幫助折木重建信心”,再到動畫中“折木繼續追求薔薇色的生活”。此處OVA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一方面擴充了劇情,使其更加連貫,增加了角色互動,豐滿了人物形象,加強了折木供惠這一角色在全劇中推動劇情的角色作用;另一方面,OVA中也增加了一定的“媚宅”元素,吸引了觀眾眼球,完成了場景的轉換,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原作以及劇集動畫中開篇便提出的“薔薇色的高中生活”這一場景。
3 跨媒介敘事策略
3.1 單一敘事場景的視聽化
輕文學作品相較于輕小說而言,書面性語句多,口語化程度低,因此在改編過程中由書面敘事轉為動畫敘事的難度相對提高。原作第1部開篇由折木的姐姐折木供惠的一封長度跨越原著兩頁開本的信展開,信中大致交代了折木供惠目前的處境,以及劇情中非常重要的推動點——她希望折木加入古典文學部。這封信給讀者提供了很多有關折木供惠這一關鍵角色的細枝末節的線索,這封信不僅是劇情主線發展的關鍵一環,也是整部作品所要表達的內核的一個側面。信的篇幅較長,而京都動畫在改編時對此段情節進行了非常詩意化的演繹:首先將這封信進行了手寫字體化的處理,將句子分組,每一次僅呈現少量的信息內容,以類似對話體的形式幫助觀眾更好地理解信件內容;其次將句子分組的更替方式處理為色澤清麗的水波蕩漾開來的形式,輔之以折木一系列日常生活狀態的演出,展示了他的住所以及其他家庭成員,既完成了信中內容的輸出,同時也豐富了角色形象,補足了部分輕小說和輕文學中缺失的中景[5]。
關于文學和電影之間的差異,評論家羅伯特·斯塔姆認為,文學是一種單聲道的媒介,而電影則是一種多聲道的媒介。視聽化的優勢之一在于配音的加入為敘事效果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角色配音在動畫作品中擁有重要地位,看似不引人注意,卻是衡量作品優劣的關鍵元素,觀眾會為符合他們對角色特質預期的配音買賬。在原著中,折木供惠這一角色雖然關鍵,但刻畫扁平,難免使這一比觀眾更加具備上帝視角的角色有些生硬刻意,而動畫化中則很好地避免了角色扁平的問題,畫面中折木供惠的文字配合上聲優出色的配音技巧,傳達出了姐弟之間的親昵和關切之感,讓她的囑托更加難以拒絕,不失趣味地將內容傳達給了觀眾,讓這個從未露臉的角色圓形、立體起來。
“古典部系列”小說中的推理事件通常是由人物在固定場所內的交談,或是男主一人的內心獨白得出結論,并沒有過多場景的轉移和刻畫,這使故事中的推理邏輯更加聚焦,但這也可能導致視聽化之后的視覺效果被削弱,帶來敘事拖沓、節奏緩慢的觀感。京都動畫在這方面的處理非常出色,在動畫劇集的第4話中,古典文學部的4個部員分別對“關谷純事件”的事情經過進行了推理假說,4個人假說的內容也分別用了不同繪畫風格的小短片進行了演示。動畫在其他情節中也多次出現了富有創意、傳達精簡的小短片,以此表現人物的對話內容,彌補了場景單調的缺陷。
3.2 文字敘事到鏡頭敘事
跨媒介敘事過程中,文字敘事中對于事物的描述,如口頭描述轉化為動畫、電影敘事時便成了直觀的圖像,而圖像意味著更多的細節。文學作品對于物質世界描述模糊的特性,給予了改編更多的可能。在輕文學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對白和內心獨白占據了劇情信息的絕大部分。而在這一方面,京都動畫以一向精細的動畫制作優勢給觀眾留下了更多可以反復追尋的細節。例如,動畫劇集第5集中,折木對于糸魚川養子老師的身份進行了推測和說明,在原作中,這一段推理僅用了折木的一段陳述,而在動畫劇集中,這一情節共跨越了8秒左右的時長,在后5秒中動畫運用快切的形式展示了糸魚川養子在過去45年中34個關鍵人生節點,如生子、成家、戀愛、入學等,幫助觀眾完成了一次時間上的逆溯,極具代入感,角色在每一個節點的樣貌、穿著和姿態都各不相同,精準地傳達了畫面語義。
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電影有存儲和傳遞信息的能力。它能夠用圖像瞬間將一幅全景畫面展示出來,而這些圖像則需要用很多頁的文字來描述。相比鏡頭敘事,文學作品在呈現物質世界的效果時描述顯得十分乏力而模糊,而作為推理小說,文字媒介“單聲道”敘事的弊端尤為明顯。原作故事中的關鍵線索是直接給出的,細心的讀者可以根據書中給出的提示完成推理,敘事中以折木的視角完成對事件環境的觀察,破案的線索在他的觀察中暗埋,但由于文字媒介的限制,線索的提供難免有些生硬,暗埋沒有達成“暗”的效果。鏡頭敘事則更適合“埋伏筆”,其打破了書面敘事的局限性,可以靈活拿捏故事細節,帶來更流暢的敘事效果。如在第1話《深具傳統的古典文學部之重生》和第7話《初見真身》中,一閃而過的線索人物不露聲色地完成了提示,敘事上抹去了線索提供的突兀感和刻意感,同時也讓折木的推理更具合理性和可完成性。
3.3 敘事人稱的轉換
在對文學作品的改編中,最難處理的視角就是第一人稱敘事。文學敘述中,表達敘述者內在思想的手法通常是自言自語,或是對另一個沒有聽其講話的角色說話。而在動畫作品中,大量的角色心理活動和內心獨白可以頻繁地使用畫外音來揭示。除此之外,還可以對故事敘述者內在思想進行敘事人稱的轉換,進行角色分工。無論是在小說的書面敘事中還是動畫的視聽語言敘事中,都應合理安排、分配觀眾的注意力,鏡頭長度和節拍的把控都會給敘事節奏帶來影響。在動畫劇集第7集《初見真身》中,他們一行人為了什么,如何來到這里進行團建的信息由原作中折木的第一人稱陳述轉為福部里志對折木的口頭轉告,動畫將故事信息合理地分配給不同的角色,陳述變為對話帶來了鏡頭的切換,推動了故事情節靈活發展。
輕文學、輕小說作品通常都是圍繞一個主角的主觀視角進行寫作的,在《冰菓》系列小說第3部《庫特莉亞芙卡的排序》中,作者運用了非常特殊的第一人稱交替變化的寫作手法敘事,即敘事視角不僅僅停留在折木一人身上,而是在四個主角中來回切換。動畫劇集中對此手法進行了保留,一改之前折木的單一視角,加入了其他三人的視點和內心獨白,營造了一種近似群像的敘事景觀。與閱讀原著時由敘事人物視角轉變帶來的斷層相比,動畫化的表現更加自然且不引人注意,視角的切換也十分流暢。
3.4 角色設定的解構與重組
角色是一切敘事的推動者,被寫作和電影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承擔和實現[6]。在動畫作品中,角色與其他敘事要素相比被觀眾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期待,觀眾會將他們標簽化,分析他們的行為舉止,甚至人們在承認他們的虛構性時,也要尋求“線索”和“來源”,以便進一步把他們逼向“真實”[7]。以一種傳播媒介為基礎創立的“人設”,在進行跨媒介敘事的過程中,將在其他媒介傳播中沿用“人設”以加強受眾印象,并為此“人設”發展更多其本身或傳播信息的可能性[6]。京都動畫公司在作品中充分其展示了角色塑造能力,也證明了優秀的角色塑造對全劇起著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角色塑造多是由角色與角色之間的互動完成的,原著里4個主人公在各類事件發展過程中完成了心態、關系的轉化,推動了劇情發展,完成了角色塑造。《冰菓》中伊原摩耶花與折木是9年的同班同學,她對待折木的態度多是毒舌、傲嬌的,收錄在原作第6部《遲來的羽翼》中的短篇《鏡不能鑒》描述了伊原摩耶花持此態度的緣由,而在TV動畫劇集中卻沒有將這一部分展現出來,這使得她的形象看起來更加“萌”化,更貼合書中以折木為第一人稱對她的主觀印象的描寫,表現得更加直觀。同時,她對折木處事態度的不滿也更好地塑造了一個多年老友的鮮活形象。
對小說作品進行動畫化改編時,動畫制作方常常會根據劇情需要進行一定的剪切、合并、刪減和排序,以實現在跨媒介敘事中優化故事情節的效果。“古典部系列”小說是由多個故事組合起來的,故事之間的暗線拼接并不明顯,改編時并不需要沿襲原著中的時間安排。因此,為了營造更清晰的因果關系和角色情感糾葛,原著第4部《繞遠的雛人偶》被拆分為3段,分別排列在整部動畫劇集的前、中、后3個階段。第一階段兩人“初識”的橋段強化了折木的“節能主義”信條和千反田的“好奇心”性格,在第1集就給予了觀眾印象深刻的角色特征,確定了全劇人物性格沖突的基調;第二階段折木進一步對千反田的內心世界有所了解,并反思和提醒自己不可犯下相同的錯誤,為后續“折木不慎犯下原罪”做了鋪墊;第三階段折木與千反田兩人頻繁互動,這樣的編排更符合感情線的推進邏輯。這樣大幅度的改編大幅改動了故事的時間順序,令部分觀眾對劇情中的時間推移印象模糊,無益于對作品的理解。于是在動畫劇集中,過場動畫以二十四節氣的順序編排設計,將一個個故事單元串聯在了一起。通過這種方式來標記,不僅可以作為刻度標明故事發生時所處的時間及階段,梳理了故事線,引導觀眾不至于迷失在大量松散零碎的故事單元中,更能通過這些真實的符號增強故事的真實性,給人一種故事具有真實依據的感覺,減弱了故事的虛構性,使故事產生了虛實相交的效果[8]。
4 結語
跨媒介敘事是對原有作品進行再創造的過程,可以完成作品新舊媒體的跨越和轉化。輕文學、輕小說作品的動畫化在日本早已形成了成熟的體系,這種IP構建模式有效保證了粉絲基數,也為產業帶來了良好的收益。成熟的視聽化演繹手段能為觀眾提供更優質的觀感,為作品帶來更好的口碑與評價,并為原作品吸引更多的關注度和銷量。同時,此類文學作品在產能高的基礎上為動畫影視行業提供了大量劇本素材,兩者相輔相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構建了一個積極的生態。
相比之下,我國輕小說、輕文學產業并不發達,但擁有頗具規模的網絡小說市場。網文IP的改編一度引發熱議,且出現了不少質量優良的電視劇、動畫等作品。國內網絡小說在改編動畫作品時要認識到“原著黨”的重要性,很大一部分觀眾希望改編能高度還原原著,因此,制作方要注意跨媒介敘事的作品忠誠度問題,虛心學習、合理借鑒成功作品的經驗,為我國動畫影視事業注入新的生機。
參考文獻:
[1] 天聞角川.天聞角川“輕文學系列小說”:輕文學介紹[EB/OL].天聞角川,http://www.gztwkadokawa.com/zt/
qingwenxue/jieshao/index.htm,2020-12-25.
[2] 崔秋駒.輕淺的美學:論日本輕小說的文體特征與審美價值[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16.
[3] 朱曉燦.從日本輕小說談國內網絡小說的出版[J].出版廣角,2020(02):42-44.
[4][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與舊媒體的沖突地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57.
[5] 薛秋實.論輕小說的審美與消費特性[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9.
[6][法]弗朗西斯·瓦努瓦.書面敘事·電影敘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29.
[7]于明潔.談人物設定在跨媒介敘事中的重要性[J].國際公關,2019(11):244-245.
[8]張曉東.淺談東野圭吾《白夜行》的敘事手法[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20,36(04):11-16.
作者簡介:關童(1996—),女,山東淄博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動畫、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及理論。
殷俊(1973—),男,江蘇武進人,博士,教授,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動畫、數字媒體藝術設計、交互藝術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