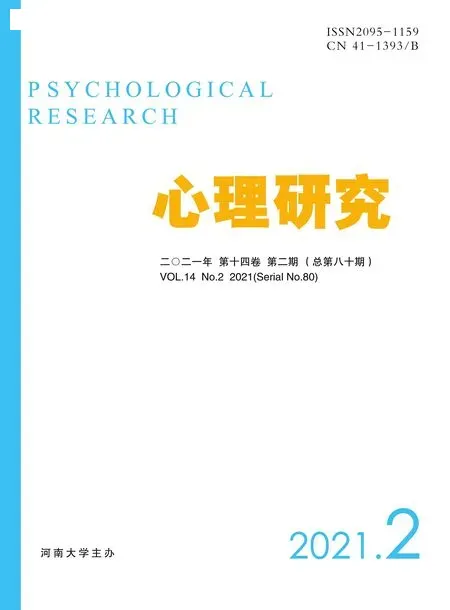社會分組信息對公平?jīng)Q策的影響
楊瀅巧 沈佳燕 楊亦松 何曉燕
(寧波大學心理學暨研究所,寧波大學群體行為與社會心理服務研究中心,寧波315211)
1 引言
追求公平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個重要且普遍的現(xiàn)象(Kahneman,Knetsch,&Thaler,1986),人們甚至會為了達到公平的結果而犧牲自己的物質利益(Camerer& Thaler, 1995; Forsythe, Horowitz,Savin,&Sefton,1994)。這一現(xiàn)象違背了經(jīng)濟學中經(jīng)典的完全理性經(jīng)濟人假設——人們會絕對理性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追求公平的行為備受研究者關注。
對追求公平相關問題的研究一般采用最后通牒游 戲 實 驗 (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1982)。在該游戲中,兩名參與者對一筆資金進行分配,由提議者提出一種分配方案,而回應者選擇接受或拒絕。若回應者接受,則資金按照該方案進行分配,否則雙方均得不到任何金錢。假如人類是完全理性的經(jīng)濟人,則提議者應該分給回應者盡量少的金錢,而回應者應該接受任何比例的分配方案。但一系列的行為研究 (Bolton&Zwick,1995;Güth&Tietz,1990)發(fā)現(xiàn),提議者會分給回應者很可觀的金錢數(shù)目,平均達到了金錢總數(shù)的40%~50%;而對回應者來說,如果得到的金錢少于總數(shù)的20%,則有40%~60%的可能性會拒絕該分配方案。后續(xù)有研究進一步發(fā)現(xiàn),這種看似不理性的追求公平的行為源自情緒的作用。如Sanfey等人采用fMRI技術發(fā)現(xiàn),回應者在面對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時,與厭惡情緒有關的腦島和與認知相關的背外側前額葉均會被激活,而且腦島的激活程度與拒絕他人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有很高的相關(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Cohen,2003)。據(jù)此,Sanfey等人(2003)認為,不公平待遇帶來的負性情緒促使人拒絕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從而使雙方從不公平狀態(tài)回歸到收益均為0的公平狀態(tài)。Tabibnia等人(2008)研究發(fā)現(xiàn),公平的分配能夠讓人們獲得更高的幸福感,且與獎賞有關的很多區(qū)域也會被激活,而接受不公平分配會引發(fā)右側的背內側前額葉更高的激活(與情緒調控有關),而腦島的激活降低(與負性情緒有關)。總之,這一系列關于追求公平的研究表明,人們并非按照完全理性經(jīng)濟人假設進行決策,即當遭遇不公平分配時,人們會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來懲罰對方。
決策中追求公平并非純理性認知的結果,其行為可能具有情景的相對性,即根據(jù)具體情景設定不同的公平標準。因為涉及公平的決策往往發(fā)生在多人互動的情景中,而決策的結果很可能受到互動對象相關特性以及決策者與對方關系的影響。也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對公平的追求受到博弈雙方特征的影響。如回應者的年齡越小越容易接受對方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Harbaugh,Krause,&Liday,2003),且當對方為異性時,對其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的接受率越高 (Sutter,Bosman,Kocher,&van Winden,2009)。不僅如此,對方的面孔吸引力和身份同樣也會影響個體在決策中對公平的追求。相比于低面孔吸引力者,人們更傾向于接受高面孔吸引力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Solnick&Schweitzer,1999);相比于提議者為計算機的情況,回應者對由真人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的拒絕率更高(Sanfey et al.,2003)。
綜合上述研究可見,博弈雙方的一些社會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個體在決策中對公平的追求。然而鮮有研究考察博弈雙方的核心社會特性——社會分組(Brown,Hitlin,&Elder Jr,2007)對人們決策中公平的追求。社會分組決定了個體間的社會群體關系,是影響個體認知和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當人們歸屬于一個群體時,會給該群體較高的評價,分給該群體內成員較多的資源;而對該群體外的成員則表現(xiàn)出更多的吝嗇和仇視(Tajfel&Turner,1986),其具有更少的正面特征,更不值得信任(Brewer&Harasty,1996)。據(jù)此,筆者預期社會分組信息極有可能對人們追求公平的行為產(chǎn)生影響:面對一個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當提議者為群體外成員時,回應者體驗到更多的惡意、歧視和侵犯,選擇拒絕的可能性相對于提議者為群體內成員時更高。考慮到種族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分組屬性,并且能夠自動化地從面孔中進行提取(Sporer,2001),本研究通過呈現(xiàn)不同種族的提議者面孔來實現(xiàn)對社會分組因素的操作,并采用研究公平行為的經(jīng)典范式——最后通牒游戲,探討社會分組信息對決策中追求公平行為的影響。
2 方法
2.1 被試
招募30名大學生自愿參與本實驗。其中2名被試在實驗中因正確率低于89%(根據(jù)實驗結果,被試正確率均在98%左右,若正確率低于90%說明被試不認真),及1名被試的數(shù)據(jù)由于程序原因存在缺失而被剔除,最終獲得27名被試的有效實驗數(shù)據(jù),其中男性9名,女性18名。被試年齡在18到25歲之間,所有被試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無色盲,無身心疾病,參加完實驗后獲得一定的報酬。
2.2 實驗儀器和材料
實驗程序采用Matlab的Psychtoolbox工具箱編寫(Brainard,1997),通過Pentium計算機進行控制,刺激呈現(xiàn)在17寸顯示器中央,屏幕背景為灰色。分辨率為1024×768,刷新頻率為100HZ。被試眼睛距屏幕60cm。刺激材料采用Photoshop軟件處理,使得每張面孔圖片大小一致。所有的面孔均為正面照,五官清晰可見,面孔表情均為中性表情且所有的面孔對被試來說都是陌生的。實驗材料參考Dickter(2007)的實驗,包含東方人物和西方人物面孔各6張,其中男女各半(如圖1所示)。

圖1 人物圖片
2.3 實驗程序
實驗分為兩部分進行。首先,正式實驗開始前,被試需對實驗中所使用的12張?zhí)嶙h者的面孔吸引力進行0~10評分(0表示不吸引,10表示非常吸引,分數(shù)越高代表吸引力越強)。評分結束后,實驗指導者告知被試將要進行最后通牒游戲,強調本實驗為聯(lián)網(wǎng)實驗,會有其他人一起進行游戲。該人可能為在校的中國學生(內群體),或為在校留學生(外群體)。被試任務是對提議者提出的分配方案做出接受或拒絕的選擇。為了使實驗環(huán)境更具有真實性,實驗開始后,主試會假裝打電話提醒另外一邊的實驗負責人。主試根據(jù)提議者的類型來決定用語,當提議者為外群體時,問“Are you ready?”“Ok,let’s begin!”提議者為內群體時,問“你們準備好了嗎?”“好的,我們開始吧!”正式實驗分兩節(jié)。首先是一個主觀調查,主試要求被試給提議者分20元錢。包括兩個方面的調查,對方分的話,給你多少你愿意接受;如果自己分愿意給對方分多少。之后則是公平分配反應時判斷實驗。具體實驗流程如圖2所示,首先呈現(xiàn)提議者面孔圖片,呈現(xiàn)時間為1s,空屏0.5~1s后呈現(xiàn)總的分配金額(用灰色條標示),并出現(xiàn)倒計時,1s~3s后呈現(xiàn)提議者提供的分配方案(呈現(xiàn)被試被分給的金額并用紅色條標示),要求被試按鍵選擇接受還是拒絕該分配方案,若接受按“J”鍵,若拒絕按“F”鍵。被試做出反應,空屏1.5s~2s后進入下一個試次。
實驗總共240個試次,分為2個block進行,每個block包含120個試次。實驗過程中每個block的組別關系相同,block順序在被試之間進行平衡。根據(jù)提議者與被試的組別關系及被試分配給自己與他人錢的比例構建2(社會分組信息:內群體vs外群體)×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的被試內設計。

圖2 實驗流程圖
3 實驗結果
3.1 反應時結果
根據(jù)被試的總體反應情況,剔除反應時大于4s的數(shù)據(jù),對反應時進行2(社會分組信息:內群體vs外群體)×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社會分組信息的主效應不顯著,F(xiàn)(1,26)=1.03,p=0.319,ηp2=0.04;社會分組信息和分配比例兩因素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1,26)=1.10,p=0.304,ηp2=0.04;分配比例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12.95,p=0.001,ηp2=0.33,其中分配比例為9∶1時的反應時均顯著小于其他四種情況(p值均小于0.05),分配比例為7∶3時,反應時最長(如圖3所示)。結果表明回應者在面對內群體和外群體提議者時選擇時間是一致的,提示對內群體和外群體提議者的反應難度是一致的。回應者對極端不公平提議(分配比例為9∶1)非常敏感,因此能很快做出反應;面對中等不公平提議(分配比例為7∶3)時,選擇難度增大,可能在權衡公平和自身利益,因此反應時增長。
3.2 接受率結果
對接受率進行2(社會分組信息:內群體vs外群體)×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社會分組信息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6.67,p=0.016,ηp2=0.20,其中回應者對內群體提議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提議的接受率高于對外群體提議者的。分配比例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1325.67,p<0.001,ηp2=0.98,其中除分配比例為9∶1和8∶2兩種條件下的接受率無顯著差異外(p=0.370),其他任意兩種分配比例條件下的接受率均有顯著差異(p值均小于0.01)。接受率會隨著回應者被分配所得比例的提高而上升,其中多數(shù)情況下(90%以上)回應者會拒絕低于30%的分配(見圖4)。社會分組信息和分配比例兩因素的交互作用顯著,F(xiàn)(1,26)=3.25,p=0.015,ηp2=0.20。進一步簡單效應分析發(fā)現(xiàn),只有在分配比例為7∶3時不同社會分組條件下的接受率有顯著差異,t(26)=3.08,p=0.005,而其他分配比例下無顯著差異(p值均大于0.400)。該結果表明回應者在面對非常不公平(分配比例為9∶1、8∶2)和相對公平(分配比例為6∶4、5∶5)的提議時,只會考慮提議本身的公平與否,而不會受到提議者的社會分組信息影響;當提議的不公平程度處于中等(分配比例為7∶3)時,回應者做決策較為困難,開始關注提議者的社會分組信息,如提議者為內群體,則更易接受中等不公平提議。該結果暗示人們的公平感具有情景相對性。

圖3 不同社會分組和分配比例下的決策反應時(M±SD)

圖4 不同社會分組和分配比例下的接受率(M±SD)
以上對反應時和接受率的分析表明,社會分組信息會影響決策中對不公平選項的反應。有研究表明,社會分組會影響人們對面孔吸引力的判斷(Bernstein,Lin,& McClellan,1982;Dickter&Bartholow,2007),為了排除面孔吸引力在本研究的作用,本實驗對提議者面孔的吸引力進行分析。
3.3 提議者面孔吸引力結果
對提議者面孔吸引力進行2(性別:女vs男)×2(社會分組信息:內群體vs外群體)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社會分組信息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12.16,p=0.002,η2=0.30,其中內群體提議者的面孔吸引力顯著高于外群體提議者;性別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12.40,p=0.001,ηp2=0.31,其中女性提議者的面孔吸引力顯著高于男性提議者;社會分組信息與性別的交互作用也顯著,F(xiàn)(1,26)=15.02,p=0.001,ηp2=0.35。對交互效應進一步簡單效應分析發(fā)現(xiàn),女性面孔吸引力受社會分組信息影響,內群體女性面孔的吸引力顯著高于外群體女性面孔F(1,26)=32.84,p<0.001,ηp2=0.54,男性面孔吸引力不受社會分組信息影響(如圖5所示),F(xiàn)(1,26)=0.09,p=0.769,ηp2<0.001。
以上提議者面孔吸引力分析顯示,女性面孔吸引力受社會分組信息影響,男性面孔吸引力不受社會分組信息影響,那么是否是面孔吸引力造成了本研究的結果?為了排除面孔吸引力的作用,進一步對男、女性別條件下對不同分配比例條件下的接受率進行分析。
當提議者為男性時,對接受率進行2(社會分組信息:內群體vs外群體)×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社會分組信息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10.40,p=0.003,ηp2=0.29;分配比例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1188.75,p<0.001;社會分組信息和分配比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1,26)=1.52,p=0.229,ηp2=0.06(見圖)。

圖5 不同社會分組和性別提議者面孔吸引力得分(M±SD)

圖6 提議者為男性時不同社會分組和分配比例下的接受率(M±SD)
當提議者為女性時,對接受率進行2(社會分組信息:本群體vs外群體)×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社會分組信息的主效應不顯著,F(xiàn)(1,26)=1.90,p=0.180,ηp2=0.07;分配比例的主效應顯著,F(xiàn)(1,26)=1419.97,p<0.001;社會分組信息和分配比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1,26)=0.57,p=0.455,ηp2=0.02(見圖7)。以上分析結果說明,被試對男性與女性提議者接受率的結果模式均相同,因此可說明吸引力并非解釋本研究結果的因素,回應者的反映差異確實反應了社會分組信息的作用。

圖7 提議者為女性時不同社會分組和分配比例下的接受率(M±SD)
4 討論
本研究采用最后通牒游戲范式,就決策中的追求公平問題進行了探討。結果發(fā)現(xiàn)當?shù)玫降慕疱X少于總數(shù)的30%,多數(shù)回應者(90%以上)會拒絕該分配方案,結果支持前人的觀點(Handgraaf,Van Dijk,Vermunt,Wilke,& De Dreu,2008;Hoffman,McCabe,&Smith,1996)。此外,在7∶3這個分配比例上,社會分組信息會影響人們對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而在其他分配比例上則沒有這種差異。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7∶3這個分配比例上,回應者做決策最為困難,因為需要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追求公平,從而需要更長的反應時間。據(jù)此,筆者認為7∶3這一分配比例具有轉折點的特性。在該分配比例上,回應者需要在獲得物質利益和對追求公平之間進行權衡,做決策最為困難,因此社會分組信息的影響顯現(xiàn)出來;而在其他分配比例上,都有明顯的偏向,回應者很容易做出拒絕或接受的決定。該結果也表明以后做相關的研究時可采用7∶3的分配比例作為研究變量。
前人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表明,由于相貌出眾的個體被認為具備更多積極的人格特質(Berry,1991;Dion,Berscheid,&Walster,1972),人們對其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更易接受。后續(xù)也有直接的實驗證據(jù)(Solnick&Schweitzer,1999)說明人們往往傾向于接受由面孔吸引力高的人提出的不公平分配,而拒絕面孔吸引力低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然而,本研究通過分析,排除了面孔吸引力的解釋作用,結果確實反映了社會分組信息的影響。筆者認為,本研究沒有發(fā)現(xiàn)面孔吸引力的作用的原因是由于在面孔吸引力和社會分組信息的雙重作用下,人們更多考慮的是社會分組信息。社會分組是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下,單獨生存是不可能的,只有被群體接納才有生存的機會。為了更好地在所從屬的群體內生存,會對該群體內的成員表現(xiàn)出更多的友好和合作行為(Stets&Burke,2000)。因此,社會分組在人們心中逐漸根深蒂固,影響到人們合作、公平等許多社會行為。
本研究探討了決策中社會分組信息對追求公平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公平行為具有社會分組信息的相對性。本研究的情景因素與已有研究僅局限于關注博弈雙方所具有的群體特性,后續(xù)研究可引入具體的決策情景,探討決策情景對追求公平行為的影響。此外,本研究與已有研究中,提議者和回應者均互不相識,但現(xiàn)實博弈中博弈雙方是相互熟悉或相互了解的,因此創(chuàng)造更符合現(xiàn)實的博弈情景,探討其對追求公平行為的影響也是十分必要的。
5 結論
本研究通過最后通牒游戲實驗,考察了社會分組信息這一社會關系中的重要特性對決策中人們追求公平行為的影響。結果發(fā)現(xiàn),回應者在分配比例為7:3時,社會分組信息會影響其對公平的追求,且在此情景下人們更能接受具有相同社會分組提議者的不公平行為,可見人們的公平感具有情景相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