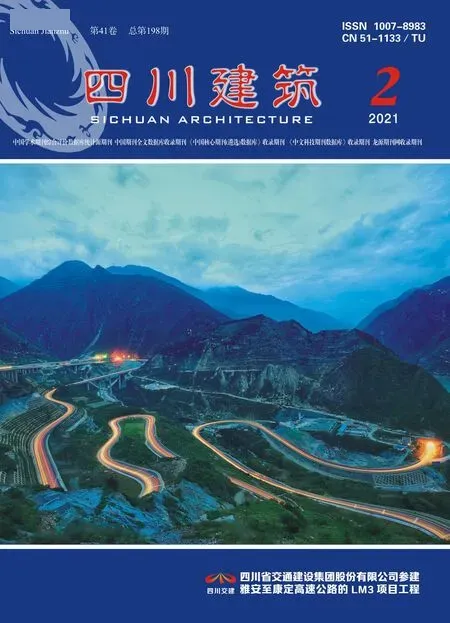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成都特色鎮發展策略及建設模式探討
沈莉芳, 李 果, 付 洋, 楊得草
(成都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94)
1 成都鄉鎮發展現狀及主要問題
1.1 成都鄉鎮發展現狀
成都市幅員面積1.43×104km2,共有116個鎮(含涉農街辦),鄉鎮戶籍人口約550萬人(2019年末),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432元(2020年)。截至目前,我市28個鎮入選全國重點鎮,數量列全國副省級城市第一位;郫都區德源鎮、三道堰鎮,大邑縣安仁鎮,龍泉驛區洛帶鎮4個鎮入選中國特色鎮,雙流區黃龍溪鎮等6個鎮入選省級特色鎮;36個鎮入選四川省“百鎮建設行動”試點鎮;27個鄉鎮入選國家、省、市歷史文化名鎮。
1.2 成都鄉鎮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成都自2007年獲批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縮小,現代農村產業體系逐漸形成,城鄉關系也發展到了“以城帶鄉”到“城鄉融合”的新階段。但因為歷史、經濟、制度等原因,鄉鎮發展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發展模式單一。有的鄉鎮盲目上馬古鎮搞仿古開發、有的鄉鎮過度開發自然資源搞旅游地產、有的鄉鎮為拉投資項目降低工業門檻等,造成許多鄉鎮面臨產業結構單一,生態環境不佳的問題;二是發展動力不足。許多鄉鎮陷入產業發展滯后→承載力小→人口外流→發展更加乏力的惡性循環,據統計成都近年年均勞務轉移輸出約260萬人,約占農村勞動力的63 %;三是資源要素整合不夠。典型如公共資源集約節約不夠,2019年底,全市650個場鎮社區中,常住人口4 000人以下的440個,占比68 %(全市鎮(街道)行政區劃調整和村(社區)體制機制改革“后半篇”文章),人口聚集度不高,場鎮公共配套設施利用效率低;四是體制機制不適應發展需要。現有的鄉鎮政府職能繁雜,既包括經濟發展職能,也包括公共服務保障及生態環境保護職能,導致了現有的工作重心分散,職能錯位、缺位、越位的問題較突出。同時因鄉鎮層級低,在土地、財稅政策方面對地方發展的支撐不足。
2 相關研究進展
2.1 鄉村振興理論研究
自從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學界掀起了研究“鄉村振興的熱潮,從目前研究成果來看,主要集中在路徑模式和對策辦法研究兩方面: 在路徑模式上,學者普遍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尺度和層次去探尋鄉村振興的內涵、鄉村振興的本質要求、主要目標內容進行研究探討,廖彩榮、陳美球[1]認為鄉村振興頂層設計是關鍵,需以鄉村振興規劃為統領,強化鄉村制度供給,緊抓“人、錢、地”三大核心要素,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在對策方法上,學者們圍繞國家鄉村戰略規劃,結合國內國際案例剖析,從宏、中、微觀深入開展了鄉村振興戰略對策、鄉村振興規劃體系及相關技術的研究,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指導性和可操作性。龍花樓、屠爽爽[2]從土地利用轉型與鄉村振興兩者之間的關系入手,認為鄉村振興帶來的生產要素流動,勢必帶來地域空間結構重構和土地利用形態的變化。
2.2 特色鎮相關理論研究
特色鎮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鎮是什么(即內涵、特征及意義),特色鎮怎么做(建設原則及方法路徑)兩大方面。在特征上,學者普遍認為特色鎮是鄉鎮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來源于產業、文化、體制機制方面的特色和競爭力。陳炎兵[3]認為特色鎮的特色包括產業特色、文化特色、風情風俗風貌特色和管理服務特色;在意義上,蘭建平和郭金喜認為特色鎮在促進區域聯動及帶動鄉村發展方面作用明顯,蘭建平[4]提出特色鎮的三大功能包括:促進產業集聚、提高小鎮知名度、提升地方經濟實力;在建設原則方面,盛世豪、張偉明則認為特色鎮應充分體現綠色發展的理念,注重創建和保持一流的生態環境,并應做好統籌規劃,避免一哄而上,陷入千篇一律的怪圈中;在方法研究上,吳一洲等學者[5]從五大發展理念出發,與產業緯度、功能緯度、形態緯度、制度緯度四方面形成評價框架,建立評價體系,著重強調產業“特而強”、功能“聚而合”、形態“精而美”、制度“活而新”。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鄉村振興和特色鎮本身的理論研究已相當成熟,但發展過程中如何將兩者的核心理念進行有機結合,并立足于現實情況推進城鄉融合,是當下成都特色鎮建設發展的核心要務,特別是亟須回答:如何發揮特色鎮的區域影響?如何尋找特色鎮有效的發展動力機制?如何針對不同的特色鎮針對性制定產業、文化、空間策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新格局、新動能、新發展、新活力”賦能成都特色鎮未來發展,推動特色鎮建設的提檔升級。
3 成都特色鎮發展策略
3.1 破舊立新,重塑城鎮發展新格局
一是打破原有行政邊界局限。通過以特色鎮為核心,建構城鄉融合發展單元的模式,提高鄉鎮管理效率,適應經濟單元跨區域布局需要。促進農民集中居住,實現服務集中、投入集中、資源集中,節約土地資源,為經濟建設、產業發展騰挪空間;二是打破鄉鎮傳統定位。以基于產業基礎與資源本底的特色產業發展,作為推動特色鎮發展的核心動力,營造空間適度、環境凈美、人員高知、社區和諧的新型功能體,以復合的功能定位支持國家中心城市建設;三是打破鄉鎮散亂布局。依托軌道線路和站點、高快速路節點等優勢資源,綜合考慮現狀發展基礎、人口規模、生態旅游資源等多方面因素,優化現有特色鎮布局。圖1為九個風景名勝區及龍泉山城市森林公園涉及城鎮。

圖1 九個風景名勝區及龍泉山城市森林公園涉及城鎮
3.2 多元植入,培育特色鎮發展新動力
一是植入輕資產、高附加、綠色化的新經濟產業,結合成都的生態資源本底條件和現狀發展基礎,積極引導旅游、商貿服務、文化創意、教育培訓、互聯網導向及新經濟資源向特色鎮聚集;二是植入高標準城市配套功能,通過提高教育、醫療、文娛等公共服務水平,鼓勵引入社會資本建設高標準的國際化學校、標準化醫院、綜合文化活動中心、標準化田徑場等公共服務設施,實現特色鎮資源要素、資本要素及人口要素的快速、規模化集聚;三是將天府文化作為特色鎮的“內核”,傳承巴蜀底蘊,彰顯“創新創造、時尚優雅、樂觀包容、友善公益”的文化特色。
3.3 統籌體系,推進城鄉融合新發展
一是以特色鎮建設為契機,整合鄉鎮小散弱的資源,圍繞特色鎮產業發展和建設需要,發展相應的配套產業,促進鄉鎮產業能級提升,形成互為支撐的城鎮體系格局;二是將特色鎮建設發展作為就近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加強特色鎮與周邊新農村之間互聯互通,形成以特色鎮為中心,周邊各具特色的林盤環繞的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體。讓新農村共享特色鎮發展機遇及技術、資金、市場優勢;三是以支撐區域功能建設為核心目標轉變傳統鄉鎮職能,根據“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全市戰略及全市66個產業功能區發展定位,確定各區域特色鎮功能定位(圖2),以產業錯位發展、互為補充為原則,融入全域成都產業布局和產業生態圈。

圖2 市域66個產業功能區布局規劃
3.4 改革創新,釋放特色鎮新活力
一是以資源整合和項目管理相結合的方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加快國土空間規劃背景下鄉鎮規劃編管審體制改革,以“城鄉融合發展單元”來統籌鎮鄉國土空間規劃與鎮、村詳細規劃,形成城鄉國土空間、資源信息、規劃管理協調共享的工作平臺。在城鄉融合發展單元規劃編制中,為促進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將以“總綱+圖則+項目庫”的管控方式來編制規劃。其中,“總綱”通過條文和圖集落實鄉村發展中的剛性控制;“圖則”以控規的方式將管控內容具體落地;“項目庫”設置“留白”機制,在不突破規劃剛性管控及預留指標的前提下,根據項目需求機動安排新增用地,動態化滿足鄉村地區發展要求;二是將建設用地指標集中于特色鎮,鼓勵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農民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入股,土地整理節約的建設用地以及農民的宅基地通過置換的方式,將建設用地指標集中于特色鎮;允許農民帶“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三權進鎮,引導要素向特色鎮聚集;三是拓展特色鎮建設融資渠道,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營”的原則,鼓勵國企、民企、外資等各類市場化主體及社會資本通過PPP(公私合營)、BOT(建設―經營―轉讓)、特許經營等商業模式,參與特色鎮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使特色鎮發展模式由“政府輸血”變為“市場造血”。
4 成都特色鎮建設模式
按照“核心帶動、資源整合”的思路,將交通聯系廣、產業關聯強、人員交流密切的多個鄉鎮為統籌對象,通過綜合實力評價、發展潛力評價、中心性、資源稟賦等分析,選出發展條件較好的鄉鎮作為核心(特色鎮),結合成都鄉村所獨有的“林盤”地貌特征,形成“特色鎮+林盤+農業園區”等三種類型的城鄉融合發展模式,將資源進行集聚整合,形成發展合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4.1 “特色鎮+林盤+農業園區”模式
在平壩和淺丘區域的傳統農業種植區,綜合考慮以現代化規模農業推動農產品加工、農事觀光體驗等關聯產業發展,采用“特色鎮+林盤+農業園區”的組織模式,該類模式規模一般在50~100 km2(圖3),其結構為特色鎮鎮區處于核心位置,周邊圍繞布局林盤,以林盤為支點帶動農業園區發展。此種模式下,特色鎮集中發展1~2種特色產業,鄉村地區則以規模種植、高附加經濟作物種植為主導產業。特色鎮對外交通主要通過軌道與高快速路實現,內部特色鎮與林盤間倡導慢行交通方式出行。生產與生活配套集中布置于特色鎮鎮區,規模較大的生活性林盤可布局部分基礎配套設施。

圖3 “特色鎮+林盤+農業園區” 模式示意
4.2 “特色鎮+林盤+景區”模式
在龍門山、龍泉山地區的鄉鎮,考慮到兩山地區生態保護及依托自然景區發展旅游服務的需要,采用“特色鎮+林盤+景區”的組織模式,該類模式規模一般在100~300 km2(圖4)。主要布局于兩山山腳區域,方便對外交通的同時,規避地質災害風險,通過縣鄉道及綠道聯系景區、景點,形成“山上游、山下住”的結構。此種模式以發展旅游業及配套服務業為主。特色鎮對外交通通過軌道與高快速路實現,特色鎮、林盤、景點間通過游道連接。生產與生活配套集中布置于特色鎮鎮區,部分交通便捷的林盤及景點可配置商業、應急救援等基礎配套。

圖4 “特色鎮+林盤+景區”模式示意
4.3 “特色鎮+林盤+產業園”模式
在城市近郊及產業功能區周邊鄉鎮,依托66產業功能區做好產業園區配套,采用“特色鎮+林盤+產業園”的組織模式,發展與產業園區密切相關的研發、文創等新興業態,該類模式規模一般在40~60 km2。特色鎮與產業園毗鄰分布,形成雙核結構,周邊圍繞布局多個林盤(圖5)。產業園發展相應的產業方向,特色鎮則承接產業園產業鏈功能外溢及配套生活生產服務功能。產業園及特色鎮對外交通通過軌道交通及高快速路網實現,特色鎮與產業園與林盤互聯互通。此種模式中,生產與生活配套相對分離布置,生產配套集中布置于產業園,生活配套集中布置于特色鎮,規模較大的生活性林盤可布局部分基礎配套設施。

圖5 “特色鎮+林盤+產業園”模式示意
5 結語
未來,成都應結合自身城鄉發展規律,緊抓“鄉村振興戰略”和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建立的歷史機遇背景,充分利用2019年獲批“全國城鄉融合改革試驗區”的契機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進城鄉融合新發展。對成都特色鎮建設發展來說,在宏觀層面上將真正實現承接中心城區外溢產業,吸納城鄉要素資源,提升產業發展能級,促進農村人口就近城鎮化。形成大中小城市和特色鎮產業協作協同,橫向錯位發展、縱向分工協作的發展格局。在中微觀尺度,應以特色產業發展為主線,挖掘文化內涵,重視發揮市場主體作用,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尊重個人的利益與訴求,同時應避免建設同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