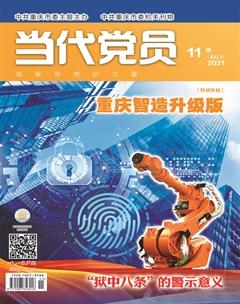稻田里的守望者
王雪 汪茂盛
每次進出重慶市農業科學院特色作物研究所,研究所黨支部書記、副所長,重慶再生稻研究中心主任李經勇總會想起一片稻田。那片稻田,就長在研究所旁。
多年前,水稻研發基地還在研究所附近,研究所與稻田,不過幾步路的距離。那時,李經勇最幸福的,便是在不經意間想起水稻的某個研發細節后,立即沖向稻田一探究竟。俯仰之間,他竟和水稻一起度過了一季又一季的時光。
“研發基地就在研究所旁,對科研人員來說,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李經勇沉醉其間。
而今,研發基地移到了鄉間深處,但帶給李經勇的幸福感絲毫不減——在那片稻田里,他帶領團隊育成的“渝香203”是重慶首個國頒二級優質雜交稻,由此結束了地處西南高溫伏旱區的重慶沒有高檔優質雜交水稻品種的歷史。
“這輩子,我就對水稻稍微懂一點。”李經勇說。
初與終:津津樂“稻”
一雷驚蟄,萬物復蘇。
開溝、擺秧盤、抹泥漿、撒谷種、蓋薄膜……種子播下去,又一個希望的春天開始了。
“最近氣溫較高,要及時給秧苗揭膜,免得秧苗被高溫烤死了。”李經勇穿著雨鞋,快步穿行于阡陌間。
春雨剛過,田坎泥濘不堪,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可李經勇卻走得又快又穩,鞋面還十分潔凈。
“從這里下田比較容易,也比較好操作。”話還沒說完,李經勇便翻過護網,一腳踩進了稻田里。與水稻打了幾十年交道,李經勇是懂稻田的。而這份懂,源于兒時的“餓怕了”。
20世紀60年代,由于物資匱乏、糧食產量低而導致的饑餓給童年的李經勇留下了深深的記憶。
“那時,農村主要種植早、晚稻及麥子,畝產很低,還時常接不上趟,我們不得不到處借糧維持生計。”李經勇說。
有一天,李經勇和大姐去井邊挑水,看著滿當當的井水,大姐突然由衷地感嘆道:“如果糧食能像這井水一樣,取之不盡就好了。”
正是這句話,讓不甘被饑餓折磨的李經勇下定決心:一定要讓農民多收三五斗糧食。
1989年,李經勇從西南農業大學(現西南大學)農學院畢業后,進入重慶市作物研究所(現重慶市農業科學院)工作,主要研究中稻、再生稻栽培技術和品種選育,就此與水稻結下了不解之緣。
初到研究所,李經勇每天不僅要面對復雜的科研試驗,還得下田收割稻子,腦力與體力雙雙受到考驗。
收割完第一季稻子后,李經勇提筆給家里寫了封信。
“現在我能將所學知識與工作有機結合。提高水稻的產量是我的人生理想,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在信中,李經勇如是說。
知與行:“稻”亦有道
春夏之交,稻田里的秧苗一天一個樣。返青后,秧苗逐漸分蘗,微風吹過,綠浪滾滾。
巡田時,李經勇總會帶上一根竹竿。他把竿往田里一插,秧苗生長的快慢、葉片的長短、植株的高矮便一目了然;他用竿撥動秧苗,其莖干質地、抗倒伏性和稻穗大小便了如指掌……
人、竿、稻,三者看似簡單,但要練就用竿一探便知稻的信息的本領,沒有日積月累的經驗和極高的悟性,是難以達到的。
李經勇與稻相伴,年年歲歲,早已深諳其道。
20世紀80年代,有關專家通過廣泛研究證明,重慶是典型的高溫伏旱區,不具備生產優質稻所需的氣候條件,便將重慶劃分為“劣質稻產區”,斷定重慶不可能生產優質稻。
“那時重慶所產的稻米被視為劣質米,既沒品相,又沒品質。”為改變這樣的狀況,1994年,李經勇和同事開始進行優質雜交稻研究。他說:“我想證明,在重慶也能種出高檔的優質稻。”
篩選資源材料是第一步,也是最難和最關鍵的一步。
在試驗田里種下的幾十萬株選種材料,每一株都是雜交后代中的唯一變數。要從這些材料中尋得最優單株,就得從苗期開始觀察、篩選研究。為此,李經勇時常“泡”在田里。
重慶夏季酷暑難耐,40攝氏度高溫是常有的事,人站在田里就像待在蒸籠中一樣。單季水稻抽穗一般在七八月,這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也是雜交工作最忙的時候。李經勇下一次田,往往一待就是幾個小時,衣服被汗水浸濕后,可直接擰出水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1998年,李經勇和同事在巡田時突然發現一株變異株。在成千上萬株材料中,這株材料不僅莖稈粗壯,結成的稻谷還格外吸引鳥兒,最重要的是,它所散發的稻香比其他材料都要濃烈。李經勇隱隱感覺到:“選育研究可能要有所突破了。”
經過一載又一載的室內組織培養、田間篩選及裂變,2002年,優質雜交水稻基本定型。2006年,“渝香203”通過重慶市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結束了重慶沒有國標二級高檔優質雜交水稻品種的歷史。2010年,國標二級優質雜交水稻“渝香203”通過國家審定。2020年,“高溫伏旱區高品質雜交水稻‘渝香203的選育及產業化應用”成果獲重慶市科技進步一等獎。
李經勇的“多收三五斗”糧食夢終于實現了。
“是我遇上了。”李經勇如是說。但這個“遇”,不是“偶遇”和“巧遇”,而是道盡了科研工作者在人與自然和科學之間,主觀認知和客觀存在面前,艱難抉擇的無盡感慨:沒有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遇不上;沒有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的意志,遇不上;不清楚農民需要什么,遇不上;不了解科技發展前沿,遇不上;沒有正確前瞻時代發展潮流,還是遇不上……多少育種專家窮其一生卻總是與最優化的那一株水稻擦肩而過。
濃與淡:為“稻”癡狂
夏去秋至,穗子越來越沉,該豐收了。
“唰唰”,鐮刀揮舞,稻禾齊刷刷倒下;“轟轟”,收割機轟鳴,金黃的谷粒迅速蹦出……如今,“渝香203”在全國推廣種植逾千萬畝,在云南、貴州、四川、廣西、江西和湖南等地也都已通過審定,可以大面積種植。這意味著,“渝香203”已實現從科學成果到農民應用成果的歷史性轉變。
這樣的成果,來之不易。
在品種選育過程中,由于重慶一年只能種一季水稻,為縮短育種年限,李經勇帶領團隊科技人員宛如候鳥,在重慶豐收后就立即趕往海南再種一季水稻,來年3月又回到重慶繼續播種,年復一年。
“上個世紀90年代去海南,只有火車,有時根本擠不上車。站了幾十個小時,實在堅持不住了,我們就躺在座位底下休息。”李經勇回憶,那時他們在海南沒有固定的基地,只能找農民租田地,風餐露宿。
兩只腳牢牢地站在稻田里,在沒有鮮花和掌聲時,李經勇始終守望著田野,守望著精神的天空。
對稻癡狂的李經勇,不僅奮戰在農業生產一線,同時也奮戰在科研一線。他先后主持、主研“水稻強再生力品種資源(材料)的引進與利用”、“再生稻高效生產模式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等各級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項目40多項,通過國家、重慶等審定的優良品種21個,鑒定“渝香813A”和“渝恢2103”等親本材料12個,獲得植物新品種權6個,獲國家授權專利6項。
搞科研,是個枯燥漫長且極其辛苦的工作,領導曾多次想讓李經勇從事相對輕松的管理工作,但李經勇想也沒想便拒絕了:“我不能丟下水稻科研工作,不能離開水稻研發團隊。”
與稻相伴32年,李經勇始終對稻愛得深沉。在李經勇和妻子的影響下,女兒也“子承父業”,在西南大學攻讀農學——那個糧食夢,穿越兩個世紀,在一家兩代人的胸膛里熊熊燃燒。
“讓農民多收三五斗糧食的夢想已經實現了,但如何讓人們吃得更好、更健康的研究還沒有停止,我一直在路上。”看著綠浪翻涌的田野,李經勇已為心中那樸素的夢想、深沉的愛找到扎根一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