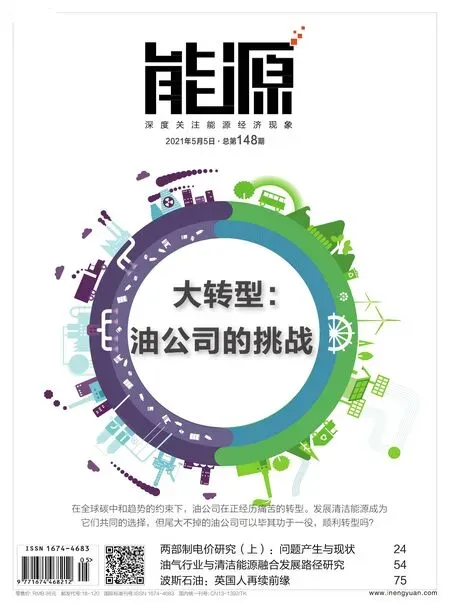碳中和目標將重塑金融資產估值體系
文 | 張仕元
作者系平安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高級業務經理
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這一概念隨著比爾蓋茨的新書《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的出版變成高頻詞匯。這一概念可以簡單理解為:在滿足消費者同等效用的情況下,可實現碳中和的新產品與仍產生碳排放的原有產品之間的價格差。兩者相比,新產品的價格越高,則綠色溢價越高。
作為曾經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經濟實力完全可以為自己遠超常人的碳足跡買單,從而踐行作為一位世界公民的社會責任。而身處于現實世界中的你我,如果每天仍然在為生計而奔波勞作;大多數消費者還在為買一件有基本功能即可的商品而多方比價;企業經營者堅持年復一年地在日益加劇的市場競爭中謀求生存,相信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每個“理性經濟人”,恐怕還不愿承受廣泛的“綠色溢價”。
同樣,在現實的金融世界里,資本也很少講情懷,達到預期的投資回報率才是投資人永恒不變的“冷血”要求。相應地,在金融市場中的債券、股票等標準化程度較高的金融資產也普遍存在“綠色溢價”,以作為對資產價值存在更高不確定性的風險補償。
金融產品的“綠色溢價”在降低
綠色金融近年來開始步入發展的快車道,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通過開展綠色信貸、發行綠色債券等方式支持綠色產業發展,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綠色金融市場。截至2020年末,綠色貸款余額近12萬億美元,存量規模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8132億元,居世界第二。
步入2021年,在“30·60目標”指引和政策推手下,國內大型金融機構和央國企積極搶抓債券發行窗口,中國首批“碳中和債券”也應運而生。截至目前,我國已發行48只碳中和債券,發行規模合計達692.2億元。從債券發行人主體來看,34只債券發行人主體為央企,5只為地方國企;9只為政府投融資平臺。
從已成功發行債券的價格水平來看,碳中和債比相同期限普通債券利率較低,債券的“綠色溢價”似乎已經降至0甚至負值。但如果進一步分析造成近期綠色債券的“綠色溢價”消失的原因,究竟是因為金融機構在當前貨幣政策相對寬松的環境下,對高信用等級債券的爭搶所形成的短期價格波動,還是基于對募集資金投資標的長期認可,仍有待市場檢驗。
從推動綠色金融健康發展來看,筆者建議:監管機構應加強對綠色債券的審核,完善并統一綠色債券的認證標準,同時對綠色債券所融得資金的用途進行監督,加大對企業“漂綠”行為的處罰。同時,應在債券需求方出臺相關政策,鼓勵投資者投資綠色債券。
氣候變化“灰犀牛”顯形
在去年世界各國元首提出“碳中和”目標之前,氣候變化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少數極端環保人士鼓吹的“陰謀論”,從提出之日起質疑和反對之聲不斷,這些聲音中既有代表傳統化石能源的利益集團,也有對地球自然生態的自我恢復能力有“十足”信心的理論家。
然而,隨著近年來“百年一遇”的自然災害頻發,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的一次又一次損害直接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規模更大、范圍更廣的傷痛,國際社會終于在徘徊中達成了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世界各國必須制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和時間表,并早日實現“碳中和”。
在金融投資領域,風險管理領域的著名學者對可能影響金融市場的極端風險有幾類很貼切的比喻:“黑天鵝”指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灰犀牛”指太過于常見以至于人們習以為常的風險,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相比之下,“灰犀牛”比“黑天鵝”更可怕,更值得關注。
在世界范圍內對應對氣候變化達成共識背景下,氣候變化不再是難得一見的“黑天鵝”,這只一直潛伏在人類社會身邊的“灰犀牛”已輪廓清晰,并隨著倒計時的啟動開始徐徐迫近。氣候變化,這個足以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實質性影響的系統性風險確實來了,未來還將與全球碳中和的進程直接相關。
金融機構的兩難困境
金融機構對金融資產的定價,本質上是對各類型金融資產所對應風險的定價,當前金融市場上被廣泛應用的主流定價邏輯是“風險與收益對等原則”,即收益以風險為代價,風險用收益來補償,簡而言之就是“高風險,高收益;低風險,低收益”。
盡管氣候變化將對金融資產價值構成實質性影響的觀點,已被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所認同,但如果無法準確量化氣候變化的風險,也就無法給予公允的風險定價。究竟是應該盡可能考慮到氣候變化所導致最壞的情況,還是只基于當前能夠預計和量化的成本/損失評估風險,甚至選擇性忽視無法量化的部分,成為金融機構風險管理人員在實踐中面臨的兩難選擇。
國家綠金委主任馬駿博士多次建言:金融機構應高度重視氣候變化給金融資產帶來的風險,而發展綠色金融也將帶動數十萬億的投資機會。為此,“金融機構要開始注重對氣候轉型風險的理解和估算”,另一方面“對金融機構來說,如果不參與這個過程,就會失去最大的投資和業務增長機會。”
金融機構對各類金融資產進行風險評估,量化方法會因資產類型和風險類型而定,通常情況下,信用風險主要看違約概率,市場風險主要研判市場價格波動,對資產組合的風險評估還會用到相對復雜的二叉樹、神經網絡、蒙特卡洛模型等。氣候變化此前通常被認為是很小概率發生的極端事件,只有到“壓力測試”的時候才可能套用一些極端場景進行模擬計算。
針對氣候變化風險進行評估的 “壓力測試”方法,主要是通過模擬金融市場的極端情況,量化計算各類資產價格和風險參數的變動,進而估算出可能給機構持有資產的價值和現金流帶來的最大損失值。但是,壓力測試所設定的情景多數是基于歷史上發生過的極端情況,而對全球氣候變化這個“不能承受之痛”還沒有可供參照和完全匹配的場景。
低碳時代的資產估值需要創新
站在實業投資的角度,實體企業所推動的新興技術幾部在發展路徑上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觀規律,當前與低碳發展相關的新興產業和能源清潔化技術,多數還未真正進入產業發展的穩定成熟期,與傳統高碳產業相比,不僅在成本上不具備競爭優勢,技術上也不具有穩定性,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所隱含的風險使得投資人對投資回報率提出更高的要求,最終反映在金融產品上的“綠色溢價”。
金融投資的對資產價值的評估主要是基于未來現金流折現(DCF)模型,這個模型中有3個最為核心的輸入項:初始投資,未來的凈現金流,折現率;模型的輸出項有2個:凈現值(NPV)和內部收益率(IRR)。而資本所要求的投資回報率,在金融機構的具體實踐中一般會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并參考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風險水平而進行設定。
在上述估值體系的框架內,低碳時代對估值模型的假設、模型的輸入和輸出項所帶來的新變化需要根據市場環境進行相應調整,基于模型所得出的投資價值分析和資產配置策略也需要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做出合理的設定,從而更好地踐行價值投資的原則。
筆者嘗試在當下主流的金融投資估值體系框架內,對在資產估值中踐行ESG投資理念的提出幾點創新性的思考:

1.將項目的綠色權益收入納入到對未來現金流、初始投資的估算和調整。在運用未來現金流折現模型時,可以將項目資產未來可形成的綠色權益(包括但不限于碳配額、CCER、綠證)按合理價格折算為每期的現金收入;此外,如果通過實施低碳相關的投資可有效降低項目所面臨的氣候風險,可以將氣候風險的保險費(實際未發生)以市場價格在初始投資中做適當核減。
2.將項目“綠色溢價”所對應的內部收益率折算為投資回報率的調整項。隨著低碳清潔技術的不斷進步,低碳產品相比高碳產品的“綠色溢價”有望在不遠的將來將降至0,屆時低碳產品將基本實現對高碳產品的完全替代。在上述情景下,低碳項目相比高碳項目在期初的超額投資,未來將通過對高碳產品完全替代的方式實現收入增加并給投資人帶來增量投資收益。相應地,期初的超額投資、未來增量收入所折算出的內部收益率,可以作為對原有項目投資回報率的增加項。
3.在對公司的股權估值中,對高碳產業、低碳產業采用符合發展趨勢的股利增長率。在碳達峰碳中和的總體目標指引下,高碳產業的增長放緩甚至進入停滯和負增長已成為必然的趨勢,低碳產業則有望實現長期穩定增長甚至指數級增長。在運用戈登股利增長模型進行估值時,可以考慮基于所在行業碳達峰的時間表,對高碳產業的增長率設為0或負值,對低碳產業則可以采用較高的潛在增長率。
筆者以上所提出的改進方法,仍然是在既有金融資產估值體系下對原有經典模型所進行的補充和調整,但當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撼動了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僅通過調整模型自身的輸入項和參數是無法合理反映客觀實際的。未來隨著碳中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相信還會有更加符合實際的理論模型和估值方法被提出,更好地指導金融資產定價和投資估值。
重塑綠色金融
氣候變化對全球各行業的影響將是長期和深遠的,金融行業作為驅動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之一,在這場事關人類命運的系統性變革中無疑也將面臨全新的挑戰。金融投資估值體系發展至今,始終與實體產業的發展與時俱進,估值方法和投資模型也兼具科學性與藝術性,可以豪不夸張的說:估值不僅是一門技術,更是一種藝術。低碳時代,估值藝術值得為更好地塑造可持續的未來而進行創新和變革。
人類社會構建綠色低碳的未來,除了依靠科學技術進步,也需要有戰略眼光的資本助力;金融資本只有更加積極的面向未來,才有可能通過健康的資產配置獲得可持續的價值增值。金融機構要與時代同行,與實體產業一道共同重塑對綠色低碳產業的投資估值體系,在3060目標的引領下,做有溫度的金融,實現從“綠”到“金”,而這也恰好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論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