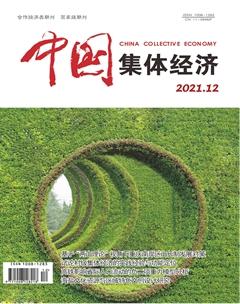鄉賢資本返鄉與鄉村產業振興的新路徑
李建民 李丹
摘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產業振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和工作重點。資本下鄉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關鍵,目前學界針對資本下鄉的研究,政府資本下鄉與工商資本下鄉是主流。文章基于對浙江義烏何斯路村的實地調研,提出了鄉賢資本下鄉作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新路徑,以期為實現鄉村產業興旺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鄉賢資本;產業振興;鄉村振興
一、問題的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講到,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必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我們黨和政府一向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自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已經連續15年關注“三農”問題的解決。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將這一問題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把產業興旺放在了實現鄉村振興總要求的首位。2018年3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提出,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從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5個方面著手,產業振興同樣被放在首位,由此可見,產業振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
目前我國鄉村缺乏產業的支撐,“沒有產業,中青年農民就不可能留在村里,村里就只能以留守群體為主” ,從而農村呈現嚴重的空心化,陷入發展的困境。盡管人們在進行著關于振興農村產業的多種路徑嘗試,有待于找到一個可供借鑒、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作者通過對何斯路的跟蹤調研,發現何斯路十年的經驗探索為我們提供了鄉賢資本下鄉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這樣一種新路徑。在何斯路村發展中,鄉賢返鄉形成抱團合作,成立股份合作社發展旅游產業,由此帶動村民間的合作,合力解決了其產業發展空殼化的問題。本文僅就何斯路的發展路徑進行進一步思考,深入分析其利用鄉賢資本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內在機制,探討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真正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的新路徑。
二、資本下鄉的路徑與困境分析
產業振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資本下鄉是鄉村產業發展的關鍵所在。通過對資本下鄉的研究,目前學界主要呈現了以下兩條路徑。
(一)政府資本下鄉
政府主導鄉村產業發展是一種自上而下為鄉村注入發展資源的方式,折曉葉、陳嬰嬰認為項目進村是“自上而下資源輸入”振興道路的基本表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農業生產經營和農村社會服務等領域,國家以項目制為手段提供大量資源 ,田園綜合體是項目下鄉的典型。在這種模式下,項目資源輸入的規模、大小和類型決定了鄉村發展的效果,資源輸入與鄉村發展之間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關系 。而且在項目建設過程中,掌握體制資源的村組干部更容易利用體制身份優先占有獲利機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主導進行項目輸入為鄉村帶來了資金、技術與人才,但是依靠資金注入的項目缺乏可持續增長的動力,并且普通村民沒有利益可獲得。
(二)工商資本下鄉
工商資本經營,是以土地流轉入股為手段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打造鄉村特色產業經營體系,以外源性的工商資本主體帶動農民參與市場化、資本化的農業產業經營方式 。資本下鄉有兩種形式:一是工商資本參與以“農民上樓”為主的土地綜合整治項目,作為投資方獲得節余建設用地指標出讓的收益;二是工商資本大規模轉入農地,幫助基層政府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大力發展現代農業 。學者普遍認為工商資本下鄉促進產業振興是弊大于利。楊磊、徐雙敏認為工商資本的注入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社會資源稟賦不足的難題, 然而由于這種模式資本外源性的屬性, 產生了對“小農”的排斥問題, 出現了資本主體與普通農民的利益不兼容現象 。張良認為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鄉村治理中“權力—資本”利益共同體的發展違背了農民的公共利益 。焦長權、周飛舟指出工商資本下鄉投資農業是為房地產開發等非農盈利項目做鋪墊, 其在農業經營上并無效益。因此,學界所提倡的工商資本下鄉與農民利益是不相容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振興鄉村。
總之,政府資本與工商資本下鄉都旨在解決鄉村產業發展的問題,但在實踐過程中遭遇了不同的困境。鄉村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資本的注入,政府利用政策指引帶動項目下鄉,在實施過程中無法真正嵌入當地村莊,盈利也不能直接到達村民手中。工商資本下鄉追求利益最大化,產業建設過程中使村莊整體搬遷。去農化的鄉村建設,對于村民來說沒有任何利益保障可言,這樣對村民無益的資本是不可取的。
三、鄉賢資本下鄉的路徑與機制
在傳統社會,鄉賢作為一個特別的群體在引領社會發展、治理農村方面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四十年,每個村莊都有走出去的人,他們年輕時為了生計離開家鄉,經過在城市多年努力打拼,收獲了人生的成功,成為新鄉賢。改革講先富帶動后富,鄉村振興要充分利用好這一部分人的力量。鄉賢們對于自己的家鄉有深厚的情感,鄉賢返鄉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而鄉賢所帶回的資金、資源、人才與技術正好滿足了鄉村發展的需求。
(一)鄉賢資本下鄉的情感認同
鄉賢依附強烈的親緣、地緣與血緣關系而生長,對鄉土社會有著深深的依戀。面對何斯路產業發展空心化、村莊處于負債狀態的現狀,何斯路的發展首先要解決資金來源的問題,而鄉賢資本的注入成功解決了這一難題。鄉賢資本不是物質的,飽含了鄉賢對村莊情感與文化的認同。鄉賢“回歸鄉村,將知識和產業帶回鄉村,成為鄉村社會的支撐。他們有著濃厚的鄉愁,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鄉村有著不可割舍的依戀”。因此,鄉賢資本的下鄉不以利益為主導,更是基于情感認同的回歸。
何書記自己拿出100萬元進行土地流轉。面對何斯路土地面積小且不集中的現狀,要進行薰衣草園的建設,先要把土地集中起來。目前土地零散分布在各戶村民手中,何書記想到借助大戶進行流轉,先將錢分到大戶手里,把土地從小戶流轉到大戶再到村集體。村集體成為農戶土地的轉入方,土地由村集體統一經營,農民把土地轉租給村集體從中獲得租金,規避了經營風險。
在投資何斯路發展的十年中,通過訪談了解到,鄉賢投資至今未獲得過股權分紅。在多數人的眼中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為什么鄉賢能忍受多年沒有收益的事實呢?
事實如此,鄉賢投資以情感為出發點,他們從小在村子里長大,有著對村里親情、鄰里情甚至愛情的回憶,這種回憶是最深處的對于家的強烈情感,這種情感是支撐鄉賢返鄉的重要精神力量。如一位鄉賢所講,即使沒有收益鄉賢內心依然是認可的。不同于工商資本純粹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是沒有感情的賺錢機器,鄉賢資本是有情感的寄托。在鄉村產業振興中,需要的就是鄉賢這樣帶著反哺村民的心,不以利益為最大化的資本下鄉。
(二)熟人社會中的鄉村產業運營
我國農村社會是熟人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基于農村熟人社會所構建的社會網絡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網絡, 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體現為感情、關系、規范和機制等層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會成了一張微觀權力關系網 。鄉賢從小在村里長大,熟悉鄉土社會的人情關系,在鄉村產業發展及管理中,會根據鄉村熟人社會的特點進行調適,站在村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
鄉村酒店是何斯路的主要產業。鄉村酒店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員工的本土性,而作為酒店的管理者,首先要學會處理好員工與村民雙重角色的轉換問題。酒店運營初期,為了酒店的規范化發展,酒店的管理人員是外聘的,外聘經理有著專業的酒店管理知識、豐富的酒店管理經驗,能夠引領酒店斯路何莊的規范化發展。但是,斯路何莊是一個鄉村酒店,它不同于城市酒店的管理,嚴格規范的管理制度在鄉村酒店是行不通的。因此,外聘經理的專業性在鄉村酒店沒有用武之地。
產業發展與村莊村民是分不開的,拿酒店餐飲來說,村里的紅白喜事、宴請客人大多從何莊訂餐。作為酒店的經理,就要十分了解村里的情況,評估訂餐家庭對費用的承擔情況,給與適當的折扣。臨近過年的時候,還有家庭主動詢問年夜飯的預定,酒店會根據村民的需求提前制定好年夜飯套餐,供人們進行參考選擇。現在村里整體經濟狀況確實變好了,整個村民的訂餐每年會帶動消費十幾萬元,可以說整個酒店的運營,離不開全民營銷全民支持。如同陳經理所講,何斯路整個村莊村民與它的產業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共同的目標就是使何斯路發展好,從而實現村民生活富裕。
鄉賢內生于村莊這一熟人社會,清楚了解熟人社會的人情規則,“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有人違背這一人情準則,那些在人情關系中有所失誤的人,人情對方和人情關系網都會對其進行疏遠” ,鄉賢生長于村莊,即使離開家鄉在外發展多年,依然深諳鄉村人情所帶來的利與弊。基于鄉村熟人社會這一特質,在鄉村產業發展中,會更多考慮村民的利益,正是這一特質使得鄉賢資本促進產業振興農民富裕成為可能。
四、總結與展望
何斯路產業發展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經驗,首先鄉賢資本下鄉重新發現鄉村價值,在鄉村生態保護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發展為可以增值的資本造福村民。其次鄉賢在鄉村熟人社會中管理經營產業,村民參與獲益其中。最后鄉村產業發展將原子化的個人重新集聚到一起,重建鄉村公共生活,增強了村民的鄰里感情。本文充分證明了鄉賢基于對鄉村情感的認同而返鄉,不以利益最大化為導向來發展鄉村產業,從而使村莊變好使村民變富裕的事實,而這也正契合了鄉村振興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鄉賢資本下鄉主導鄉村產業振興不同于政府資本、工商資本下鄉對村民的排斥性,它是作為村莊內生力量的支持,為全國各個村莊的產業發展提供了一個模板。改革開放四十年,每個村莊都有鄉賢產生,他們客觀上有能力,在城市打拼多年,擁有鄉村發展所需要的資本、人才、資源、技術等要素。主觀上有熱情,對于家鄉有著強烈的鄉愁與鄉情,愿意返鄉為家鄉發展做貢獻。因此,新時代鄉村產業的發展要積極引導鄉賢返鄉,發揮鄉賢資本的積極作用,從而增強農民的主體性,真正實現農村美、產業興和農民富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姜長云.推進產業興旺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J].學術界,2018(07):5-14.
[2]申端鋒,楊盼盼.適度積極:鄉村振興的路徑優化[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8,20(05):70-75.
[3]折曉葉,陳嬰嬰.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和治理邏輯——對“項目進村”案例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1(04):126-148+223.
[4]賀雪峰.論利益密集型農村地區的治理——以河南周口市郊農村調研為討論基礎[J].政治學研究,2011(06):47-56.
[5]陸文榮,盧漢龍.部門下鄉、資本下鄉與農戶再合作——基于村社自主性的視角[J].中國農村觀察,2013(02):44-56+94-95.
[6]周飛舟,王紹琛.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城鎮化的社會學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5(01):66-83+203.
[7]楊磊,徐雙敏.中堅農民支撐的鄉村振興:緣起、功能與路徑選擇[J].改革,2018(10):60-70.
[8]張良.“資本下鄉”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公共性建構[J].中國農村觀察,2016(03):16-26+94.
[9]焦長權,周飛舟.“資本下鄉”與村莊的再造[J].中國社會科學,2016(01):100-116+205-206.
[10]張勁松.鄉愁生根: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鄉村振興的實現[J].江蘇社會科學,2018(02):6-16
[11]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12]陳柏峰.熟人社會:村莊秩序機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會,2011,31(01):223-241.
(作者單位:李建民,山東曹縣農業農村局;李丹,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