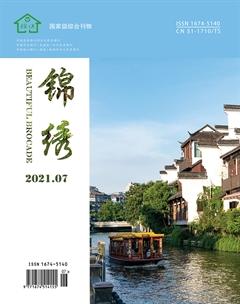孔子文論思想淺探
摘要:中國文化軸心時代思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該時代的杰出代表——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為后人留下了眾多精神財富。作為中國文論的領路人,孔子的文藝理論思想極具開創性意義。他提出文藝的最高理想是“盡善盡美”;文藝的社會功用是“興”、“觀”、“群”、“怨”;文學批評的準則是“思無邪”。本文就以上觀點加以分析,淺探孔子文論。
關鍵詞:孔子;文論思想;盡善盡美;興、觀、群、怨;思無邪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axis age though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is era, Confucius, the founder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left a lot of spiritual wealth for later generations. As the leader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onfuciu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of great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He proposed that the highest ide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perfection";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re "prosperity", "outlook", "group" and "resentment". The maxim of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ink innocen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bove viewpoints and probes into The literary theory of Confucius.
Key words: Confucius; Literary theory; As good as it gets; Xing, view, group, resentment; Think innocence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人才輩出、思想迸發的時期,融入于中華民族血脈的儒家思想文化就誕生于該時期。要追根中國文學精神,溯源中國文論脈絡,探尋孔子的文藝理論思想不可或缺。
孔子(公元前551 ——公元前479 BC)不僅在思想、教育、政治等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他在文藝理論方面也頗有見地。在《論語》中孔子的文論思想得到了集中體現,與老莊、荀子、孟子等文論家思想共同構成中國文論思想之濫觴。孔子的“盡善盡美”、“興”、“觀”、“群”、“怨”、“思無邪”等思想是其文論思想的核心內容,對后世文化和文論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文藝的最高理想——“盡善盡美”
“詩言志”與“詩緣情”是中國古典詩論中的兩大重要命題,幾千年來關于二者的討論從未停歇。相較于誕生在魏晉時期的“詩緣情”理論,“詩言志”思想流傳時間更為悠久。“詩言志”始見于《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1]這段記舜的語句首次點明了詩是抒發作者志向之作。荀子受其影響曾談到:“《詩》言是其志也。”莊子也曾發表過“詩以道志”的觀點。同樣,孔子也繼承并發揚了“詩言志”的觀點,從《論語·先進》侍坐章中孔子觀子路、曾點、冉有、公孫華的“志”這一內容可以看出,孔子將“志”所表現的含義從思想志向具體成了政治抱負。
同時,在《論語》第三篇《八佾》中曾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2]孔子在評論《韶樂》時談到:“《韶樂》在節奏韻律層面和表達內容層面已然盡善盡美。”評論《武樂》時卻說:“《武樂》在節奏韻律觀賞性層面已然表現的十分優異,但在歌舞表達的內容層面上還是稍有不足。”
《韶樂》,又稱《舜樂》,是為歌頌舜帝而作的及詩、曲、舞為一體的國樂。《中庸》中曾記載過這樣一段話:“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3]孔子對舜帝的“仁、和”的治國方略以及對舜帝本人的“禮”、“孝”都極為推崇,因此對歌頌舜帝的《韶樂》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也曾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武樂》為歌頌周武王而作。《漢書·禮樂志》中曾談到:“武王作武。武,言以功定天下也。”[4]武王伐紂,以殺伐定天下,因此《武樂》殺伐之氣重,有未“盡善”的遺憾,而舜帝以禪讓得天下,兵不血刃,為政以“和”,因此《韶樂》“盡善”、“盡美”。
孔子將藝術“美”和“善”的概念加以區分,且在此基礎上,他還要求在藝術中把“美”和“善”統一起來。孔子認為,藝術可以安撫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修養。但是并不是所有藝術都對人有這種作用,只有符合“善”、體現“仁”的藝術才能起到這種作用。所以,孔子強調文藝的最高理想應是將“美”與“善”相統一,藝術在形式“美”的同時也要擁有符合“善”的要求的道德內容。
二、文藝的社會功用——“興”、“觀”、“群”、“怨”
孔子十分重視文藝的社會功用。《論語·泰伯》篇中談到以“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5]的個人修養發展過程。孔子肯定了文學與音樂對人的品德修養的積極作用。孔子對文藝的社會功用的理解在《論語·陽貨》篇中體現的則更為全面,他曾談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6]在這里孔子提出了著名的“興、觀、群、怨”理論。
1、《詩》可以興
“興”可以理解為詩歌用比興的手法創造出生動感人并蘊含著某種普遍真理的藝術形象,從而感染接受者的情緒,激發接受者的意志,使其精神激動并從中中受到正面的影響和教育,即詩的審美教育功用。同時在文學接受過程中,接受者的想象和聯想活動與詩歌的審美形象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詩歌的鑒賞過程中人可以獲得來自于詩歌所提供的美的享受。如:最經典的例證《詩經·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詩》可以觀
所謂“觀”,鄭玄注為“觀風俗之盛衰”。指的是詩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接受者可以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了解社會的風俗的興衰,考察政治的得失,即詩歌的認識功用。詩歌的欣賞活動是一種認識活動。“觀”還有另一層涵義,即“觀志”,即從詩中看出詩人之志,以及讀詩誦詩人之志。可以說,詩可以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通過閱讀詩歌可以穿越千載光陰了解該時代的社會歷史。如:“建安風骨”、“正始之音”、“盛唐氣象”等等都在詩歌中有所體現。
3、《詩》可以群
“群”,是指文藝可以使接受者溝通感情,相互交往切磋,在和諧的環境下共同提高,即發揮文學藝術的倫理功用。人在這種相互友好的溝通交流環境下,進而產生認同感從而有利于社會穩定,使社會保持和諧。詩是與人交往的橋梁與紐帶歷史上不少詩人就是以詩交友,留下了很多彼此唱和的千古佳作,如:高蟾的“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韋莊以“誰謂傷心畫不成?畫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滿故城。”相和,以為經典。
《荀子·樂論》有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7]“樂”同“詩”一樣也能夠起到倫理教化的作用,居于宗廟的音樂反映了民族集體的情感,比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還有《黃河大合唱》、《國際歌》均引起廣泛共鳴。
4、《詩》可以怨
“ 怨" 為“刺上政也"(孔安國注)。“怨”,即指“怨刺上政”,即批評、指責執政者在社會政治方面的得失,即發揮詩的社會批判功用。凡是對現實的社會生活表示一種帶有否定性的情感都屬于“怨”。“可以怨”,意味著詩歌可以引起接受者對于社會生活的一種情感態度。詩可以針砭時弊,直指某些惡劣的社會風氣,甚至可以對政治環境產生影響。無論是先秦的《詩經》、《楚辭》,還是后世的詠史懷古詩都時常借古諷今、批判現實的不公與黑暗。如:唐代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再如:元代張養浩《山坡羊 · 潼關懷古》“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孔子的“興觀群怨”學說的詩教理論系統地闡釋了文藝的審美教育作用、認識功用、倫理功用以及社會批判功用。文藝審美功用的提出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不可否認的是,“興觀群怨”學說一方面體現出了孔子思想的鮮明特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其思想的局限性:除“興”之外,“觀”、“群”、“怨”的思想皆與政治相關,從“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可以看出孔子過分強調文藝應服務于政治,盲目的強調文藝的政治功能。
三、文學批評的準則——“思無邪”
《論語·為政》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8]這是孔子評詩最著名的觀點,也是孔子文學批評的準則。孔子認為,《詩經》用一句話概括即為思想純正、毫無邪念。“思無邪”的觀點從審美層面分析可以說就是對"中和"之美的倡導。“無邪”即為不過“正”,切合“中正”,即“中和”。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贊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9]他認為藝術包含的情感必須是一種有節制的、有限度的情感。這樣的情感符合“禮”的規范,才是審美的情感,這里也體現出了孔子“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中庸思想。《論語·雍也》中曾談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10]孔子在論“文”、“質”關系中強調內容不可以超越外在形式,外在形式顯然也不可超越內容,文藝作品只有把內容與形式相統一才能達到“思無邪”的標準,展現出“中和”之美,該思想時至今日依舊對中國的文學批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姚小鷗. 關于上海楚簡《孔子詩論》釋文考釋的若干商榷[J]. 中州學刊, 2002(03):43-45.
[2]蒲友俊. 孔子文論淺議[J].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9.
[3]王云亮, 劉金同. 淺談孔子對我國古代文論的影響[J]. 中華素質教育, 2005, 000(006):100-101.
[4]李啟榮, 張智淵. 淺論孔子文論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特征[J]. 昭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0(04):36-39.
[5]牟鐘鑒. 論孔子的中和之道與當代溫和主義[J]. 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 2013.
[6]李啟榮, 張智淵. 淺論孔子文論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特征[J]. 昭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0(04):36-39.
作者簡介:
焦韻晗(1997-)、女、山東濟南人、漢族、 碩士研究生、 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 研究方向:中國美學及文論.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