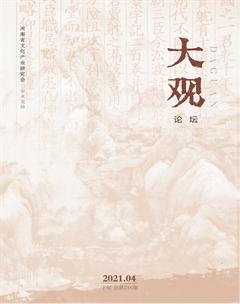十卷詞曲百家味,香溢人間
馬行月
摘 要:音樂(lè)與文學(xué)之間的聯(lián)系年深歲久,從先秦時(shí)期至今,詩(shī)與樂(lè)同氣連枝,形成詩(shī)歌藝術(shù),這當(dāng)中的奇奧值得我們探尋。在中國(guó)上下幾千年的歷史長(zhǎng)河里,許多音樂(lè)家和文學(xué)家踵事增華,使詩(shī)歌藝術(shù)積厚流光,卓然地立于時(shí)代的舞臺(tái)。音樂(lè)與文學(xué)皆是文化瑰寶,二者孕育的果實(shí)成熟飽滿,我們將其篩選再摘下,釀成美酒伴隨未竟之旅。
關(guān)鍵詞:詩(shī)歌藝術(shù);文人音樂(lè);文學(xué)素養(yǎng)
詩(shī)歌由文學(xué)精煉生產(chǎn),音樂(lè)再加工賦予靈魂,相得益彰,表達(dá)人的情志亦反映社會(huì)現(xiàn)象。子曰:“興于詩(shī),立于禮,成于樂(lè)。”詩(shī)歌是人的精神源流,又和人一樣有著不同的命運(yùn),探尋詩(shī)歌的起源、發(fā)展與現(xiàn)狀,路過(guò)古代先人們的前世今生,我們會(huì)更加充滿敬仰。
一、詩(shī)歌的發(fā)源與進(jìn)化——發(fā)軔之始
在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與音樂(lè)關(guān)系緊密,演化出詩(shī)歌這一藝術(shù)形式。《尚書》曰:“詩(shī)言志,歌永言。”漢語(yǔ)中“詩(shī)歌”一詞也直觀反映了詩(shī)與歌、文學(xué)與音樂(lè)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中國(guó)現(xiàn)存最早的漢語(yǔ)詩(shī)歌總集為先秦時(shí)期的《詩(shī)經(jīng)》,這是中國(guó)古代詩(shī)歌的光輝起點(diǎn),具有歷史標(biāo)志性意義,也基本確定了中國(guó)古代詩(shī)的格式。《詩(shī)經(jīng)》中四言詩(shī)習(xí)見,五言詩(shī)少有,以抒情詩(shī)為主,委婉含蓄,相比于直接的敘事詩(shī)更具有藝術(shù)性。《詩(shī)經(jīng)》常常運(yùn)用疊字和疊韻的手法,疊字可達(dá)視覺上的層序分明,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疊韻以求聽覺上的抑揚(yáng)頓挫,例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詩(shī)經(jīng)》中的詩(shī)篇配有曲調(diào),為西周至春秋時(shí)期的民間百姓吟唱。后人收錄詩(shī)歌,編成總集,并一直被延續(xù)下去。
《論語(yǔ)》有云:“詩(shī),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shī)歌在當(dāng)時(shí)具有教育作用和社會(huì)價(jià)值,值得傳述和歌詠。戰(zhàn)國(guó)后期的《楚辭》為劉向輯錄而成,是中國(guó)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源頭。《楚辭》中大部分是可唱歌詞,內(nèi)容以屈原的作品為主,但也記錄當(dāng)時(shí)的人文生活和時(shí)政要事。其態(tài)度激蕩,語(yǔ)頗雋永,如“長(zhǎng)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和“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值得尋味。
到了漢朝,官方音樂(lè)機(jī)構(gòu)——漢樂(lè)府,開始搜集整理詩(shī)歌,并編輯成集用以配樂(lè)歌唱。其中《木蘭詩(shī)》與《古詩(shī)為焦仲卿妻作》贊譽(yù)最盛,即《木蘭辭》與《孔雀東南飛》,合稱“樂(lè)府雙璧”。漢樂(lè)府以五言詩(shī)為主,發(fā)展至東漢末年成熟,促進(jìn)了文人五言詩(shī)的興起,開辟了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新形式。文人五言詩(shī)經(jīng)典《古詩(shī)十九首》見于《昭明文選》,這時(shí)的詩(shī)歌趨于文人化,具有較為明顯的文學(xué)性。
二、文人音樂(lè)欣欣向榮——承前啟后
文人音樂(lè)伴隨士階層出現(xiàn),到后世,士即是文人。文人音樂(lè)包括古琴音樂(lè)和詞調(diào)音樂(lè),文人作詞也譜曲,類型豐富。與通俗的民間音樂(lè)不同,文人音樂(lè)表達(dá)的是古代知識(shí)階層的理想信念和氣概情志。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漢賦逐漸演化為駢賦,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流,講究“駢美”。而后,逢時(shí)局動(dòng)蕩不安,政治氣候壓抑,文人多愁善感,傷春悲秋,他們無(wú)心光景里,就索性嘲風(fēng)弄月,寄情于詩(shī)歌、山水之中,這使得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文壇藝苑競(jìng)綻奇葩,涌現(xiàn)出一大批文人音樂(lè)家:有編寫《聲無(wú)哀樂(lè)論》的嵇康、發(fā)現(xiàn)笛律中“管口校正數(shù)”的荀勖、提出“十二等差律”的何承天等。
詞是詩(shī)歌形式的一種,在隋唐時(shí)期被稱作曲子詞,曲子指音樂(lè)部分,詞指文字部分。中唐時(shí)期,文人受民間曲子詞的影響開始按詞歌唱或是依曲填詞,這一體裁稱文人詞。文人詞發(fā)展至晚唐時(shí)期成熟。晚唐文學(xué)家溫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及《更漏子·玉爐香》堪為代表,并對(duì)之后的詞風(fēng)產(chǎn)生了影響。宋朝間,宋詞盛行,上到皇權(quán)貴族,下到販夫走卒。《避暑錄話》中記載“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足體現(xiàn)宋詞的風(fēng)靡程度。再到元朝,詩(shī)歌發(fā)展為散曲,與雜劇合稱為元曲。宋詞與元曲在兩朝幾百年間各自發(fā)展,它們都是音樂(lè)與文學(xué)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不同點(diǎn)在于:宋詞嚴(yán)密,忌重韻,較散文化,辭藻華麗而細(xì)膩,參看宋朝女詞人李清照的《浣溪沙·莫許杯深琥珀濃》;元曲靈活,曲可重韻,較口語(yǔ)化,句式爽朗且暢達(dá),可見元朝曲作家馬致遠(yuǎn)的《天凈沙·秋思》,曲不忌俗字,直白卻又不流于俗白。單就語(yǔ)言方面來(lái)說(shuō),元曲更下里巴人,北宋詞人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中的“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wú)語(yǔ)凝噎”,在元曲作家關(guān)漢卿的《雙調(diào)·沉醉東風(fēng)》里則化為“手執(zhí)著餞行杯,眼閣著別離淚”。
文人音樂(lè)是音樂(lè)與文學(xué)高度結(jié)合之典范,其結(jié)晶不勝枚舉,泓崢蕭瑟,諸如樂(lè)曲名“梅花三弄”“高山流水”“杏花天影”“瀟湘水云”此類,內(nèi)容“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滿汀芳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這般。處處雅致脫俗,格高意遠(yuǎn)。文人音樂(lè)坊鑣水墨畫,著重堆砌意象,刻畫場(chǎng)景,借山川花木來(lái)感嘆世事如棋。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的發(fā)展起源于民間,在文人的引領(lǐng)下逐漸繁榮,民間提供素材,文人憑借文學(xué)素養(yǎng)對(duì)其優(yōu)化,使音樂(lè)具有了文學(xué)價(jià)值,也升華了其藝術(shù)價(jià)值。文人們命運(yùn)多舛,不同的人生卻有相似,他們以音樂(lè)為筆,文學(xué)為墨,譜寫了一章又一章前世今生。
三、中國(guó)風(fēng)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繼往開來(lái)
捷克小說(shuō)家米蘭·昆德拉說(shuō)小說(shuō)和音樂(lè)是同質(zhì)的東西。音樂(lè)的本質(zhì)就是文學(xué),二者難舍難分,有很大的共通性。看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余華的《音樂(lè)影響了我的寫作》,不難發(fā)現(xiàn)余華對(duì)音樂(lè)的理解極為深刻,書中道:“音樂(lè)中的強(qiáng)弱和漸強(qiáng)漸弱,如同文學(xué)中的濃淡之分;音樂(lè)中的和聲,就像文學(xué)中多層次的對(duì)話和描寫;音樂(lè)中的華彩段,就像文學(xué)中富麗堂皇的排比句。”日本當(dāng)代作家村上春樹說(shuō)他的小說(shuō)里或多或少都會(huì)提及音樂(lè),因?yàn)橐魳?lè)特征和人物性格會(huì)有相符之處,他寫有一本專門談及音樂(lè)的書叫《沒(méi)有意義就沒(méi)有搖擺》。美國(guó)民謠歌手鮑勃·迪倫一直把詩(shī)意表達(dá)當(dāng)作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核心。他于 2016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獎(jiǎng)詞是“他在美國(guó)的歌曲傳統(tǒng)內(nèi)創(chuàng)造了新的詩(shī)意表達(dá)”。在鮑勃·迪倫的歌曲中,文學(xué)性體現(xiàn)于他能把握語(yǔ)言與濃縮情感,把深刻的主題內(nèi)涵融匯于一段段一行行的歌詩(shī)中。
文學(xué)是基礎(chǔ),音樂(lè)是將文學(xué)升華的一種呈現(xiàn)。在表達(dá)愛慕時(shí),中國(guó)現(xiàn)代作家錢鐘書對(duì)夫人楊絳說(shuō):“第一次見你的時(shí)候,我的心里已經(jīng)炸成了煙花,需要用一生來(lái)打掃灰爐。”而普通人表達(dá)愛慕可能只會(huì)說(shuō)“我喜歡你”這四個(gè)字,缺乏情趣興味。這樣的現(xiàn)象在音樂(lè)里普遍存在,當(dāng)下“口水歌” 大行其道,許多歌曲表面華麗,卻沒(méi)有出色的編曲和旋律技巧,在語(yǔ)言方面,為了押韻而拗字湊詞,使情感流于泛泛,所以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應(yīng)鑒《齊人有好獵者》。真正能經(jīng)受住歲月推敲的音樂(lè),詞曲皆精,必然少不了文學(xué)素養(yǎng)的支撐。中國(guó)風(fēng)音樂(lè)應(yīng)飽含中國(guó)特色文化,而不是矯揉造作的無(wú)病呻吟,沒(méi)有文學(xué)的支撐,坍塌的速度會(huì)比流行的速度更快。文學(xué)素養(yǎng)能增添一個(gè)人的文化積淀,拓展創(chuàng)作的題材與深度,把世間百態(tài)融入音樂(lè)中,具有振聾發(fā)聵的力量,讓音樂(lè)產(chǎn)生深層次的藝術(shù)效果,經(jīng)久不衰。
如今,中國(guó)音樂(lè)多元發(fā)展,帶有鮮明中國(guó)風(fēng)格的音樂(lè)活躍輸出。用中國(guó)古代傳統(tǒng)樂(lè)器演奏出的音樂(lè)聽來(lái)是靜謐之中盡顯大氣磅礴,如純音樂(lè)《紫禁花園》《霸王卸甲》等。許多影視音樂(lè)也同樣出類拔萃,歌詞深藏文化內(nèi)涵,用現(xiàn)代編曲技巧和唱法使古代音樂(lè)重獲新生。家喻戶曉的《好漢歌》汲取了《王大娘補(bǔ)缸》等民間音樂(lè)素材,歌詞運(yùn)用文學(xué)中的比興手法:“大河向東流哇,天上的星星參北斗哇。”在流行樂(lè)歌手劉歡的演唱里,得嘯聚山林、行俠仗義之感。再以電視劇《紅樓夢(mèng)》里的配樂(lè)《紅豆詞》為例,由作曲家王立平進(jìn)行編曲創(chuàng)作,歌詞取自原著第二十八回賈寶玉的行酒令:“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詞與樂(lè)層層遞進(jìn),訴盡相思。
古時(shí)詞,今日唱。曲留聲,字傳情。中國(guó)風(fēng)音樂(lè)要注重古為今用的原則,旨在音樂(lè)與文學(xué)的結(jié)合,把具有東方美感的中國(guó)風(fēng)音樂(lè)傳承下去。雖然古人詞曲所營(yíng)造的意境是我們現(xiàn)在難以企及的,但行遠(yuǎn)自邇,登高自卑。中國(guó)音樂(lè),當(dāng)萬(wàn)里可期。
中國(guó)古代先人們把音樂(lè)與文學(xué)捻塑在一起,將成果保護(hù)流傳,傾盡一生深情。音樂(lè)與文學(xué)的高度結(jié)合,能令人細(xì)嚼之后滿口余香。音樂(lè)創(chuàng)作應(yīng)厚積薄發(fā),腹有文學(xué)素養(yǎng),才能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創(chuàng)作出好的音樂(lè),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用現(xiàn)代手法使古代音樂(lè)去蕪存菁,推陳出新,如此,音樂(lè)與文學(xué)并肩的未來(lái)必定如豐年秋收般倉(cāng)箱可期。
參考文獻(xiàn):
[1]喬雪.文學(xué)與音樂(lè)關(guān)系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2007.
[2]武恬.淺談中國(guó)古代文人音樂(lè)與音樂(lè)文化發(fā)展[J].北方音樂(lè),2020(3):4,11
[3]周曉坤.鮑勃·迪倫的“詩(shī)意表達(dá)”[J].青春歲月,2017(1):10,9.
[4]楊卓.文人詞探源[J].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1995(2):215-218.
作者單位:
湖北文理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