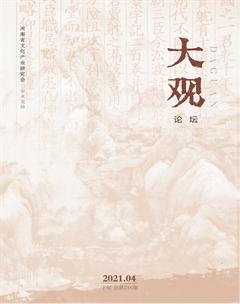儒釋道三家哲理性思想對蘇軾藝術思想與創作的影響
高睿寧
摘 要: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對本民族的藝術創作方面產生了極大影響。自春秋戰國儒道興起,至后來佛教傳入后,這三家相互交流影響,一些觀點甚至逐漸融合,共同成為歷史上主流的哲學思想。而蘇軾就是一位將儒釋道三家思想貫通并融于其藝術思想及創作中的代表人物。基于此,討論儒釋道三家是怎樣在蘇軾身上和諧共存,并在他的藝術思想及創作中體現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蘇軾;儒釋道;書畫;藝術思想
一、儒釋道三家對文人畫的影響
北宋時期以蘇軾為首的文人開始接觸并投身繪畫,并將其作為感發手段之一,為繪畫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繪畫地位逐漸提高,同時文人畫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文人畫背后的創作群體是知識分子,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想必然會受到那個時代社會上思想的影響。而北宋是儒釋道三家并存,且彼此交流融合的時代,三家的觀點主張是彼此滲透的。北宋文人群體中有代表性地位且富有影響力的蘇軾,融會貫通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主張,并將它們體現在了自身的藝術思想與創作中。
二、禪宗思想在蘇軾藝術作品中的體現
在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兩漢時期,佛教對于繪畫的影響大多在于繪畫題材以及技法上面,而最早能夠貫通佛理,并將之運用到藝術作品中的文人士大夫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王維。王維將詩畫禪相結合,以禪入詩、入畫,使詩文、山水具有禪宗內在追求的物我兩忘、高遠淡泊的禪意。在這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佛教的佛理與書畫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為北宋時期文人畫與佛教藝術深度融合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蘇軾出生于四川眉山,宋朝時期眉山的佛文化氛圍很好。蘇軾的父親雖然以儒學為宗旨,但也有一些佛、道觀念。蘇洵和當時的一些佛教僧人有往來,并把這些與佛僧的緣分延續到了蘇軾蘇轍的身上,家庭氛圍中的佛文化因素對蘇軾產生了一些影響。但同時蘇軾對于佛教有著自己的理性認識,他更看重的是本質,也就是佛理,即佛教中涉及的哲理性看法。又如蘇軾在《次韻子由三首·東亭》中提到:“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這表明他并不沉迷于其中,不相信佛教為世人描繪出的極樂世界真的存在,只是吸取養分為自己所用,為看透世事的心靈求得平衡與解脫。
而說到佛教中的哲理性看法,蘇軾追求著一種“空”,即包容萬物的寬容心態。這也影響了他的書法創作思想,他認為一幅好的書法作品也應該如此,提出了“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這樣的看法體現了蘇軾書法藝術的包容性:書法不應該是單一的美,完美與不完美并存才可說是一個整體;也不應該是在某一方面極為突出,而是應該講究一種和諧共存。正如《題顏公書畫贊》中所說:“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贊》為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后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可見蘇軾對顏真卿的碑作是十分褒獎的,認為顏真卿的《東方朔畫贊》清雄與清遠并存,字雖然小大不同,但是氣韻連貫,合起來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此外《雜評》又說:“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也。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謨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這里提到的楊、李、宋等人都在某一方面過于擅長。蘇軾認為這樣屬偏激,與他心中包容、和諧、渾然的藝術追求不相符合。他追求的是各有特色的審美趨向和諧地存在于一個整體當中,以期達到佛家追求的圓滿境界。
與此同時,佛家“無欲、無心、無執著、無住”的思想在蘇軾的藝術思想中也有所體現。不執著于某一點,萬物千變萬化,而我心巋然不動,達到“靜”。正因為蘇軾通達“靜”中奧妙,才能在創作時追求這種自由奔放、隨性適意、豁達高遠的境界。
三、老莊思想在蘇軾藝術作品中的體現
神妙的道家思想自從春秋戰國時期被提出,便貫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哲學思想發展史。后來的儒家、玄學、禪宗思想也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在不斷的交流中逐漸趨向融合。道家思想對文人及中國藝術的影響更是獨一無二,作為文人一分子的蘇軾受其影響極深。
老莊思想中的“形神說”,在蘇軾的藝術思想中就有所體現。比如在《凈因院畫記》中,蘇軾認為一個事物有它外在的“形”,也有它內在的“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作畫時不可只看到事物的外表,去追求形似,而應該深入探究事物的生長規律、存在原因和發展趨勢,做到“明于理而深觀之”,無怪乎蘇軾說“論畫與形似,見與兒童臨”。要畫出物體的神,在這一過程中就更應該冷靜思索、凝心靜氣。思索的過程應是一個慢的過程,這之后才能進入“下筆如有神”的輕松狀態,也可以叫作“胸有成竹”。
老莊所追求的“自然”對蘇軾的思想也有著非常明顯的影響。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萬物之法沒有絕對的存在,若定要說萬物法則,只能說萬物法自然。蘇軾繼承了老子的觀點,他在《石蒼舒醉墨堂》一詩中的“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一句,就深刻地印證了“無法而法,乃為至法”的觀念。在下筆時“藝”的體現由“意”與“道”推動一氣呵成,不應顧及“法”的存在。蘇軾在《跋王荊公書》中也說:“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由此更可見蘇軾“自然天放,無法而法”的觀點。但同時也說明了蘇軾“無法而法”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學有法”的基礎上的,并不是說技藝中的“技”應該被忽視或者被摒棄,而是必須要在“技”熟于心,可以熟練運用“技”之后,才能不受制于“技”,可以游于“技”之上,繼而追求“無法而法”的自由境界。
蘇軾留存下來的畫作非常少見,循跡《枯木怪石圖》和《瀟湘竹石圖》,可以感受到蘇軾對于枯木、竹子、怪石以及周遭環境的“理”都有著清晰的認識。其中每一筆畫落筆都能將事物的來龍去脈表達清楚,透析生長的規律,在此之上達到“自然天放”,表現出事物的自然之態。同時他作畫時處于無我境界,使得畫面淡泊高遠,又含有自然的生機勃勃。
四、儒家思想在蘇軾藝術作品中的體現
自春秋末期孔子建立儒家學說后,儒學逐漸發展,至漢武帝時期達到頂峰。漢朝以后,儒學地位逐漸下降,儒釋道三家開始較為平衡地共同發展。發展至宋朝,出現了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宋代理學。但是在儒家發展的過程中,其本質講求的綱常倫理、忠孝仁義是一直不變的。
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們積極入世就是受到儒家入世之說的影響,蘇軾也同樣如此。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名教”是可以與道家“自然”共存的。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蘇軾心懷天下的濟世救民情懷就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在蘇軾的藝術思想中,人格品德與書法之間有著互相影響的關系。他認為書法作品與書法家的學識、德行、氣質、修養是分不開的。正如蘇軾在《跋錢君倚書〈遺教經〉》中所言:“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由此可以看出,蘇軾認為,一個人到底是君子還是小人,其精神、氣質必然會體現在他的書作中。
五、結語
蘇軾一直都是主張思想與藝術相結合的,他認為文化藝術應該表現出作者的思想觀念,打通“藝”與“意”之間的隔閡。
儒釋道三家的思想體系被蘇軾融會貫通,他取三家之所長,致力于尋得一個處世之法,使自己的心靈達到一種平衡。同時,蘇軾把自己人生構架下的哲學思想體系體現在藝術之中,這給他的藝術思想與創作賦予了無限的生機與魅力。
參考文獻:
[1]蘇軾.東坡題跋[M].白石,校.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2]陳中浙.我書意造本無法:蘇軾書畫藝術與佛教[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3]張毅.蘇軾與朱熹[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4]林語堂.蘇東坡傳[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5]王啟鵬.蘇軾文藝美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6]寧稼雨.《世說新語》與魏晉風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7]李昌舒.身份與趣味:論蘇軾的士人畫思想[J].藝術百家,2017(5):162-169.
作者單位:
南開大學文學院東方藝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