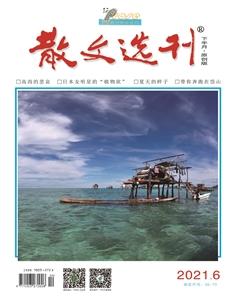居高聲自遠
鄭相豪
盛夏炎熱之時,我居所陽臺前一排高大的梧桐樹棲居著許多蟬,每天伴著聒噪不休的蟬鳴聲,行止起居,仿佛有一種遠離鬧市置身鄉野之感。
在我的家鄉,人們對蟬幼蟲叫“泥泥殼”,帶著兩個“泥”字是有道理的。蟬的前身始于泥土中之蛹。據說它在泥土中要待上四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破土而出,脫殼為蟬,歷盡了苦難坎坷。但它的生命卻很短暫,只有一個多月而已。
早年,某個夏日清晨,當我背著書包走在故鄉的大塘梗樹下,不知是哪只蟬從樹上發出一聲清脆悠長的低鳴,一蟬唱,百蟬和,呼朋引伴,競相鳴叫,似乎就拉開了它們一天合唱的帷幕。午后太陽朝西移動,蟬朝著最亮最熱的方向鳴唱得更加歡暢。我常在午后,躺在樹下涼席上,一邊歇涼,一邊凝神聆聽蟬鳴。那美妙動聽的聲聲蟬鳴,不斷地在我耳邊縈繞回旋,仿佛正在演奏一曲扣人心弦的交響樂,或輕柔委婉,或低沉悲切,或雄偉嘹亮。聽著這天籟之音,會情不自禁地撩起自己心靈之弦,時而讓人歡快愉悅;時而讓人感傷惆悵;時而讓人深思曠遠,遐想無限。當暮色漸濃,仍有蟬在淺唱低吟,真是爭分奪秒啊!
以往總覺得,蟬也就是經盛夏歷寒秋,終為泥土的一個蛹蟲。沒想到古往今來,有那么多文人雅士為之飽蘸筆墨,比如,“蟬聲未發前,已自感流年。”這是劉禹錫感嘆歲月易逝的蟬。“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這是駱賓王表達自己的高潔無人賞識、白發壯志難酬的悲憤之情。“光陰苦短爭朝夕,要向人間高處鳴。”這是當代詩人何鶴把自己比作蟬,表達了高昂向上的奮斗精神。還有大畫家齊白石是畫蟬的高手,他指點也是大畫家的張大千,蟬頭應向上而不是向下,不應疏忽這樣的細節。張大千深感愧疚,對白石老觀蟬之細、求真的精神心中佩服。兩位大畫家對畫蟬如此癡迷,如此摯愛,實在令人驚嘆!未承想,不同時代背景,在不同的環境中,蟬竟然都能受到藝術家的喜愛和關注。
蟬蛻皮要經歷劇烈的疼痛,而蟬蛻下的皮是一味好藥材。中醫稱之為“蟬蛻”或“蟬衣”,其主要功能是疏散風熱,消痰止癢,止咳利咽,還可治嬰兒夜啼等。記得女兒三歲時,不知何因,渾身過敏,起了許多紅斑點,她癢得難受,有的地方被撓破了。看到女兒難受,自己很心疼。吃了兩天的西藥沒管用。之后,請了一位老中醫,診斷后開了一服中藥方。我煎藥時,發現除了其他我不認識的幾種藥材,多數為蟬衣。女兒連喝三天,身上的紅斑點竟然消去了,這讓我很驚奇。之后問了老中醫,他說,如果初發過敏,直接喝蟬衣煎的水,也能痊愈。蟬衣有這么好的藥效,是我沒想到的。
前幾天,我翻閱唐詩時,讀到唐初虞世南寫蟬的五言詩:“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蟬聲遠傳,一般人往往以為是借助秋風的傳送,詩人卻別有智心,富有深意地點出由于“居高”而聲音自能致遠,形象地表達了詩人不肯趨炎附勢的高尚的思想境界,這種對蟬的獨特描繪,蘊含著深刻的人生感悟:立身品格高潔的人,不需要某種外在的權位與勢力,自能名聲遠揚。
我成不了虞世南筆下的蟬,不能居高,亦難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