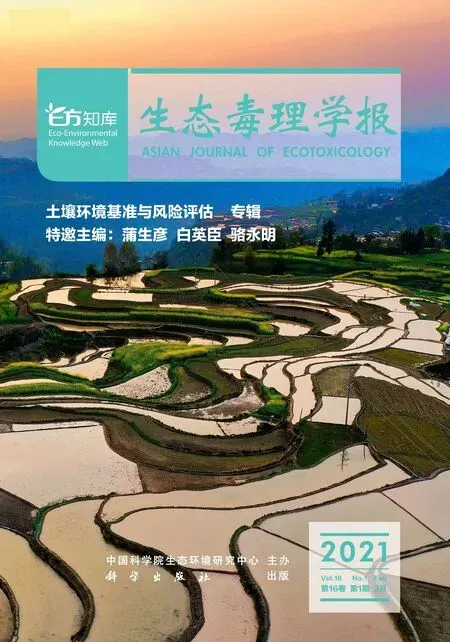C-RAG模型在砷污染場地中的修正及應用研究
雷城英,李玉進,王夢珂,沈鋒,3,*,張振師
1. 西安錦華生態技術有限公司,西咸新區 712000
2. 中國電建集團西北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710065
3.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楊凌 712100
2000年我國首次引入場地風險評估技術,在廣泛吸取國外經驗的同時,我國也在該領域形成了諸多研究成果。2014年我國正式頒布了《污染場地風險評估技術導則》,這是我國場地及地下水風險評估領域發展歷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標志著一套本土化的場地風險評估模式在我國初步形成[1-3]。
在提高城市轉型升級、加快跨越式發展的大環境下,因工礦企業關閉、搬遷或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疑似污染地塊,其調查和風險評估工作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便成為指導場地后期開發利用的關鍵環節。自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廣泛關注環境風險評估的前提下,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了多元且完善的環境風險評估體系。針對建設用地的風險評估,國內外較為成熟的評估模型包括英國的CLEA模型(Contaminated L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美國的RBCA模型(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荷蘭的RISC-Human模型,以及中國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編制的一種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理念的評估模型(Chinese Risk Assessment Guide, C-RAG)[4]。雖然C-RAG模型現已發展成為我國場地風險評估方法中的主流,但直接套用模型推薦值進行計算的評估思維還普遍存在[5-6]。而砷作為污染土壤中常見的重金屬元素,由于其保守的毒理學參數和多樣化的賦存形態,使之在不結合場地實際參數的情況下得到的評估結果針對性和適用性較差,也可能造成高估風險繼而增加修復工程量[6-8]。因此,如何根據場地實際情況,合理評估風險并妥善制定修復目標便成為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重點。
筆者以青海一處銅金選礦廠舊廠址為研究對象,以C-RAG模型為基礎,結合場地污染特點、環境條件及其后期規劃用途,針對性地評估了該場地的風險情況,給出以控制健康風險和控制修復成本為雙目標的場地修復目標值。旨在為污染場地的風險評估和管控工作提供科學依據,為廠址后期的開發利用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研究區域概況
研究區銅金礦選礦廠始建于1997年,主要進行銅、金、銀、硫和鐵等產品的初加工,2003年停產前生產規模為日處理礦石150 t,主要設備有破碎系統、球磨系統、浮選系統、濃縮系統、重選系統和尾礦處理等,占地面積12 655 m2。根據規劃,該場地后期將用于建設廣場及地面停車場。
1.2 樣品采集與分析
該選礦廠以磁鐵礦為原料,采用先浮選后磁選的工藝分別回收金與鐵。生產過程中原生礦石和選礦廢水攜帶的重金屬類物質,以及浮選劑次生的氰化物,可能經雨水沖刷、地表徑流以及大氣干濕沉降等作用對土壤環境造成影響。因此,本次地塊調查工作中的重點關注因子確定為重金屬和氰化物。
根據該場地的規劃用途和功能區域,采用系統隨機布點結合分區布點的方法,布設17個土壤調查點位(并在地塊上風向1 km的農田中設置1處對照點位)和4個地下水調查點位,土壤取樣時以不同的巖性特征和土質依據,分層采集至初見地下水(約6.5 m)為止(圖1)。最終采集并檢測土壤調查樣品51個,地下水調查樣品4個。樣品檢測指標為8項重點關注因子,即7種重金屬(砷、六價鉻、銅、鉛、鎳、鎘和汞)和氰化物。所有指標的測定均按照《土壤環境質量 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GB 36600—2018)[9]推薦的標準方法進行,并采用平行樣和有證標樣的質控方式,保證檢測結果準確無誤。

圖1 采樣點位示意圖
1.3 評估模型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場地調查的數據基礎上,以《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評估技術導則》(HJ25.3—2019)[10](以下簡稱《導則》)中的C-RAG評估模型為主,通過對場地關注污染物的篩選、暴露途徑和毒性參數的分析,最終以該場地可能引發危害人體健康事件發生的概率來表征場地風險的大小。
2 場地污染狀況及模型分析(Site pollution and model analysis)
2.1 場地污染特征分析
經統計發現,調查區域土壤pH值處于7.39~9.81范圍內,屬于偏堿性土壤栗鈣土,土壤中除砷以外的其他污染物及區域地下水中各污染物含量都處于較低水平。以一類用地篩選值(20 mg·kg-1)為標準,該場地17個土壤調查點位中砷的含量范圍為0.73~73.2 mg·kg-1,點位超標率為22.2%,樣品超標率為11.3%,最大超標倍數為2.66倍。
由于土壤砷選用的是總量分析方法,但土壤中的重金屬并不能完全解吸進入胃液及腸液而被人體吸收[11]。因此,本研究采用相對保守的統一生物可給性測試方法(unified bioaccessibility method, UBM)[12]得到了研究場地土壤中砷污染物在腸胃階段的生物可給性,其中,胃階段的生物可給性為6.54%~22.87%,腸階段的生物可給性為3.67%~19.35%。
2.2 場地概念模型及參數修正
該場地主要污染物為重金屬砷,其具有難降解、難揮發、易積累和毒性大等特點,且地下水調查結果顯示水質良好。因此,考慮人體在該場地中的暴露途徑時,主要從經口攝入、皮膚接觸和吸入顆粒物(分為室內顆粒物及室外顆粒物)3個方面建立概念模型。由于地塊規劃用途屬于第二類用地,根據模型特點,評估受體對象僅考慮成人。
C-RAG模型中所給參數,是在借鑒各國風險評估理論的基礎上,基于全國范圍內人群特征及環境條件的總體水平而給出的推薦值。而實際應用中則需結合區域特點,針對性地修正對評估結果影響較大的3項首要參數(風險可接受水平、土壤攝入量和暴露頻率)及環境空氣質量參數[4,13],以使評估結果更加合理。
2.2.1 風險可接受水平
由于風險可接受水平對風險評估的結果影響顯著,在保證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應在修正模型其他參數與修正風險可接受水平中擇一而用,否則可能造成低估風險的情況發生。因此,本研究將在修正模型其他參數的情況下,繼續沿用10-6作為單一污染物的可接受風險水平。
2.2.2 土壤攝入量
相比于英國、美國、日本和韓國(兒童攝入量:英國和美國100 mg·kg-1,日本43.5 mg·kg-1,韓國118 mg·kg-1)等國家,C-RAG模型中土壤攝入量的推薦值(兒童攝入量:200 mg·kg-1)較高[14]。因此,在對比參考各國土壤攝入量推薦值與自然人文環境間的關系后,結合場地所在區域的人均土壤占有量、城市地面硬化率等因素后,兒童土壤攝入量參考取值較大的韓國推薦值118 mg·kg-1,經整化為120 mg·kg-1,成人土壤攝入量則按模型規律,取兒童攝入量的1/2,即60 mg·kg-1。
2.2.3 暴露頻率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15],我國居民在各環境中的活動時長如表1所示。在研究地塊的規劃用途下,受體人群室內活動時長應按工作活動取值為工作日6.1 h,休息日0 h;室外活動時長取值為工作日3.3 h,休息日8 h。按照我國一年工作日為250 d,休息日為115 d,并沿用C-RAG模型理念,假設居民室外活動中,有1/2的時間在場地附近,1/2的時間遠離場地,則修正后得到的成人暴露參數為:成人暴露頻率92.2 d·a-1,其中,室內暴露頻率63.5 d·a-1,室外暴露頻率28.7 d·a-1(表2)。

表1 中國居民不同環境中的活動時間

表2 本研究場地評估模型修正參數及過程參數匯總


2.2.4 PM10
C-RAG模型中PM10推薦值是全國總體水平的指導值。本場地在參考《2019年青海省生態環境狀況公報》[16]中當地2018年和2019年的環境空氣質量平均水平后,修正PM10的值為0.073 mg·m-3。
將土壤樣品檢測濃度和上述模型參數值應用于C-RAG模型中進行計算,得到該場地的致癌風險及危害商結果,并基于模型反推得到該場地的風險控制值。
3 結果與討論(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場地風險水平
修正后的C-RAG模型相比于原模型,其致癌風險水平普遍降低為原來的1/4,從而使風險等級顯著降低,修正前后致癌風險大于10-5的比例從29.4%減少到了3.92%,致癌風險小于10-6的比例從11.8%提升至35.3%,這進一步說明了C-RAG模型在不同場地環境中應用時,確實可能造成高估風險的情況。將修正后計算得到的致癌風險值以Surfer軟件的克里金插值法作圖,得到不同土層中砷的致癌風險分布圖(圖2)。由圖2可知,水平方向上,位于場地中部的濾液收集池、晾曬區、儲藏室、篩分及球磨車間處風險相對較高,最大風險水平為1.2×10-5,這些區域均屬于選礦工藝的主要操作區,原礦石中的砷在堆存、破碎、浮選和晾曬的過程中,通過粉塵和廢水等介質進入土壤環境,從而累積產生污染,導致風險升高,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區仍處于10-5水平以下;垂直方向上,風險水平隨著土層的加深呈遞減趨勢,2~4 m土層最大風險水平降至4×10-6。

圖2 場地土壤砷修正后的致癌風險分布圖
3.2 修復目標值
目前,雖然已有部分研究采用重金屬形態分析法[2,17]、多層次風險評估法[18]和概率風險評估[19]等技術對修復目標的合理性進行優化。但以標準篩選值或模型計算得到的控制值直接作為污染地塊的修復目標值的情況仍不罕見,這就容易造成修復目標值沒有針對性或過于保守的問題。
綜合考慮上述問題后,本研究在結合污染物的生物可給性試驗[20-22]、區域背景值統計情況及國家標準值的確定依據等方面后,對比了幾種方案下的修復目標值(表3)。由表3可知,僅通過模型參數修正可使致癌風險控制值擴大4.1倍,而在此基礎上再引入生物可給性數值(按試驗結果上限取整為30%)則可使致癌風險控制值擴大13.7倍。在修復目標值的確定上,按照“在修復目標值不小于區域平均的土壤背景值,不大于區域背景值95%分位數的1.3倍的前提下,優先選擇較大值作為土壤修復目標值”[23]的原則,本研究最終確定修復目標值為21.1 mg·kg-1。

表3 不同方案下修復目標參考值的比較
當分別以1.54、6.32、21.1和60 mg·kg-1作為修復目標值的情況下,按照污染物濃度等值線圖劃定修復區域并對比其對應的修復工程量(表4)后發現,對于砷而言,采用模型參數修正的方式可縮減35.6%的修復土方量,但此方案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仍存在過度修復,易造成修復成本的額外支出,因此,并不是平衡風險水平和修復工程量的最佳方案;以標準篩選值直接作為修復目標的工程量雖然小,但其存在的健康風險卻相對較高;比較之下,在修正模型參數的基礎上引入生物可給性的評估方式,能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使修復工程量縮減98.3%,從我國行業現狀和項目實施的角度來看具有較高的可行性。

表4 不同修復目標值下的修復工程量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表明:
(1)該場地是以砷為特征污染物的單一重金屬污染,以一類用地篩選值(20 mg·kg-1)為標準,點位超標率為22.2%,最大超標倍數為2.66倍。
(2)通過對C-RAG模型受體暴露途徑、土壤攝入量、暴露頻率和PM10的修正,該場地致癌風險水平普遍降低了一個數量級,多分布于10-6~10-5水平,高風險區域與重金屬超標區域基本一致,垂直方向風險程度隨土層厚度的增加而減小。
(3)綜合考慮區域背景值、應用可行性及風險水平與修復投入之間的平衡關系后,確定以引入生物可給性的致癌效應風險控制值21.1 mg·kg-1為最終修復目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