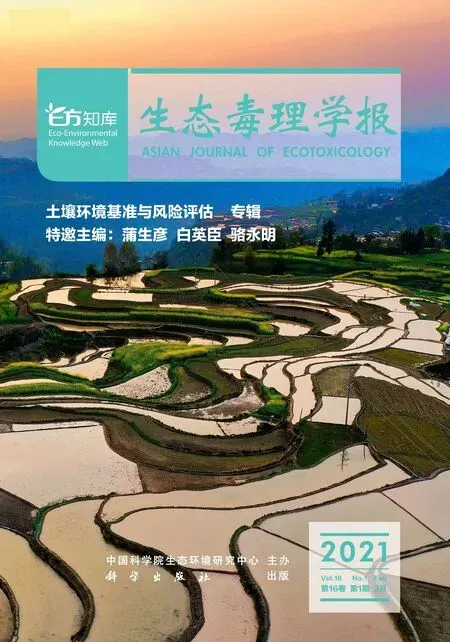基于保護(hù)生態(tài)的土壤基準(zhǔn)值制訂關(guān)鍵技術(shù)研究
——以美國和澳大利亞為例
鄭麗萍,王國慶,*,李勖之,戚旭東,張亞,閆佳莉,林玉鎖
1. 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南京環(huán)境科學(xué)研究所,南京 210042
2. 國家環(huán)境保護(hù)土壤環(huán)境管理與污染控制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南京 210042
3. 江蘇省地質(zhì)礦產(chǎn)局第一地質(zhì)大隊(duì),南京 210041
土壤環(huán)境基準(zhǔn)是指土壤中物理、化學(xué)等要素對土壤生物、作物、健康或使用功能不產(chǎn)生不良或有害影響的最大限值或臨界含量[1]。根據(jù)不同的保護(hù)對象和受體,可分為保護(hù)農(nóng)產(chǎn)品安全、保護(hù)人體健康、保護(hù)生態(tài)受體和保護(hù)地下水的土壤環(huán)境基準(zhǔn)等。土壤基準(zhǔn)研究是一項(xiàng)科學(xué)性的研究工作,主要體現(xiàn)技術(shù)性與科學(xué)性,較少考慮經(jīng)濟(jì)和社會因素,而土壤環(huán)境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的制訂是在土壤基準(zhǔn)研究結(jié)果的基礎(chǔ)上,綜合考慮經(jīng)濟(jì)和社會因素后提出的一系列可服務(wù)于環(huán)境管理的值,二者存在聯(lián)系而不完全等同。土壤環(huán)境基準(zhǔn)是土壤環(huán)境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制修訂、土壤環(huán)境質(zhì)量評價和監(jiān)管的重要科學(xué)依據(jù)[2-7],加強(qiáng)土壤基準(zhǔn)的研究工作可為我國相關(guān)標(biāo)準(zhǔn)的制訂提供數(shù)據(jù)支持[8-17]。
筆者選取美國和澳大利亞基于保護(hù)生態(tài)的土壤基準(zhǔn)制訂中的關(guān)鍵技術(shù)進(jìn)行深入討論,從兩國的制訂策略和關(guān)鍵推導(dǎo)方法等方面進(jìn)行詳細(xì)闡述,比對了兩國的基準(zhǔn)值制訂技術(shù)要點(diǎn),旨在為我國土壤基準(zhǔn)研究提供一定參考。
1 美國土壤生態(tài)篩選值制訂的關(guān)鍵技術(shù)(Key techniqu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cological screening lev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1.1 關(guān)鍵技術(shù)1:采用數(shù)據(jù)打分制獲取推導(dǎo)篩選值的核心數(shù)據(jù)
土壤生態(tài)篩選值(Eco-SSL)由美國環(huán)境保護(hù)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制訂[18],US EPA首先通過一系列嚴(yán)格的篩選程序,篩選出可信度較強(qiáng)的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其中必須包含土壤理化性質(zhì)數(shù)據(jù),包括土壤pH和有機(jī)質(zhì)百分比。如果土壤pH<4或>8.5,或者土壤有機(jī)質(zhì)含量>10%時,文獻(xiàn)數(shù)據(jù)不被采納。相關(guān)的毒性數(shù)據(jù)按照4種生態(tài)相關(guān)評估終點(diǎn)進(jìn)行總結(jié)整理,即繁殖、數(shù)量、生長和生理特征。
(1)數(shù)據(jù)收集
文獻(xiàn)檢索包括紙質(zhì)文獻(xiàn)檢索和計算機(jī)抽象數(shù)據(jù)庫檢索。基于論文的文獻(xiàn)檢索過程主要包括書目、指導(dǎo)性文件和評論文章的手工審查。其中,檢索過程中需剔除研究內(nèi)容如藥品、生物制品、污水或者定量構(gòu)效關(guān)系(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QSAR)等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3]。
(2)數(shù)據(jù)選擇
US EPA設(shè)置了10條文獻(xiàn)數(shù)據(jù)選擇的標(biāo)準(zhǔn)(表1),并根據(jù)所獲取的毒性數(shù)據(jù)的質(zhì)量進(jìn)行相應(yīng)賦分(2分、1分或0分)[18]。US EPA規(guī)定,推導(dǎo)Eco-SSL需要選擇總分18分中得分>10分的數(shù)據(jù)[18]。生物有效性評分被確定為評分過程的一部分,根據(jù)毒性數(shù)據(jù)所包含的土壤pH和有機(jī)質(zhì)含量信息,對照數(shù)據(jù)評價第1條生物有效性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相應(yīng)賦分。美國推導(dǎo)Eco-SSL優(yōu)先選擇具有較高生物有效性的土壤的毒性數(shù)據(jù),采用土壤生物有效性最高(如4≤土壤pH<5、土壤有機(jī)質(zhì)含量<2%)的所有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20%效應(yīng)濃度(EC20)、10%效應(yīng)濃度(EC10)和最大允許毒物濃度(MATC))的幾何平均值計算Eco-SSL,要求數(shù)據(jù)必須≥3個,如果有效數(shù)據(jù)<3個,可從土壤生物有效性次高的土壤中(如5.5<土壤pH<7、土壤有機(jī)質(zhì)含量<2%)尋找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EC20、EC10和MATC),以上數(shù)據(jù)尋找過程直到≥3個的時候可以計算Eco-SSL[18-19]。

表1 美國環(huán)境保護(hù)局(US EPA)評價植物和土壤無脊椎動物毒性數(shù)據(jù)的標(biāo)準(zhǔn)
1.2 關(guān)鍵技術(shù)2:美國的Eco-SSL制訂未考慮土壤微生物過程,但考慮了對野生生物的保護(hù)
美國的Eco-SSL的保護(hù)對象主要考慮了植物、土壤無脊椎動物和野生動物(鳥類和哺乳動物),但未考慮土壤微生物過程。根據(jù)US EPA生態(tài)篩選值制訂導(dǎo)則[20],美國的Eco-SSL不考慮土壤微生物過程的主要原因歸納為以下3點(diǎn):(1)Eco-SSL的制訂是為了支撐美國超級基金(Superfund)場地的風(fēng)險管理決策,這些場地污染程度較高,污染物對生態(tài)的風(fēng)險應(yīng)優(yōu)先考慮對環(huán)境具有重大意義且營養(yǎng)級別更高的生物體(即植物、無脊椎動物和野生動物);(2)由于數(shù)量規(guī)模、功能冗余和環(huán)境復(fù)雜性等因素的條件差異,實(shí)驗(yàn)室微生物生態(tài)毒理學(xué)研究是否適合自然環(huán)境尚存在不確定性,研究結(jié)果對美國超級基金場地的污染相關(guān)性無法確定;(3)微生物生態(tài)毒理學(xué)常用的測試終點(diǎn)有微生物數(shù)量、群落結(jié)構(gòu)、呼吸作用和酶活性等,這些指標(biāo)對溫度、水分、氧氣和許多其他非污染因素的環(huán)境變化具有較高的響應(yīng)能力,閾值變化范圍較大,存在地域性差異。植物、土壤無脊椎動物和陸地野生動物對污染物的響應(yīng)閾值通常受環(huán)境影響變化很小,而微生物的反應(yīng)通常會受到測試條件的極大影響。基于上述3點(diǎn)原因,US EPA未考慮采用微生物過程推導(dǎo)Eco-SSL[20]。
美國推導(dǎo)保護(hù)野生生物的Eco-SSL采用了野生生物風(fēng)險模型[18,21-27]。野生生物受體主要通過2個暴露途徑接觸土壤污染物:(1)進(jìn)食時偶然攝入土壤;(2)攝入富集了土壤污染物的食物[21-27]。通過這2種途徑計算土壤篩選值的公式為:

式中:HQj為污染物j的危險商值;Soilj為土壤中污染物j的濃度(mg·kg-1);FIR為食物攝入量(kg food (dry weight)·kg-1(wet weight)·d-1);Ps為食物中攝入土壤的比例;Bij為污染物j在生物i體內(nèi)的濃度(mg·kg-1);TRVj為毒性參考值(mg·kg-1BW·d-1);不同食物(生物)i中污染物j的濃度Bij可以根據(jù)土壤中該污染物的濃度Soilj按照以下方法進(jìn)行估測:
方法1:Bij=BAFij×Soilj(常數(shù)法)
方法2:ln(Bij)=Iij+Sij×ln(Soilj) (對數(shù)線性法)
方法3:Bij=Iij+Sij×Soilj(線性法)
式中:Bij為污染物j在食物i中的濃度(i可以為植物、蚯蚓或小型哺乳動物)(mg·kg-1);BAFij為污染物j在生物i體內(nèi)的生物富集系數(shù);Iij為污染物j在生物i體內(nèi)的生物累積模型的截距;Sij為污染物j在生物i體內(nèi)的生物累積模型的斜率。
在涉及100%食用小型哺乳動物的捕食者時,目前尚無足夠的數(shù)據(jù)可將土壤污染物濃度與小型哺乳動物組織中的污染物濃度直接建立關(guān)系。在此情況下,需根據(jù)以下模型計算Bij。
方法4:Bij=Cdiet×BAFdm
方法5:ln(Bij)=Iij+Sij×ln(Cdiet)
方法6:Bij=Iij+Sij×Cdiet
式中:Bij為食物i中污染物j的濃度(i為小型哺乳動物)(mg·kg-1);Cdiet為根據(jù)方法1、2或3得出的小型哺乳動物的食物中污染物j的濃度(mg·kg-1),默認(rèn)食物為100%蚯蚓;BAFdm為污染物j在哺乳動物或鳥類中的生物富集系數(shù);Iij為污染物j在生物i體內(nèi)的生物累積模型的截距;Sij為污染物j在生物i體內(nèi)的生物累積模型的斜率。
1.3 關(guān)鍵技術(shù)3:美國的Eco-SSL定位為場地初步篩查,不作為保護(hù)生態(tài)的土壤修復(fù)目標(biāo)值
Eco-SSL用于場地初步篩查判斷污染物對土壤的生態(tài)風(fēng)險,從生態(tài)風(fēng)險角度初步對土壤污染物進(jìn)行篩選,在特殊場地需根據(jù)特定導(dǎo)則[28-33]進(jìn)行詳細(xì)生態(tài)風(fēng)險評估,進(jìn)一步確定特定潛在污染物(contaminants of potential concern, COPCs)的環(huán)境風(fēng)險。US EPA在指導(dǎo)文件[18, 28]中明確指出,Eco-SSLs不可用作清潔修復(fù)目標(biāo)值,也不能將其修改后用作聯(lián)邦清潔修復(fù)標(biāo)準(zhǔn)。US EPA強(qiáng)調(diào)土壤Eco-SSL用于指導(dǎo)識別可能對陸生生態(tài)受體產(chǎn)生不可接受風(fēng)險的污染物,不能替代US EPA現(xiàn)有的法規(guī)或規(guī)章,它對US EPA、美國各州或監(jiān)管社區(qū)不具有法律約束力[18]。
土壤Eco-SSL制訂通用方法包括4個步驟[18]:(1)進(jìn)行文獻(xiàn)檢索;(2)篩選確定需要排除和可接受的文獻(xiàn);(3)提取文獻(xiàn)毒理數(shù)據(jù)并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評分,得出適用于推導(dǎo)Eco-SSL的毒理數(shù)據(jù);(4)推導(dǎo)得出篩選值。這些程序被確定為Eco-SSL推導(dǎo)的標(biāo)準(zhǔn)操作程序[18, 32-33]。目前美國已制訂的土壤Eco-SSL如表2所示。

表2 美國生態(tài)土壤篩選值(Eco-SSL)[18-25]
2 澳大利亞土壤生態(tài)調(diào)查值制訂的關(guān)鍵技術(shù)(Key techniqu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levels in Australia)
2.1 關(guān)鍵技術(shù)1:澳大利亞土壤生態(tài)調(diào)查值的制訂考慮了土壤背景值
澳大利亞基于保護(hù)生態(tài)的土壤基準(zhǔn)值在該國被叫做生態(tài)調(diào)查值(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levels, EILs),該推導(dǎo)方法關(guān)鍵是規(guī)定了用來推導(dǎo)EILs的數(shù)據(jù)必須是外源添加到土壤中以引起毒性的污染物含量,不可使用野外污染土壤的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34-36]。當(dāng)使用這些毒性數(shù)據(jù)時,結(jié)果值稱為添加污染物水平(added contaminant level, ACL)。由于土壤中某些元素本身存在背景值,澳大利亞在制訂土壤EILs的時候考慮了土壤背景值的因素,在ACL中加入一個被調(diào)查土壤的環(huán)境背景值(ambient background concentration, ABC)來計算EILs[36],表達(dá)公式為:
EILs=ACL+ABC
式中:EILs為生態(tài)調(diào)查值;ACL為添加污染物水平;ABC為土壤環(huán)境背景值。澳大利亞的EILs的推導(dǎo)方法如圖1所示。

圖1 澳大利亞土壤生態(tài)調(diào)查值(EILs)的推導(dǎo)方法示意圖
2.2 關(guān)鍵技術(shù)2:使用土壤理化性質(zhì)計算特定土壤的ACL
澳大利亞使用了包含土壤的理化性質(zhì)(pH、陽離子交換量和粘土含量)多元模型用于計算特定土壤的ACL。在這種方法中,不同理化性質(zhì)的土壤具有不同的污染物EIL,而不是每種污染物的只有一個通用EIL值,即每種污染物的EIL值不唯一[36-41]。
ACL適用于三價鉻(Cr(Ⅲ))、銅(Cu)、鎳(Ni)和鋅(Zn),用于特定土壤的EIL測定。特定區(qū)域土壤推導(dǎo)Cr(Ⅲ)、Cu、Ni和Zn的EILs時需測定的土壤理化參數(shù)如表3所示[36]。

表3 特定區(qū)域土壤推導(dǎo)Cr(Ⅲ)、Cu、Ni和Zn的ACL時需測定的土壤理化參數(shù)
由于澳大利亞沒有足夠的數(shù)據(jù)和相關(guān)模型支撐推導(dǎo)砷(As)、滴滴涕、鉛(Pb)和萘的特定區(qū)域土壤ACL,As、滴滴涕、Pb和萘的EILs為唯一的土壤通用值。
2.3 關(guān)鍵技術(shù)3:使用數(shù)據(jù)歸一化模型對毒性數(shù)據(jù)進(jìn)行校正
由于土壤的異質(zhì)性,澳大利亞采用了數(shù)據(jù)歸一化的方法對不同土壤的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進(jìn)行校正,使用校正過的數(shù)據(jù)通過物質(zhì)敏感性分布(SSD)法推導(dǎo)EILs。該國導(dǎo)則中納入了不同研究團(tuán)隊(duì)開發(fā)的土壤與生物毒性關(guān)系的經(jīng)驗(yàn)?zāi)P汀=?jīng)驗(yàn)?zāi)P屠猛寥赖奈锢砘瘜W(xué)性質(zhì)(例如土壤pH值和有機(jī)碳含量)預(yù)測單一污染物對單一物種的毒性。通過使用歸一化關(guān)系方程表達(dá)土壤特性對毒性數(shù)據(jù)的影響,以此來使毒性數(shù)據(jù)反映試驗(yàn)物種的固有敏感性。例如導(dǎo)則在推導(dǎo)土壤中Zn的EILs時,列出了文獻(xiàn)所報道的7種Zn毒性的經(jīng)驗(yàn)?zāi)P蚚37-38](表4)。其中,3種經(jīng)驗(yàn)?zāi)P团c植物有關(guān),2種與微生物功能有關(guān),2種與土壤無脊椎動物有關(guān)。
該導(dǎo)則中的Zn利用不同歸一化方程表征土壤理化性質(zhì)對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的影響,所得到的毒性數(shù)據(jù)可反映試驗(yàn)物種的內(nèi)在敏感性。Zn對不同生物物種的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按照表4的經(jīng)驗(yàn)?zāi)P捅粴w一到澳大利亞標(biāo)準(zhǔn)土壤的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澳大利亞規(guī)定本國的標(biāo)準(zhǔn)土壤理化參數(shù)如表5所示[38]。

表4 Zn對土壤無脊椎動物、土壤過程和植物毒性的歸一化模型[38]

表5 澳大利亞標(biāo)準(zhǔn)土壤理化參數(shù)
2.4 關(guān)鍵技術(shù)4:根據(jù)不同用地類型確定物種保護(hù)水平
澳大利亞為3種用地方式設(shè)置開發(fā)了EILs:(1)具有生態(tài)價值的地區(qū);(2)城市住宅區(qū)和公共區(qū)域;(3)商業(yè)和工業(yè)用地。EILs不適用于農(nóng)用地土壤,農(nóng)用地土壤需要評估污染物對植物的毒性、植物污染物吸收富集和土壤類型等因素[36]。
一般土地使用設(shè)置的保護(hù)級別為:具有生態(tài)價值的地區(qū)物種保護(hù)水平為99%;城市住宅區(qū)和公共開放空間物種保護(hù)水平為80%;商業(yè)和工業(yè)用地的物種保護(hù)水平為60%。當(dāng)污染物存在生物放大效應(yīng)時,保護(hù)水平將相應(yīng)增加5%[36,39-41]。
EILs在土壤的適用深度為地面以下2 m,地面以下2 m為大多數(shù)生物物種的根系區(qū)和生物居住區(qū)。干旱地區(qū)的生物物種的根滲透率可能更大,具體考慮可能應(yīng)用到地表以下3 m[36-37]。
3 討論(Discussion)
對上述2個國家制訂基于保護(hù)生態(tài)的土壤基準(zhǔn)值的技術(shù)要點(diǎn)進(jìn)行比較,結(jié)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兩國的基準(zhǔn)名稱、保護(hù)對象和毒理數(shù)據(jù)處理措施等有一定差異,這與各國的具體制定策略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有些國家在制定土壤基準(zhǔn)值時已考慮了土地利用方式[36-38,42-46]。筆者認(rèn)為由于不同的土地后續(xù)利用方式存在差異,在推導(dǎo)土壤基準(zhǔn)值的時候建議考慮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別。同時,毒理數(shù)據(jù)的選擇與甄別直接關(guān)系到基準(zhǔn)值制訂的科學(xué)性、合理性,建議借鑒各國對毒理數(shù)據(jù)的篩選方法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科學(xué)選擇。

表6 美國和澳大利亞制訂保護(hù)生態(tài)受體的土壤基準(zhǔn)值技術(shù)要點(diǎn)比較
兩國的土壤環(huán)境基準(zhǔn)值制訂技術(shù)方法各有其優(yōu)勢,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筆者就本文研究的美國與澳大利亞土壤基準(zhǔn)的技術(shù)方法提出3點(diǎn)建議與意見。
(1)美國對于數(shù)據(jù)的打分制優(yōu)先選擇生物有效性高的土壤,未體現(xiàn)土壤理化性質(zhì)的差異性
美國推導(dǎo)Eco-SSL優(yōu)先選擇具有較高生物有效性的土壤的毒性數(shù)據(jù),采用土壤生物有效性最高(如4≤土壤pH<5、土壤有機(jī)質(zhì)<2%)的所有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的幾何平均值計算Eco-SSL,如果有效數(shù)據(jù)少于3個,可從土壤生物有效性次高的土壤中(如5.5<土壤pH<7、土壤有機(jī)質(zhì)<2%)尋找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此類推導(dǎo)方法會導(dǎo)致所推導(dǎo)的土壤基準(zhǔn)是基于生物有效性較高的土壤毒性數(shù)據(jù)獲得,生物有效性低的土壤未有相應(yīng)的土壤基準(zhǔn)值。
我國幅員遼闊,由于地域的差異,不同省份的土壤理化性質(zhì)差異明顯[47-52],如果采用美國的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打分制,某些土壤生物有效性低的省份的土壤毒性數(shù)據(jù)不會被納入基準(zhǔn)值制訂基礎(chǔ)毒性數(shù)據(jù)的考慮范疇,導(dǎo)致所推導(dǎo)的基準(zhǔn)值較為嚴(yán)格,如果在我國北方土壤生物有效性低的地區(qū)按照此基準(zhǔn)值參照執(zhí)行環(huán)境管理,可能造成“過保護(hù)”的情況,因此,建議因地制宜,分區(qū)域制訂土壤環(huán)境基準(zhǔn)。如我國《土壤環(huán)境質(zhì)量 農(nóng)用地土壤污染風(fēng)險管控標(biāo)準(zhǔn)》(GB15618—2018)[5]采用了分4檔pH(pH<5.5,5.5≤pH<6.5,6.5≤pH<7.5,pH>7.5)分別制訂了我國的農(nóng)用地土壤篩選值[5],筆者建議我國的基準(zhǔn)研究應(yīng)借鑒農(nóng)用地標(biāo)準(zhǔn)的制訂經(jīng)驗(yàn)開展相應(yīng)的基準(zhǔn)研究工作,分區(qū)域進(jìn)行土壤基準(zhǔn)的針對性研究。
(2)澳大利亞采納本國不同團(tuán)隊(duì)開發(fā)的經(jīng)驗(yàn)?zāi)P痛嬖谝欢ǖ南拗菩院筒淮_定性
澳大利亞在其EILs制訂過程中,采用了本國研發(fā)團(tuán)隊(duì)所開發(fā)的經(jīng)驗(yàn)?zāi)P停{入了針對土壤理化性質(zhì)制訂不唯一的EILs,其方法值得我國學(xué)者參考與借鑒。但其模型涵蓋的生物物種相對有限,導(dǎo)致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使用模型的歸一化后結(jié)果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使用包含土壤理化參數(shù)的經(jīng)驗(yàn)?zāi)P停P捅旧泶嬖谝欢ǖ牟淮_定因素。使用經(jīng)驗(yàn)?zāi)P瓦M(jìn)行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校正,可能與實(shí)際土壤生物毒性試驗(yàn)結(jié)果有所偏差,高估或者低估化學(xué)物質(zhì)在不同土壤中的毒性,建議對不同開發(fā)團(tuán)隊(duì)的經(jīng)驗(yàn)?zāi)P瓦M(jìn)行科學(xué)的甄別與采用。
(3)建議我國針對本國的土壤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進(jìn)行集成,形成共享數(shù)據(jù)平臺,為土壤基準(zhǔn)研究提供高質(zhì)量的基礎(chǔ)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
我國針對土壤生態(tài)毒理已開展了大量基礎(chǔ)科研工作[7-17,47-53],相關(guān)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國內(nèi)外期刊,可在中國知網(wǎng)、Web of Science等國內(nèi)外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庫進(jìn)行查閱。建議我國參考ECOTOX的數(shù)據(jù)收錄方法整理我國已發(fā)表的陸生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對我國的土壤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進(jìn)行集成,利用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等數(shù)據(jù)處理技術(shù)建立中國生態(tài)毒性數(shù)據(jù)平臺[52-53],為我國土壤基準(zhǔn)研究提供高質(zhì)量的土壤基礎(chǔ)生物毒性數(shù)據(j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