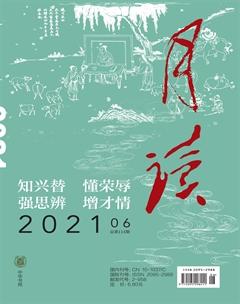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天人智慧(上)
王杰
前幾期介紹了中國哲學的核心概念和范疇、中國哲學發展的基本脈絡等內容。從這一期開始,我們將正式進入主題,系統介紹中國哲學的智慧。
中國哲學的智慧,主要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三大領域,其余智慧都是從這三大領域引申而來。人與自然的關系,其目標就是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問題,解決人類所面臨的自然生態危機問題;人與人的關系,其目標就是解決人與人、人與社群、人與社會的和諧共存問題,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人際生態危機問題;人與自我的關系,其目標就是解決人與自身心理、精神之間的平衡問題,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精神危機問題。
我們首先來介紹中國哲學的第一個智慧: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天人智慧。
從宏觀方面說,中西哲學的最大差別就在于對待天人關系的態度上,其他一切差別都是由此延伸而來。中西方的哲學家們都是站在天人關系的視角探討天與人之間的關系,把天人關系看作自己理論的出發點。
先看看西方哲學。西方哲學發源于古希臘,此地土壤貧瘠,資源匱乏,人們從土地等自然資源中獲取生活資料是極其艱難的,于是逐步發展出了商業,以海上貿易為主要謀生方式。這樣的自然環境使當時的人們對大自然產生了恐懼心理,客觀上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尖銳矛盾。人們需要不斷與大自然抗衡、斗爭,這種矛盾通常以人與神的對立形式表現出來。如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寫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詩人采用神話題材,描述了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下火種給人類而觸怒了宙斯,被鎖在高加索山巖峭壁受苦受難的故事。同時,又賦予神人格化的特征,鼓舞人們與大自然進行抗爭。因此,西方文化更加注重征服自然的技術力量,激發了人們注意觀察自然和分析客觀外界事物的致思方式。這樣觀察分析自然的致思方式,把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對立起來思考,逐步形成了“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宇宙的主宰”的“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和思想特征,并由此衍生出冒險精神強,突出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家庭觀念不強等價值觀。
再看看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的產生與發展同天人關系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古代中國跟古希臘有著不同的地理環境,大部分地區比較適宜發展農耕經濟,因此,中華民族歷來依靠農業維持生存,是典型的“以農立國”的民族。人們的家庭、家族興衰跟農作物的豐歉、農業生產的好壞有著直接的聯系。寒暑時至,風雨調勻,就能五谷豐登,獲得好的收成,稍有不和不順,就會遭受災害,甚至會出現“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人間悲劇。在與大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中國古代先民們既敬畏自然、依賴自然,又愛慕自然、贊美自然,把人作為大自然天然的組成部分,于是逐漸發展出中華文明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天人觀。
農耕生產方式也要求人們按照農時進行生產勞作,重土難遷,比較穩定地生活在同一區域。從而逐漸使人們養成了一種樂于耕種、隨遇而安,追求安穩和諧,重視家庭和社群,以及家國同構的心理習慣。
如果說西方哲學在天人關系上主張天人二分、主客對立,那么,中國哲學在天人關系上則主張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天人貫通、天人合一。西方哲學重視“分”,中國哲學則重視“生”。《尚書·泰誓上》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經》中也兩次提到“天生烝民”。就是說,在古人眼中,這個天并非是與人毫無瓜葛的純粹客體,而是把云行雨施、四時變化的天看作生人、生物的本源和萬物的始祖,并由“生生之本”的根義衍生出其他內涵。所以《周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天人合一是我們把握中國哲學智慧的首要出發點。人是大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天道與人道是貫通的、一體的、統一的。
天人合一既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是自然中心主義,它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這種方式就是把人類與大自然看作一個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一氣貫通的生命整體,人中有天,天中有人。
那么,外在于我們人類之外的天是什么呢?所謂天,在中國思想史上,它的含義有一個演化的過程。在人類早期文明,認識水平有限,對大自然懷有畏懼之心,認為天就是上帝,就是天命;到了周朝,天的神秘性有所弱化。天的含義,從命運之天、主宰之天、宗教之天到義理之天,再到自然之天,經歷了一個演進的過程。我們在談天人關系時,所理解的“天”就是指自然之天,指外在于我們人類的天,也就是自然界。
那么,自然界在中國哲學中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呢?在儒家看來,自然界有其恒常不變的秩序和運動規律,孔子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天雖然不言不語,無聲無息,但春夏秋冬四時依然在輪回,太陽依然是東升西落,日夜依然在交替,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依然在生滅變化,這就是自然界永恒不變的規律。人們通過把握自然界的規律,智慧地透過紛繁的表象,歸納出大自然循環往復的準則,正所謂“天行有常”。人們洞察日月變換的步履,推測草木榮枯的密碼,揣摩天地自然的性情,然后應和著它們的韻律,來安排自己的生產和生活節奏,人的生命與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孟子也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離婁,黃帝時人,生卒年不詳。相傳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孟子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在這里,“日至”是天文歷法術語,古人稱冬至和夏至為“日至”;冬至叫“日短至”,一天中白天最短,夏至叫“日長至”,一天中白天最長。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那么高,星辰那么遙遠,如果了解了星辰的運行規律,那么,千年之內的冬至都可以推算出來。再如哈雷彗星,在《春秋》《史記》等歷史典籍中都有記載,一種說法是,魯文公十四年(前613),《春秋》中有“有星孛入于北斗”的記載,不少中外學者把這次記錄看成是對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史記·秦始皇本紀》關于“(秦始皇)七年(前240),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的記載,是世界上最早對哈雷彗星的記錄。孟子的預言具有真理性,他說如果了解了事物的客觀運行規律,那么未來的運行規律是可以推算出來的。孟子還論述過盡心、知性、知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思想。
荀子也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就是說,天有其恒常的運行規律,不因為堯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為桀的滅亡而滅亡。他還說:“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是說天不因為人討厭冬天就沒有冬天了,大地不因為人討厭它太遼闊就不再廣袤無垠了。荀子論天的主旨還是順應其客觀規律來歸于人道。一方面,他突出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其仰慕“惟天為大”,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現象去把握;與其“順天”“從天”,不如掌握自然規律去利用;與其仰望天時而等待恩賜,不如因時制宜地利用天時;與其消極地聽任物類的自然增多,不如積極施展“人治”的才能去促進物類的化育繁殖。另一方面,他又主張人不應該對自然濫加干涉,過度而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就是說,如果順應自然的運行規律,抓住農業這個根本,并且厲行節約,那么老天就不會使人貧困。有充分的養生之資,并按季節活動,那么老天就不會讓人患病。
上面主要是以儒家思想為例來闡釋天人關系,下面再看看道家。《老子》第二十五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段話說的是,有一種物體混混沌沌、無邊無際、無形無象無音、渾然一體,早在開天辟地之前,它就已經存在了。它獨立存在,無雙無對,遵循著自己的法則而不會改變,循環往復地運行而不會停止,它可以作為世間萬物乃至天地的根本。我不能準確地描述出它的本來面目,只能用“道”來籠統地稱呼它,勉強稱之為“大”。“大”就是指不停地運轉、變幻,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遠不至,穿行于古往今來、八荒六合之間,到達極遠處又返回到事物的根本。正因為“道”是如此幽深奧妙、無窮無盡,所以說“道”很大,遵循于“道”的天、地、人都很大。宇宙有四“大”,人也是其中之一。人必須遵循地的規律特性,地服從于天,天以“道”作為運行的依據,而“道”就是自然而然。《莊子·知北游》也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意思是,天地萬物具有偉大的美但無法用言語表達,四時運行具有固定的規律但并不刻意宣傳自己,萬物的變化具有現成的規則但無須加以談論。莊子還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是大自然的產物,與大自然具有相同的物質基礎,是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圣人最高的境界就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莊子·秋水》中記敘了莊子和惠子關于“魚之樂”的一段對話。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即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與惠子在濠水橋上游玩。莊子說:“鯈魚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閑,這是魚的快樂。”惠子說:“你不是魚,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呢?”莊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呢?”惠子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魚,本來也不了解魚。”莊子又道:“請從最初的話題說起。你問‘哪里知道魚兒的快樂,你這么問,說明你已經承認我知道魚的快樂,所以才會問我怎么知道的。我是在濠水岸邊,知道魚是快樂的。”從這段對話我們可以看出,惠子是富于現實理性的,其推理也是合乎邏輯的。而莊子運用的是“天人合一”的認識構架,超越現實理性的態度,達到我與物、內與外相合,“萬物一體”的心境。此時,人就進入一種非理性認識的審美中,進入“莊周夢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的“物化”狀態。這些無不體現著“與人和者謂之大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人合一的“天人之樂”。
《列子》中也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宋國國君叫一位巧匠將玉石雕成樹葉。三年以后雕成了,把這片葉子放在樹上,誰也難以辨出真假,因此國君非常高興。但列子聽了這件事后,便說:“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表達了對大自然的贊美和對人為觀念的譴責,告訴人們應該順乎自然,將人與自然視為一個整體。
無論是孔孟荀,還是老莊列,他們所說的“天”,已經沒有了什么神秘的含義,就是指外在于我們的自然界,他們所要表述的是這樣一個道理: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雖然變幻莫測,但其實都有其固有的運行規律,這種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這種規律是可以被我們人類所認識的,認識了這種規律,就可以服務于我們人類。只要嚴格按照自然規律辦事,就能夠做到趨利避害、逢兇化吉,若違背了自然規律,就會遭到大自然的懲罰,這也就是孟子說的“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歸結為一句話,自然界是獨立于人類而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體。這是第一個需要說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