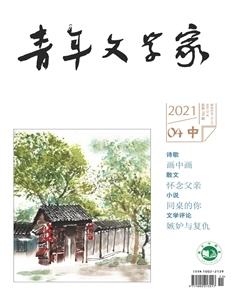曹文軒兒童小說敘事藝術(shù)研究
李莎
自從小說理論誕生以后,小說的觀察角度成了學(xué)術(shù)界的流行術(shù)語,視角成了學(xué)術(shù)界的一個關(guān)注焦點(diǎn)。申丹指出:“‘視角或‘?dāng)⑹鲆暯侵笖⑹鰰r觀察故事的角度。”視角問題在以往曹文軒小說研究中,可以說是不太受人注意的,但它在曹文軒藝術(shù)中是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了解曹文軒小說的視角形式的變化,有助于我們把握曹文軒小說創(chuàng)作藝術(shù)的變化發(fā)展,使我們更能深刻領(lǐng)會曹文軒創(chuàng)作藝術(shù)上不成熟到成熟這一藝術(shù)變遷軌跡。
一、第一人稱敘事的“真實(shí)性”
曹文軒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視角藝術(shù)上最大特征在于其“真實(shí)”,表明一種生活的真。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會因自身的切身經(jīng)歷而聯(lián)想到小說中的故事情節(jié),拉近小說人物與讀者的距離,因此讓小說充滿了感染力。
曹文軒在他的《紅瓦黑瓦》中用第一人稱講述故事,這樣的視角占有比較突出的地位,第一人稱敘事視角類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主人公”類型,一種是“目擊者”類型。“主人公”類型的敘事主要表現(xiàn)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目擊者”類型是站在故事的邊緣講述故事,作為一個旁觀者將觀察到的事物表現(xiàn)出來。
他從小生活在貧困的農(nóng)村,從小受到過貧窮、疾病的折磨,他十分渴望人間的溫暖。在他的小說中不光有自己抒發(fā)內(nèi)心苦悶的情節(jié),更有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在緊緊地拉扯著他。因此使得小說帶有明顯的自敘性特點(diǎn),深深地感染著讀者。敘事視角大都采用“主人公”類型視角,情感的表達(dá)帶有宣泄的特征。不可把握的世界中,“我”因害臊的毛病,被別人取了個“公丫頭”的外號,這讓“我”很自卑,因家里的貧困,而無法在自己喜歡、家境富有的陶卉面前抬起頭。在《馬戲團(tuán)》中,“我”只能以幫忙搬東西的狀態(tài)來親近秋這個女孩子。而在《快戽干了水的池塘》中,一次大串聯(lián)中“我”對像陶卉這樣的女生是愛而不得的苦悶。對于這樣一個極美的女孩“我”不由自主地盯著她的胸脯看,在大家睡在同一個房間,因她均勻的呼吸聲,幾乎一宿沒睡著,甚至為自己不小心碰到了對方胸脯,是羞得滿臉通紅,產(chǎn)生一系列的臆想。
在《紅瓦房》中的“我”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別人,而唯有在學(xué)業(yè)上是值得驕傲的。而在即將走出紅瓦房時,由于家庭原因,“我”似乎要結(jié)束在油麻地的讀書生涯。“我”以逃避的方式躲開同學(xué)們,這里展現(xiàn)出對自己前途無望的一種焦慮和不安。《大隊干部的通知》里,“我”因前途的徹底無望,有著要一輩子當(dāng)農(nóng)民的苦悶,于是整天躺在床上,甚至準(zhǔn)備接受自己的命運(yùn),并開始著千篇一律的勞動。而這一切又因生產(chǎn)隊長的一封通知書而重新給了“我”讀書的希望。因為杜長明的下臺,唐文甫奪了權(quán),“我”才得以再次踏入學(xué)堂的大門。在小說中的敘述者“我”與“曹文軒”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抒發(fā)了“我”在童年時代的純真情感,以及對童年生活的美好回憶,并且以兒童第一人稱的角度,也看到鄉(xiāng)村的黑暗一面。在這里兒童的世界不僅僅只有美好,也有苦難。在《根鳥·菊坡》中,根鳥打獵時拾得一塊布條得知紫煙的情況。她以自己叫什么名字向根鳥介紹自己,因采花掉到了山谷里,并且她自己還在白色鷹的腳上綁了一封信,她想讓根鳥救救自己。小說由一塊布條上的消息展開,從此根鳥踏上了尋找這個開滿花的山谷之路。
曹文軒運(yùn)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講述自己農(nóng)村的生活經(jīng)歷,帶有郁達(dá)夫小說的自敘性特征。小說的敘述基于他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抒發(fā)作者自身真摯的情感,因此在小說中處處透露著真實(shí)動人的情境。
二、故事的“講述”
曹文軒在他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大多是以講故事的形式出現(xiàn),故事的“講述”是曹文軒敘事藝術(shù)中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曹文軒強(qiáng)調(diào)小說的故事性,小說有明確的地點(diǎn),有的時間也很清晰,人物也生動形象,這給小說營造了濃厚的故事氛圍。
曹文軒小說中故事的講述主要有這樣的兩種類型:一種是由我出面向讀者講故事。如《紅瓦黑瓦》中以“我”的視角出發(fā),呈現(xiàn)了與“我”相關(guān)的一系列的事,學(xué)習(xí)生活、身邊的朋友、大串連等都緊緊圍繞著“我”而展開故事。從主人公的視角看到人情的冷暖,也看到生活的酸甜。還有一種以他在小說中設(shè)置一個故事框架,由小說中的人物向別的人物講述故事。如《草房子·艾地》的秦大奶奶,主人公“我”講秦大奶奶夫妻倆以前是如何辛苦才換到了這樣一塊土地的。讀者的視角由近處拉往遠(yuǎn)方,最終又回到現(xiàn)在他們在土地中央蓋了一幢草房。而《紙月》里的紙月的來歷,由桑桑聽到父母親破碎的講述,連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紙月的母親懷孕了,但不知孩子生父。有一天紙月母親離家出走,幾天后,人們在池塘里看到了她的尸體。最后紙月由外婆養(yǎng)活。《藥寮》中溫幼菊的屋子常年都飄著藥香味。她講述自己幼年和外婆相依為命的悲苦生活,并為桑桑煎藥,還鼓勵他勇敢地跟病魔做斗爭。作者意在推動故事情節(jié),讓讀者能夠更加深入地進(jìn)入故事的情節(jié)。作者有意為之的小說情境,意在讓少年體驗成人世界中生活的無奈、不屈,同時也體現(xiàn)了曹文軒對兒童少年深切的人文關(guān)懷。而《根鳥》里通過板金之口,講自己失去了做夢的能力,為了找清楚原因而踏上旅途,途中因饑餓偷紅薯被主人家抓到后的釋然,并繼續(xù)著自己的找“夢”之旅。紫煙向根鳥講自己的故事,讓他踏上尋找的路途,以及根鳥回村后向身邊人講述自己路途中的見聞。作者是意在讓少年人敢于追尋自己的夢想,勇于面對困難。曹文軒在小說中運(yùn)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式,通過第一人稱和小說人物講故事的方法,讓故事波瀾起伏,推動故事的發(fā)展。
三、敘事主體的多重轉(zhuǎn)變
曹文軒的小說中除了第一人稱敘事,還有全知敘事,而有時小說中敘述又會變成小說里的人物敘述。曹文軒小說中第一人稱敘事、全知敘事與人物敘事一起組成小說的敘事,這就造成了小說中敘事主體的多種變化。
《草房子》里講“他”去看石磨時,發(fā)現(xiàn)石磨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沒有。“他”抬起頭看月亮?xí)r,發(fā)現(xiàn)四周很是寂靜,也是什么也沒有,所以很是失落。在這樣的空寂環(huán)境中,他忍不住罵了幾句臟話后再回家,以此來發(fā)泄他心中的不滿。在這里,作家使用第三人稱“他”來敘述此刻周遭的環(huán)境和人物的心情。這里的“他”即是桑桑。而從桑桑自己的敘事角度來看待周圍一切的時候,也表現(xiàn)出了桑桑的心情。作者在這里是用了一種內(nèi)在的聚焦視角,這讓人看起來是桑桑但似乎又不是桑桑。其實(shí)作者意在借用桑桑的聲音拉近讀者與文本的距離,讓讀者覺得更親切、真實(shí)。用桑桑的眼光和聲音感受著大自然周圍的微妙變化,這不單是人物的體驗,也是讀者的體驗。這是桑桑的視角與聲音的重合所造成的敘述現(xiàn)象,但并非所有的都是重合的,也有分離的現(xiàn)象。在曹文軒的小說《紅瓦》中便有大量存在,以第一人稱結(jié)構(gòu)全篇小說。“我”作為敘述者,讓讀書時的這個“我”既是主人公又是觀察者和旁觀者。小說的開頭是1965年的秋天,“我”終于考上了夢寐以求的油麻地中學(xué)。從過去切入,敘述者與人物之間的距離呈現(xiàn)出忽遠(yuǎn)忽近的感覺。《草房子》一開頭以1981年秋天的上午,桑桑坐在房頂上想著要告別和他相伴已久的草房子而傷心拉開故事的帷幕。這篇成長小說,是用全知角度,以平行分布的角度進(jìn)行敘述。小說沒有一個中心的人物或事件,小說一共九章,每一章節(jié)都刻畫了一個人物,小說的全篇可以說是描繪了一幅兒童少年群像圖。小說中看似渙散的結(jié)構(gòu),實(shí)際上卻讓小說變得很緊湊。作家以油麻地小學(xué)為小說的發(fā)生地,以桑桑的經(jīng)歷為小說的線索,把文中的人、事連結(jié)起來,使全篇結(jié)構(gòu)圓滿、嚴(yán)謹(jǐn)。
全篇第一個人物是禿鶴。由于身體的缺陷他從小是個小禿子,當(dāng)他年幼時,面對別人給他起的外號付之一笑。等他稍懂事,他懂得禿頂不是一件好事,用帽子遮擋,而桑桑摘去他的帽子,兩人引發(fā)了大戰(zhàn)。最終,他克服了自卑心理,飾演了禿頂連長,取得演出的成功。
紙月是作者著力塑造的一個女孩子,紙月長得秀美,寫得一手好字,成績也很好。紙月的魅力深深吸引著桑桑,他不由自主地向紙月看齊,他竭盡全力表現(xiàn)自己優(yōu)秀的一面。終于有一天,紙月消失了,和她一起消失的還有慧思和尚。
《草房子》從桑桑的視角以平行式且分布敘述的角度講述少年的成長故事,小說以其特有的敘述結(jié)構(gòu),有序地刻畫了油麻地小學(xué)中的各色人物。這樣的敘述策略,讓小說的視野開闊,里面的人物形象立體可感,同時又讓人物具有不同空間維度的可感性,使得小說內(nèi)涵變得綿遠(yuǎn)悠長,也充分體現(xiàn)出了作者關(guān)注兒童的生存現(xiàn)狀,關(guān)愛兒童的創(chuàng)作初衷。
基金項目:吉首大學(xué)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19SKY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