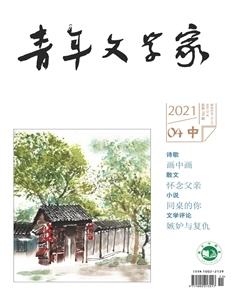凱·瑞安的游戲詩人觀解讀
黃純
凱·瑞安(Kay Ryan,1945-)是當代美國詩壇的一匹黑馬,雖進入評論界較晚,但憑借其獨特的游戲詩歌魅力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位。她曾在《詩歌之我見》中多次表達詩歌的娛樂性,認為一首完美的詩歌應該像一場精妙絕倫的魔術表演,能讓觀眾自然而然地發出“哈”的驚嘆。她的詩歌也處處充滿了魔術般的游戲元素,穿梭于斷裂模糊的詩語間的詩人若隱若現,為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罩上一層神奇夢幻的薄紗,喚起讀者對捉迷藏般的文字游戲的熱忱,激發讀者對缺失的文字意義的追尋,給予讀者一場新鮮刺激的情感體驗,振蕩了讀者的心靈。
一、日常的游戲 意義的狂歡
荷蘭文化史學家赫伊津哈認為“詩的創造性功能根植于一種真實比文化本身更為原初的功能中,它便是游戲”。凱·瑞安于2015年發表的詩集《Erratic Facts》標題中的 “erratic”是她的詩歌創造性的游戲精神的恰當表達。她對詞源如此解釋道,“erratic”一詞是地理用語,指的是被冰川搬運至離它的起源地一段距離的鵝卵石。詩人將她的詩歌與鵝卵石建立聯系,由此鵝卵石便具有了隱喻意義。鵝卵石被搬離原點這一行為在空間上區別于它的原點,而在時間上具有拖延性與滯后性,意義便在凱·瑞安搬運鵝卵石的過程中便向四面八方“延異”開來,在這一過程中詞的原義發生了消解,“所指”和“能指”的符號鏈出現了斷裂,依賴與其他詞的銜結聯系,依賴整體世界觀的揣摩,建構了意義此時此刻的在場,產生了“所指非指”的游戲效果,由此文本成了狂歡廣場,凱·瑞安把一切看來荒誕無稽又出乎意料的東西賦予新的理解,并把它們組織到各種狂歡式的場面中來,從而創造它們的藝術真實。
喬伊斯認為藝術家“每天把經驗的面包變成光芒四射的永生之體”。凱·瑞安便是如此,在日常生活的河岸邊挑選鵝卵石,以日常經驗為材料,切換不一樣的視角描寫生活中沒有修飾的、簡素質樸的事物,“用文體安置它們,將神秘注入其中,以便每個意象都蘊含對奧秘的回答”,再佐以對韻律、構詞、視圖、敘事獨特的藝術處理手段,將其“陌生化”以便打造超越日常生活的游戲空間,從而詩歌“走出真實生活而進入一個暫時的別具一格的活動領域”。就如這首《新衣》:
“那位皇帝/被裁縫們哄騙/對你而言是熟悉的。/但是那些裁縫/一直改變/他們的手法/去賺錢。/(裁縫是指/讓某物/適應某人。)/一準兒/他們會發現/你的自尊。/你會丟棄/你所珍視之物/當裁縫們/低語,/‘只有你能穿這件。/幾乎它從不是衣服/皇帝買的那件/但是它卻接近/你所擁有之物。”
裁縫推銷兜賣的并不僅僅是衣服,而是讓你“被發現自尊”,建立自我身份的某物。凱·瑞安在此對童話這一日常題材加以“陌生化”藝術手段處置,擴大“新衣”的范圍,發掘經典童話的現代意義。現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不可避免,大規模的商品消費不僅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生活方式,也悄然影響著我們看待自我、他人與世界的態度。鮑德里亞認為,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現代社會已經是一個產品過剩的消費社會。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主體性喪失,忽視自我情感上的需求,對自我的確認和認同建立在對物、對符號的追求之上,是被物質和符號主宰的客體。在現代這樣一個被“新衣”包圍、充斥、占有的世界,“新衣”變換著各種樣貌,以各種光怪陸離的形式遍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裁縫”并不量體裁衣,因為“國王”并不在乎“新衣”是否保暖,是否美觀,是否合適他的身形,反而他們會“削足適履”,會去適應“新衣”,因為他們的自尊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被“新衣”發掘的,被“新衣”代表的社會符號、文化符號所建構的。新時代的“國王”被同樣的手段哄騙,去追逐同樣虛無的“新衣”,沾沾自喜著,卻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身無一物,內心空虛貧瘠。凱·瑞安舊調重彈,對經典童話《國王的新衣》加以改寫,突出了現代消費社會人被物質奴隸,被符號控制的精神異化危機。
二、作者的缺席? 讀者的參與
浪漫主義詩人傾向于在詩歌中直抒胸臆,表達自我,而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詩人則更像是“隱蔽的上帝”,隱身于詩歌敘事的背后。凱·瑞安一般不出現她的詩歌里,將自己置于話語中心之外,在她的詩歌集里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的詩歌寥寥無幾,就連這首蘊含了深刻哀思的愛情挽歌《Polish and Balm》凱·瑞安還是同樣盡力遏制自己的情感,維持著冷靜節制的旁觀者形象――拋光劑和香油是離去的人遠走前所摯愛之物,如今已遍布灰塵。本是寄托美好記憶的紀念品已失去了它慰藉的功能。凱·瑞安卻好似隔離克制了這份深切的哀傷與悲痛,只淡淡地重復訴說“誰知道”“我們知道”。而詩歌《Impersonal》更是直接表達了她去個性化的創作理念。“只有非個人的/才是新月/像月亮一樣明亮/對稱的一瞥”
盡管凱·瑞安在她的詩歌里竭力保持缺席的姿態,“優雅的遏制”,但正如她在采訪中所言“實際上,我們無法藏起來”,詩人本人的個性過渡到了敘述本身當中,像一個生命的海洋,和緩寧靜地包裹著意象,在意象周圍涌動。正所謂“缺席乃是在場的最高形式”,凱·瑞安就像創造萬物的上帝, 她的意識溫柔平緩地流動在詩歌空間的每句言說,每個角落。
詩歌空間是一個開放的空間,正如她的詩歌《理想讀者》所言,凱·瑞安對理想讀者的定義超出世俗的限制,不分國籍,不談種族,不辨階級,甚至不論生死,她的詩歌是寫給大眾的日常贊歌,但是這同樣也是一個只由詩人和讀者共享的隱秘空間。在這樣隱秘而又開放的游戲空間里,片段化敘事盛行,意義在碎片的間隙處穿梭,偶然交叉或彼此錯過,留下大量的空白。凱·瑞安認為“藝術的一個因素是她與讀者的交流”,她重視讀者的力量,邀請讀者進入詩歌的空間去填寫空白,提倡詩人與讀者情感的共鳴。而讀者需要沿著拼圖的斷層補全邏輯的缺省,敏銳地抓住敘事的一鱗半爪以管窺豹,借助聯想或想象架起虹橋溝通“存在與理念之間的永恒鴻溝”,而意義的重新連貫,結構的重新銜接則指向“顯靈頓悟”的出口。
就比如在凱·瑞安的詩歌《云》里:
“一塊藍色的污漬/爬行穿過/草地上的/長毛絨。/從里面/看起來森林/像是/一件本質的/事物/完全與樹有關,一種顏色/從一種過渡到另一種,一種/要求/他們/絕不妥協地服從/像士兵/勇敢的人/逐漸衰老。/然后太陽/回來了/一切都結束了。”
一般認為詩的標題即主題,然而凱·瑞安卻對作為主題的“云”只字不談,轉而圍繞著草地、長毛絨、樹木、太陽等等意象構建畫面。但在凱·瑞安的鋪色、描繪、敘述之下,“云”卻好似無處不在,它投下的影子遍布了詩歌的每一個角落。草地上留下的藍色的污漬是它飄過的痕跡,樹林的明暗變化是它施展的巫術,無論是多么無畏的戰士也無法逃脫被它投影、蠶食、覆蓋的命運。整首詩里包裹著一層薄霧似的淡淡的恐慌。而這種縈繞心頭的危機感就像是天空中浮著的那層云一樣是不明的,隱藏在詩歌的淺層敘事里。在凱·瑞安創造的詩歌空間里四處彌漫著捉迷藏似的游戲氛圍,字里行間意義的突然斷裂,打破了讀者預期的期待,留下了意義自由嬉戲的場所,詩人和讀者作為一個游戲共同體,詩人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編撰者,截選日常的片段施以“陌生化”的手段,開放了詩歌的入口,悄然等待著讀者的來臨,進入詭秘奇特的幻想空間。而當作為游戲的參與者的讀者和詩人產生共鳴,幻想空間和日常空間互相重疊,短短的十幾句詩行有限的場所和空間猶如宇宙星辰聚變一般爆發出巨大的能量,成就了超越日常生活的純凈的神性世界。
三、結語
凱·瑞安以其特有的游戲詩人視角,敏銳地觀察生活,描寫日常同時也超越日常,在一種輕松愉悅的游戲氛圍里“創造一種‘陶醉讀者并使其心馳神往的張力”,帶領讀者超出普通現實步入更高的游戲秩序,獲得純粹神秘、深刻雋永的心靈洗滌和情感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