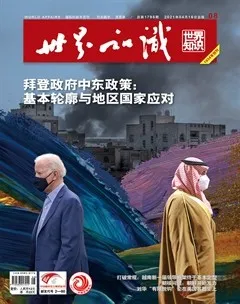對華“有限脫鉤”論在美國甚囂塵上
安雨康
2020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將“結束對華經濟依賴”作為其“第二任期”的重要目標,其政策團隊大肆鼓吹政治、科技、金融、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全面脫鉤”和對華新冷戰。拜登贏得這次大選上臺后,其政策團隊反對“全面脫鉤”論調,但認為美國必須減少關鍵領域的中國依賴。在此背景下,如何阻止中國獲得在供應鏈中的主導性優勢,又維持同中國“必要的”技術和貿易聯系,成為拜登對華政策審議的一個焦點性問題。近來,美府院、智庫大肆鼓吹“有限脫鉤”“有選擇的脫鉤”“針對性脫鉤”等論調,試圖對決策施加影響。
“小院高墻”似已成主流認知
美部分保守派政客聲稱,中國高科技產業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主導優勢構成“巨大威脅”,美應以強硬、有力的“科技脫鉤”迫使中國屈服。美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認為,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5G等領域實施了雄心勃勃的“重商主義政策”,美在一些領域已明顯落后,必須在科技政策層面做出反制。傳統基金會認為,中國高度重視自主科技創新的“十四五”規劃將繼續激化美中矛盾。極端反華的聯邦參議員湯姆·科頓發布了《擊敗中國——針對性脫鉤和長期經濟戰爭》報告,鼓吹“針對性脫鉤”,呼吁撤銷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待遇,禁止中國學生在美從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學習研究,禁止向中國實體銷售美國研發或制造的半導體設備和設計工具,降低對中國的稀土依賴并最終禁止自華稀土進口,等等。該報告還建議強化對中國經濟和技術情報的搜集,建立美國主導、類似巴黎統籌委員會的5G技術聯盟。
多數自由派智庫認為,以當前的美中互動模式,真正問題不在于會不會“脫鉤”,而是“有限脫鉤”將達到何種程度,對美國的影響是否可控。美應推動“小院高墻”式的“選擇性脫鉤”,比如,在保持美國對全球人才和投資開放性的同時,將中國徹底與美國涉及國家安全的關鍵產品和關鍵技術隔絕;對不涉及國家安全、不影響美供應鏈主導優勢的經貿、人文交流合作,則審查后放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多份報告提出,美中一定程度的“科技脫鉤”不可避免,美對中國半導體和半導體制造商的出口管制、限制華為和中興參與全球范圍內5G項目建設,都有助于減少美及盟友對華依賴。在另一份關于美中接觸框架的報告中,該中心認為,美應避免“廣泛脫鉤”,同時對可能損害美利益的特定領域“脫鉤”持一定靈活性。
辛里奇基金會認為,美應以重點領域“脫鉤”、回流和“圈護”策略,回擊中國的“經濟技術民族主義”,比如強化出口管制政策、引導臺積電在美辦廠。布魯金斯學會認為,美中在電信和其他高科技領域的“脫鉤”不可避免,互信的淺薄程度根本無法支撐雙方在這些領域的相互依存。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美國的科技人才儲備和芯片制造能力優勢正在急劇減弱,美中在人才、技術交流領域的“廣域脫鉤”只會使美失去稀缺的科技人才,并阻擋美國初創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并獲得中國投資,美應以“針對性脫鉤”保護關鍵行業。
在智庫游說層面,保守派和自由派對于如何實現“針對性脫鉤”,是有賴于引導海外產業回流美國本土的“供應鏈獨立”,還是基于美國盟友伙伴國家網絡構建“供應鏈聯盟”,存在明顯差異,其背后反映的卻是美國深切的產業鏈主導權焦慮,即,在中美科技競爭背景下,美是應作為“領先國家”,繼續將生產環節外包以提高生產效率,還是作為“守成國家”,通過主動創造本土需求、積極承接外部(盟國)需求來加速“產業回流”。
本土生產成本過高一直是美半導體、醫療、新能源等產業實現“美國制造”的難關,相關產業不斷呼吁政府增加補貼。湯姆·科頓等人要求“將美國就業和出口擺在雙邊貿易協定的優先位置”,“加強對研發活動的聯邦支持和技術管控,恢復到冷戰時期水平”。這種極端的“本土產業優先”主張得到了行業團體、鐵銹帶工會的認可,它們呼吁拜登政府用更強勢的“購買美國貨”計劃為本土產業創造需求。
正轉化為實際政策
民主黨政策層則有觀點認為,不必放棄特朗普的“經濟繁榮網絡”和“清潔網絡”倡議,而應以此為基礎構建印太、美歐更緊密的“供應鏈聯盟”。五角大樓“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的拉特納、羅森伯格和梅蘭妮·哈特都曾提議通過提供補貼等方式,在美及其盟友之間建立“半導體同盟”。經濟策略研究所的普雷斯托維茨認為,美應聯合歐盟、印度、日本等國,建立類似“中國制造2025”的“自由世界制造2030”戰略,保持在大客機、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領先地位。普雷斯托維茨承認,安全盟友間的“供應鏈同盟”并不一定意味著美在供應鏈中地位和影響力的強化,相反可能因規模經濟的優化、分工的精細化,進一步加速供應鏈的“去美國化”。白宮國家安全理事會中國事務高級主管杜如松批評英特爾公司將半導體制造業務外包,使美國喪失了“關鍵的知識和創造力”。另一位高級主管格維茲則主張“選擇性脫鉤”,即在中國供應鏈使美國及其盟國造成“不可接受的劣勢”時應“完全脫鉤”,在損害有限時則通過“供應鏈多元化”加以應對。

2021年3月20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經濟峰會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主題為“邁上現代化新征程的中國”。圖為美國特斯拉公司CEO馬斯克通過視頻發言。
圍繞供應鏈主導權的“針對性脫鉤”可能已成為美對華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2月24日,拜登簽署對半導體、電動汽車大容量電池、稀土和醫療用品的關鍵產品供應鏈審查令,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3月12日,在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峰會上,四方同意成立“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工作組”,約定就“關鍵技術供應鏈”展開對話。在3月18日安克雷奇中美高層戰略對話舉行前,美國將華為、中興、海康威視等中國科技公司的電信設備和服務列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通信設備和服務清單,并出臺針對聯通等三家中國電信運營商的在美運營禁令。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飛赴歐洲,國防部長奧斯汀飛赴印度,“供應鏈同盟”問題成為美歐、美印之間更重要的雙邊議題。
無論是“全面脫鉤”,還是“針對性脫鉤”,都遭到美工商界反對。《華爾街日報》報道,拜登政府正在準備針對信息和通信技術供應鏈的行政令,涵蓋美中幾乎所有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網絡、互聯網軟件、無人機等技術的交易。美國商會就此發表聲明稱,商務部將因此獲得“幾乎無限的權力干預美國公司與涉及技術的外國同行之間的任何交易”,對美中電信和金融服務合作造成嚴重沖擊。
面對中國超大規模的生產能力和消費需求,美國如在供應鏈環節主動同中國“脫鉤”,必將面對“喪失對中國技術發展的影響”“損害美國的技術和市場優勢”“加速中國自主研發”的三角難題,不僅無法阻止中國增強新興技術優勢地位,反將阻擋美國企業獲得中國的市場和資金。美將產業鏈、供應鏈泛“政治化”和“武器化”的作法無法解決美國面臨的產業問題,只會更加激發中國維護產業安全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