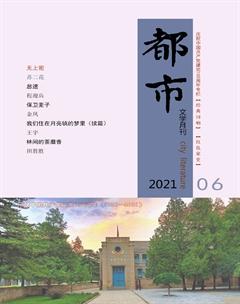長大后,我成了你
2020年2月,當山西省第二批援鄂醫療隊隊員王婷,在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看到家鄉人千里迢迢送來的蘋果與牛肉時,恍惚間想起爺爺講過的故事,老百姓給八路軍送糧食、納鞋墊……她也在一瞬間理解了什么叫“軍民魚水情”,理解了什么叫眾志成城。
那些從爺爺身上傳下來的故事,竟然再一次上演。而她,成為故事中人。
“來到武漢,突然覺得找到了方向。”王婷坦言,“就是那種平素很少說的信仰。一聲號令,大家不講條件往上沖!”
信仰這個詞,就這樣從爺爺身上傳給了“80后”王婷。
王婷出生在一個醫學世家,這也是一個革命家庭。她的爺爺叫王金全,這個名字還是1937年他參軍時部隊首長給他起的。王金全起初是八路軍總部特務團的一名衛生員,后轉至八路軍武工隊。他從抗日戰爭一直打到解放戰爭,從太行山一路打到海南島。他參加過著名的“皮旅突圍戰”,以及第一批南下后在桐柏地區的戰斗。剛參加革命時,爺爺是一名扛槍的戰士,但戰斗中常常有人受傷,他就兼職當起了救護。當有戰友負傷,他便放下槍進行包扎,還學會了給骨折傷員固定復位。等傷員被抬離戰場,他便又立即返身繼續戰斗。
就這樣,一路戰斗,一路受傷,王金全的腰部有彈片傷,左手有刀傷,腿上有槍傷。最嚴重的一次,是南下時攻打襄樊城,一顆子彈從他的頭部穿進去,將他的視神經打斷,自此,王金全的右眼失去光明。他最后一次負傷是在四野四十軍時期,痊愈后,他又一路跟隨部隊打到了海南島,參與了我軍第一批陸軍轉編海軍的過程,成了南海艦隊的一員。解放廣州以后,因地方急需大批干部,積累了許多戰地救護經驗的王金全,就帶著甲級三等傷殘的身體,轉業到廣東省人民醫院當了一名醫生。
在廣州,王金全結識了同樣從部隊轉業到廣東省公安廳醫院工作的妻子,也就是王婷的奶奶。1964年,夫婦二人回到家鄉,在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繼續獻身醫療事業。
巧的是,王婷的姥爺賈小本,經歷幾乎與她的爺爺一樣。姥爺1946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后參加了晉南戰役與淮海戰役等重大戰役,還因作戰勇敢榮獲兩次三等功。后跟隨陳賡率領的第二野戰軍南下到了大西南,曾任原成都軍區昆明總醫院某部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后,賈小本繼續在部隊工作,由于表現突出曾受到通令嘉獎。1962年,他隨部隊到達老撾,把兩年時間投身在公路建設中。彼時,他克服了生活艱苦、任務艱巨的困難,團結和帶領所屬指戰員完成了筑路任務,再一次受到部隊的通報表揚。回來后他又遠赴邊疆,為保衛與建設邊疆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8年,姥爺轉業,回到長治市第二人民醫院擔任總支副書記,直至1990年9月離休,他一生樸實的作風,以及一個老黨員老干部的高風亮節,也一代代傳了下來。
王婷的爸爸王衛國,退休前是長治市和平醫院放射科的副主任,她母親也在醫院工作。出生在白衣世家,又從小生活在醫院大院的王婷,耳濡目染的都是救死扶傷,因此無須刻意,高考填報志愿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醫學專業,仿佛一切都是那么順理成章。
2003年初,非典型肺炎疫情爆發。那一年,王婷滿十九歲,剛上大學不久。學校封校后,在到處彌漫的84消毒液味道中,王婷想到爸爸從事的工作,想到他也可能在被這種可怕的病毒包圍著。躲在宿舍的她非常擔心爸爸,于是就鋪開紙,給爸爸寫了一封信:
爸爸:
遠思!
真的好想您,也好牽掛您!SARS疫情在一天天嚴重,患病人數在一天天增多,聽說咱們醫院為長治市定點醫院,已有五位患者。您和媽媽一定小心呀!
作為一名醫護工作者,救死扶傷,是我們的責任,義不容辭。所以我參加了大同市紅十字會,具體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點我明白,我是學醫的,將來必定是個醫生。也許我不會是個好醫生,但只要病人需要,我會不顧一切挺身而出的,您放心。我是您的女兒,骨子里流著您的血,我有正義感。
……
學校已經封校了,也每天消毒、清潔,不用擔心我。學校說最好的方法就是原地不動,因此“五一”我不準備回家了。您不用掛念,更不用開車接我。
倒是您!作為女兒,很是擔心您,卻無力為您分擔。您是醫務工作者,且直接與患者打交道。盡管醫院的防護做得很好,但我依然很擔心,您一定小心!
聽說太原封城了,您就別再往太原跑了。也別出去吃飯了,好好在家待著!
好嗎?
好了,不多說了,祝您和媽媽一切都好!
婷婷
這封信2003年4月23日由山西大同發出,26日到達長治。
只是,她不知道,寫滿牽掛與叮嚀的這一封信到達爸爸所在的醫院時,爸爸早已經沖上了太原市第四人民醫院的抗疫第一線,這里正是她信中擔心的城市。
“其實我當時知道,如果爸爸做出決定,我的阻止是沒有用的,我了解他。”
確實是。支援太原之前,王衛國已經吃住在醫院的感染科半個多月了。他所在的和平醫院是長治地區的定點收治醫院。當時,對病人的診斷檢查全靠X光片,因此王衛國經常全副武裝,深入到病房進行檢查。之后,省城太原告急,單位立即響應,組建了醫療隊馳援。動員會剛剛結束,王衛國便積極報了名,并很快與兩名同事一起,組成放射醫療小組前往太原展開工作。
出發那天,王衛國突然在醫院送行的隊伍中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母親,她是坐著輪椅來的。他心里驚了一下,因為害怕母親擔心,他并沒有告訴母親這件事。然而,他忽略了他身處的是醫院家屬區,這么大的事兒,母親怎么會沒有耳聞呢?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母親深知兒子此行有諸多風險,因此她緊緊握著兒子的手說出一句話:“國家需要,你就趕緊去,千萬不要給我敗興回來!”
果然是軍人風范,果然是醫生品格。王衛國一顆懸著的心放下來了。
“媽,放心!”他愉快地給母親撂下這句話,就轉身奔赴疫情一線。
當時走得緊急,醫院給每位醫生配發了一個行李箱。沒有來得及帶更多的東西,這只行李箱,陪伴王衛國在太原度過了漫長的一個多月,并最終凱旋而歸。
沒想到十七年后,走上工作崗位的呼吸科醫生王婷,在2020年2月1日晚10點45分,接到醫院同樣的出征任務:次日一早隨山西第二批援鄂醫療隊出發,支援湖北抗擊新冠疫情!
彼時,王婷正在發熱門診值夜班。之前因為接觸患者的不確定性,她已經幾天沒敢回家了。
等待接替值班醫生的過程中,爸爸的電話來了:“我們已經聽說你要去湖北了,媽媽在給你收拾東西,回來拿吧。”
掛斷爸爸的電話,王婷的淚水忍不住了。她說不清,自己此刻的淚水是激動,還是擔心,就那么洶涌而出了。
這一天,她是有準備的。院內第一次報名時,因為看微信群消息晚了一陣,她錯過了。第二次,她早早遞出申請,“當年,爸爸參加了抗擊‘非典,現在輪到我了。”
聽到女兒報了名,王衛國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去吧,你就是學這個專業的。”一如十七年前的他,平靜而執著。
穿起白大褂后,王婷曾無數次想過爸爸當初為什么要如此執著去往那么危險的地方。此刻,她覺得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作為一名醫者,對生命執著守護的職業本能。
王婷是次日一早回到父母家的。媽媽準備好的東西齊整整擺在那里。而爸爸翻騰了好久,從幾個行李箱中挑出一個,拉了過來。
看到那只箱子,王婷當時的喉嚨里涌動著一種東西,她來不及與父母多說話,快速接過箱子。她不知道,爸爸有沒有看出她內心如潮的感動。
出發前,王婷八歲的兒子竟也早早起床了。他知道,媽媽的這次出差與一種病毒有關。于是,在媽媽出門的一瞬,他硬是把一只口罩塞進了媽媽手里。
王婷所在的呼吸科,與重癥、感染、ICU等科室一樣,都是治療新冠肺炎患者的對口科室,“因此,我不能缺席啊,也不想給自己留遺憾。”王婷坦言,她覺得,就像沒有經過戰爭就不能叫真正的戰士一樣,如果沒有與特殊的對手做過較量,那她行醫的生涯就會顯得不夠圓滿。
然而,她畢竟只有三十六歲。這樣突然而至的兇險疫情,還是第一次遇到。如何應對,她沒有概念。因此接到通知的那個夜里,她幾乎沒合眼,除了“支援湖北”,腦中一片空白。她不知道第二天將去往湖北哪里,不知道將被派往哪一所醫院,不知道病毒有多厲害,不知道患者又有怎樣的癥狀。
她在忐忑中充滿渴望與期待。
隊伍集合完畢,馬上就要出征了,王婷在送行的隊伍中看到了爸爸。
爸爸走過來,給了王婷一個長長的擁抱。王婷的眼淚“唰”的就出來了,眼前出現了十七年前坐在輪椅上的為爸爸送行的奶奶。
淚水模糊中,一股力量升騰在王婷胸中。
2月2號16點10分,王婷一行到達武漢天河國際機場。
“偌大的天河機場,空空蕩蕩。心情是說不出的復雜,甚至有一些悲涼。” 王婷一直強調,一個九省通衢的大都市,那種空寂讓人無所適從。依舊是沒有目標的行進,她緊緊跟著隊伍前行。她知道,形勢嚴峻,任務艱巨。
武漢晴川假日酒店門前,大巴停了下來。司機師傅告訴他們,這就是他們在武漢的“家”。還告訴他們,這個酒店是武漢市的標志性建筑,附近就是大名鼎鼎的晴川閣。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這美好的漢陽景致,此刻也一定寂寞靜守在這座被按下暫停鍵的城市里。
一切安頓好之后,王婷得到通知,她的工作地點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
那一刻,她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正身處最嚴重的疫區。
“不知道穿了防護服是什么感覺,不知道醫院環境怎樣,不知道面對什么患者,不知道他們的病情如何。”手機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紛亂信息,而真正的現實中又是什么樣子?她能應對嗎?
一個無眠之夜后,是短暫卻嚴格的培訓。
病區,就在前方。
“洗手,手消毒,戴一層帽子,戴防護口罩;手消毒,戴第二層帽子,穿隔離衣,第一層手套,第一層鞋套;穿防護服,第二層鞋套,第二層口罩,戴護目鏡,戴面屏,第二層手套。”整整十五個步驟下來,居然需要用時五十分鐘。
“加油王婷!山西和濟王婷!”同事們用粗粗的筆,互相將名字與鼓勵語寫在防護服上。
“腳步很沉重,動作很緩慢。”一步一步走向隔離區、污染區,王婷的心咚咚跳著,“不緊張是騙人的,畢竟是人生第一次。”
“一共五十張床位,要陸續接收五十位危重癥患者。”當王婷走進病房,見到患者,反倒平靜下來,“還是平時的工作嘛,只是多穿了一層防護服。”
問病史,查體,對患者院外胸部CT、化驗單、檢查單進行拍照,上傳。一個一個,一步一步。一口氣,王婷完成了首日安排給她的十個病人的檢查與治療工作。
“好累呀,口干舌燥的,真的好累好累。”那時候,王婷真想坐一坐,哪怕靠一靠。可是,不行啊,身上的防護服不允許她像平時出診時一樣隨意。稍有不慎,就會是大隱患,不僅自己有風險,隊友也有風險。
看著身邊一個個忙碌的同事,她努力告訴自己,要堅持。她用所有的空檔,認真觀察每一位患者。她知道其中有很多人剛剛經歷了失去親人的痛苦,他們不僅需要身體上的治療,更需要心理上的撫慰。
她知道,一句話,一個眼神,都是安慰劑。
第一天工作整整十個小時,回到酒店王婷才想起,早飯后就沒再吃過任何東西。
面對收治的五十名危重癥患者,每次查房,醫生們都盡力做到全部問詢了解一遍。“聽起來似乎像假話,但防護服穿脫一遍真是不容易,萬一被漏掉的那個患者恰好出了問題怎么辦?再進去一次不僅需要時間,防護服也要浪費一套啊。”王婷這樣解釋。
很快,王婷學會了武漢人的稱呼,“婆婆,今天感覺如何,胃口怎么樣?”
沒想到有一天,一位婆婆竟然向王婷訴起苦來,“你們給的飯菜不好吃啊!”
“婆婆,都知道眾口難調嘛,如果哪天覺得不適合口味,就多喝點奶,吃點雞蛋。”
“你們覺得好吃嗎?”
“好吃啊!”
“你們從山西來,能吃慣嗎?”
“婆婆,慢慢就習慣了。”
“你們和我們吃的一樣嗎?”
“一樣啊婆婆,咱們都是一鍋出來的,都是一個廚師。”
一句一句,婆婆追著她問,她耐心做著解答。當聽到醫護人員吃的飯與患者一樣時,婆婆不再說什么。
“說實話,那么多人的大鍋飯,能有多好吃呢?”王婷說得有些激動,“但飯菜都是國家免費提供的,能看出來每頓做得很用心,盡量做到了葷素搭配。特殊時期,已經很不容易了。”
回身,她一句句耐心給患者做解釋,告訴大家,國家在全力以赴關心他們,全國人民在想方設法幫助他們,所有的人都是一個心愿,就是希望他們盡快好起來。作為患者,最關鍵最緊要的,就是克服困難,好好配合。
王婷一番話,讓婆婆連連點頭,“行行行,好孩子!”
王婷承認,盡管偶爾有患者這樣發發牢騷,但大部分人都非常感恩,他們會含著淚一遍遍說,“你們大老遠從山西來,你們都是好人,非常非常感謝!”
王婷忘不了第一次進病區時,一位六十九歲的婆婆因為隔離治療見不到家人,心情非常緊張壓抑,又因為連續發燒、腹瀉,情緒極差。后來,干脆不吃不喝,甚至拒絕輸液。看到這種情況,王婷和同事們對她好言安慰,給她細細分析病情,一項項給她講解那些指標,告訴她只要配合治療,恢復很有希望。婆婆沒有想到,這些遠道而來的醫護人員如此耐心,又如此細心,她的情緒很快穩定下來,一反常態對她們說了很多話。王婷說,很多話她都聽不懂,但從言語表情看,都是感謝。
“有了他們的認可與鼓勵,還要求什么呢?”說到這些溫暖的事,王婷忍不住哽咽了,“那個時候,就覺得心里暖暖的,這一趟沒白來。”
“以后再遇到難關,哪怕科室只出一個人,我依然會奮力爭取!”說到這里,王婷的淚水再一次涌出眼眶。或許,這就是她當初“特別想來”的原因吧。在武漢的每一天,她是在戰斗,更是在成長。
“援鄂一個月,流淚太多,感動,真的感動。我愛我的祖國,我熱愛中國共產黨,今生有幸生于華夏!加油武漢,你是我唯一用生命捍衛過的城市!”電話里,王婷說得有些語無倫次,卻鏗鏘有力。
在武漢的兩個多月時間,王婷常常感受到孤獨,也曾惶恐,但只要看到身邊靜靜立著的爸爸十七年前用過的那只行李箱,就一下踏實了。她知道,那是爸爸無聲的祝福,也是送給她的“平安符”,“當年,爸爸帶著它平平安安回家了,我也一定會戰勝疫情,平平安安回去的!”
這就是王婷一家三代醫務工作者的傳奇故事。
責任編輯 高 璟
作者簡介:
蔣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冶金作協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人民文學》等國內大型文學刊物發表作品若干。著有散文集《陽光下的蜀葵》《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天使的模樣》等。曾獲“趙樹理文學獎”及《小說選刊》年度大獎。有多篇散文收入各類年度選本及排行榜。散文《故鄉的秋夜》被收入2014年蘇教版高中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