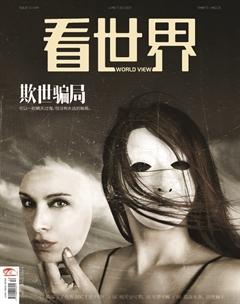戰機可否擊落“不聽話”客機
錢克錦

一架從希臘飛往立陶宛的愛爾蘭客機,5 月下旬經過白俄羅斯領空時被迫降。白方理由是獲悉機上有炸彈,但經過一番檢查,白方沒有發現炸彈,倒是逮捕了乘坐這架航班的一名白俄羅斯著名反對派記者。
歐美多國對此反應激烈,認定這是一起“國家劫機”行為。特別是白俄羅斯的戰斗機升空逼迫,令人更往深處想:如果客機當時不聽“勸告”,或者溝通有誤,會不會有更嚴重的后果?
對于這個問題,答案不簡單,因為現實很復雜。
1944 年簽訂的《國際民航公約》(因在芝加哥簽訂,一般稱《芝加哥公約》)規定,各國必須抑制對飛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如果進行攔截,必須不危及航班人員生命。后來聯合國安理會的一些決議,也強調維護航班乘客的生命安全。
但在國家主權面前,國際法的約束力和執行力往往很弱。過去幾十年,不要說逼停民航班機,就是擊落班機也不罕見。據不完全統計,造成比較大的影響的有:
1955 年,以色列一架民航飛機誤入保加利亞領空,被保國空軍的兩架米格-15 戰斗機擊落;1973 年,一架利比亞客機因突遇大沙暴、導航儀失靈偏離航道,誤入當時被以色列占領的西奈半島上空,以色列戰機升空攔截、開火警告,擊中機翼,客機墜毀,機上113 人中,108 人死亡;1978 年,一架韓國客機因導航系統出問題偏離航線,進入蘇聯領空,蘇聯戰機升空警告開火,擊中機翼,飛機迫降,導致兩名乘客死亡。
后果最嚴重的是在1983年9月,載有269名乘客的一架韓國客機偏離航線,進入蘇聯領空。蘇聯空軍誤以為是偵察機,在聯絡未果、警告無效后,派戰機發射導彈。客機中彈后墜落公海,無人幸存。因為機上乘客來自十幾個國家和地區,此事件引發嚴重外交糾紛。后來的調查表明,客機雖然的確未經許可進入了蘇聯領空,但蘇聯也過度使用了武力。
如果說這些悲劇都還有個起碼的是非判定,那么2001 年的“9·11”恐怖襲擊,則讓“戰機是否有權擊落不聽話客機”這個問題更顯復雜。
抽象而言,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滿載油料的客機,已經不再是民用交通工具,而是一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果一架情況不明、“聯絡未果”的客機偏離計劃路線,飛向類似于世貿大廈或白宮的大廈,又或是飛往人口密集地區、有危險品的工業區、大壩,此時警覺的戰斗機是否有權擊落它呢?
實際上,“9·11”事件中被劫持的聯合航空93號航班,幾乎就讓美國軍方作出類似的抉擇。由于93 號航班延誤起飛,在其遭劫持并飛往華盛頓特區的途中(后來調查顯示,它的目標是美國國會大廈),其他兩架被劫持的航班已經撞了世貿大廈,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次劫機的嚴重性。
一架F-16 戰斗機奉命升空攔截93號航班。因為匆忙,戰機沒有時間裝備導彈,當時飛行員下了決心,做好了在迫不得已情況下用戰機撞毀93號航班的準備。不過93號航班上的乘客在空中獲知恐襲事件后,和劫機恐怖分子搏斗,最后客機墜毀在賓州的野外。幾年后有美國媒體分析,這倒避免了讓戰機的飛行員作出“不可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