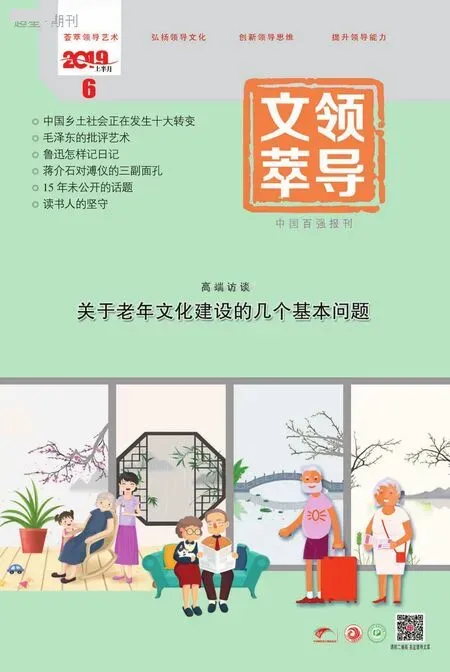墨子:一個(gè)時(shí)代的光彩開端
劉勃

出身“賤人”
《史記》寫孔子,有《孔子世家》,相當(dāng)詳細(xì)地介紹了孔子一生。關(guān)于墨子,則只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后面,附了這么一句話:“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jié)用。或曰并孔子時(shí),或曰在其后。”墨子的主張,司馬遷只介紹了六個(gè)字,“善守御,為節(jié)用”,沒有大家最熟悉的兼愛。
墨子出身大約比較卑微。說到孔子,有關(guān)于孔子祖上有多高貴的傳說,墨子的祖宗是誰,卻向來無人提起,可見沒什么可夸耀的地方。《墨子·貴義》中有這么一個(gè)故事:墨子到楚國去,游說楚惠王。楚惠王表示自己年紀(jì)大了,不能實(shí)行墨子的主張。這當(dāng)然是婉拒的客氣話,后來楚惠王派了穆賀見墨子,倒是說了實(shí)情:您的見解誠然很高明,但我們楚王是“天下之大王”,恐怕會(huì)認(rèn)為您的主張是“賤人之所為”,所以不能實(shí)行。墨子當(dāng)然不服,回應(yīng)說∶聽取建議的時(shí)候,只看是否可行罷了。譬如服藥,一把草根如果療效好,天子也是要吃的;農(nóng)民的出產(chǎn),加工成豐盛的祭品,也可以用來祭祀上帝鬼神。可見即使是“賤人”,往高里比可以比作農(nóng)民,往低里比可以比作草藥,難道我還不如一把草根嗎?
從這段對話看,楚惠王和穆賀都把墨子看作“賤人”,墨子也承認(rèn)自己是“賤人”。賤是社會(huì)地位低下的意思。結(jié)合墨子“一草之本” 的比喻,倒真應(yīng)了今天的說法,他是草根階層。
崩壞的時(shí)代
墨子生活的時(shí)代,史料殘缺特別嚴(yán)重。但可以做個(gè)大致的判斷:墨子這輩子,見識了許多大新聞。戰(zhàn)爭與動(dòng)亂,構(gòu)成了墨子青少年時(shí)代很重要的記憶。有學(xué)者概括說,儒家代表士階級的上層,墨家代表士階級的下層,這是極有眼光的看法。
以儒者的身份,排隊(duì)等官做,墨子等到公元后恐怕也輪不到;墨子選擇了自己做領(lǐng)袖,把大批下層士人乃至庶人團(tuán)結(jié)起來,形成一個(gè)有組織有紀(jì)律,擁有強(qiáng)大的行動(dòng)力甚至武裝力量的社會(huì)集團(tuán),這就可以直接引起各國國君和大貴族的重視了。應(yīng)該怎樣游說國君,墨子精心做了預(yù)案。《墨子·魯問》講到:
墨子到列國游歷,魏越問他:“見到四方的君主,您會(huì)優(yōu)先提什么建議呢?”墨子說:“我會(huì)根據(jù)這個(gè)國家具體情況,指出他的當(dāng)務(wù)之急:國家昏亂,就告訴他們尚賢、尚同;國家貧窮,就告訴他們節(jié)用、節(jié)葬;國家喜好聲樂,沉湎于酒,就告訴他們非樂、非命;國家荒淫、邪惡、無禮,就告訴他們尊天、事鬼;國家喜歡掠奪、侵略、凌辱別國,就告訴他們兼愛、非攻。”
顯然,這是墨子最重要的思想,往往也被稱為墨家的“十大主張”。墨子說:仁德的人的工作,就是為普天下的人謀福利,為普天下的人除禍患。這應(yīng)該被看作是普世的,對人民有利的就實(shí)行,對人民不利的就停止。那么,墨子對利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民眾的最基本的物質(zhì)生活。可能損害到這一點(diǎn)的事,都不要去做。具體說,以下這些追求都是不值得的。
世間不值得
不值得之一,是物質(zhì)享受。統(tǒng)治者一追求物質(zhì)享受,人民負(fù)擔(dān)就會(huì)加重,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情。《辭過》等篇, 都批判這個(gè)問題。“辭過”是告別過錯(cuò)的意思。里面講了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個(gè)問題。他所謂的“利人”,訴求是人作為 “物”的價(jià)值要被重視,而不是人作為“人” 的尊嚴(yán)要被尊重。
不值得之二,是死后世界。厚葬久喪的問題,也是儒家和墨家爭論的焦點(diǎn)之一。儒家理論也是反對厚葬的,但和墨家主張的節(jié)葬是兩個(gè)概念。儒家的反厚葬, 是說每個(gè)社會(huì)等級都有相應(yīng)的喪葬標(biāo)準(zhǔn),等級高標(biāo)準(zhǔn)也高,等級低標(biāo)準(zhǔn)也低,不應(yīng)該超過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墨家主張的節(jié)葬,按照古人的觀點(diǎn),卻真是儉薄到極點(diǎn)了 :衣服三件, 棺木三寸厚。死者既已埋葬,活著的人就不要長久地服喪哀悼。
不值得之三,是文化娛樂。墨子所謂“非樂”,樂是音樂的意思,也是快樂的意思。非樂是不聽音樂,也是不要娛樂。對音樂的態(tài)度,是墨家和儒家爭論的另一個(gè)焦點(diǎn)。儒家對音樂極重視,有學(xué)者甚至認(rèn)為,從文化淵源上說,儒家就出自西周的樂官。《史記·樂書》說:音樂,從個(gè)人修養(yǎng)說, 可以培養(yǎng)你的正義感 ;從調(diào)整社會(huì)關(guān)系說,可以區(qū)別人的等級。
墨子反對音樂,照例還是從成本-收益著眼:鑄造樂器很花錢,演奏樂曲要用人,欣賞音樂要花費(fèi)時(shí)間。總之,為了聽音樂,不知道浪費(fèi)了多少人力物力。
不值得之四,是科學(xué)探索。《墨子》書里,和工程技術(shù)有關(guān)的內(nèi)容是不少的,也有些觀察自然界的發(fā)現(xiàn)。但科學(xué)和技術(shù)是兩回事。技術(shù)強(qiáng)調(diào)有用,能解決具體的問題;科學(xué)在于求真,關(guān)心物質(zhì)世界的規(guī)律和本質(zhì),是否有用,往往暫時(shí)不在考慮范圍之內(nèi)。而墨子是特別關(guān)心有用的。
世上的不值得,當(dāng)然不僅以上這些,但結(jié)合上面內(nèi)容,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出墨子的基本邏輯:他關(guān)心的一是吃飽穿暖,二是增強(qiáng)國防。舍此而外,一切追求都是多余的。
在戰(zhàn)國時(shí)代,墨家的學(xué)說深受歡迎,以至于孟子要感嘆“楊墨之言盈天下”,韓非子要說儒家和墨家是“世之顯學(xué)”。
而墨家組織,也取得極為快速的發(fā)展。也正是因?yàn)榻M織的力量,墨家才有了倡導(dǎo)“非攻”的底氣。
墨家的非攻
反對戰(zhàn)爭的立場,中國比西方可是鮮明多了,這簡直可說是中國文化的基調(diào)——當(dāng)然,這也不影響中國這片土地上,有頻繁而殘酷的戰(zhàn)爭。
所以,墨家“非攻”這個(gè)主張,本身并不算很有特色。那么,為什么只有墨家的非攻,最令人印象深刻呢?
《墨子·公輸》講了墨子救宋的故事,敘述很有民間故事的風(fēng)味,也許更適合當(dāng)寓言而不是事實(shí)看待。但作為一個(gè)寓言,它確實(shí)信息量很大,內(nèi)涵也很豐富。三篇《非攻》的主要觀點(diǎn),都包含在這個(gè)故事里了。
墨子救宋的第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是去勸阻公輸般,兩個(gè)人討論的核心,是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是否正義的問題。
墨子采用的辦法,是先請公輸般殺一個(gè)人,公輸般拒絕后,就提醒他:“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這里墨子指出了一個(gè)問題:即使是不愿意做小壞事的人,可能做大壞事卻不覺得有什么道德障礙。很重要的一個(gè)原因是距離感:對公輸般而言,親手殺一個(gè)人,那種罪惡的感覺是直擊內(nèi)心的;但你發(fā)明了武器在前線殺死很多人, 你也要負(fù)責(zé)任,卻需要墨子提醒,公輸般才無法回避。
墨子向公輸般強(qiáng)調(diào)的另一個(gè)要點(diǎn)是:宋國是沒有罪的,所以楚國攻打宋國不正義。
在另外一些辯論中,墨子對戰(zhàn)爭的性質(zhì)作了區(qū)分:邪惡的戰(zhàn)爭叫作“攻”,正義的戰(zhàn)爭叫作“誅”,如商湯伐桀,周武王伐紂,都是“誅”。墨子只反對攻,不反對誅。
有人對墨子這種態(tài)度是盛贊的,認(rèn)為他最早區(qū)分正義的戰(zhàn)爭和不正義的戰(zhàn)爭,是一大貢獻(xiàn)。其實(shí),一來墨子肯定不是最早做這種區(qū)分的人,看《左傳》里的記錄,各國圍繞著戰(zhàn)爭所做的各種外交爭論和宣傳,就知道戰(zhàn)爭正義不正義,他們腦子里都是有清晰標(biāo)準(zhǔn)的;二來,支持正義的戰(zhàn)爭,對人的心態(tài)所發(fā)生的影響,是好是壞也很難說。
這一層,莊子看得比墨子透徹,他說:“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為了追求正義而想消除戰(zhàn)爭,才是戰(zhàn)爭的根源。
(摘自《作家文摘》)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