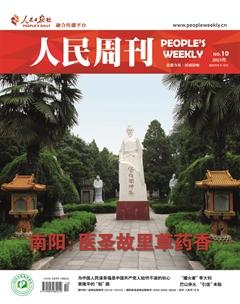多城加速跑 角逐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鄭新鈺
在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我國線上線下消費亮點紛呈。短期來看,假日經濟加之全國消費促進月活動的啟動,使得經濟發展呈現火熱態勢;長期來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培育將成為我國經濟穩定向好的重要支撐。
引人關注的是,就在“五一”假期前幾天,江蘇省南京市、浙江省杭州市相繼發布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三年行動計劃;北京市發布五年實施方案;上海市、廣東省深圳市則提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若干措施;廣東省廣州市召開構建世界一流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圓桌會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所擔負的時代使命,在新發展格局下,它要擔負起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引擎的重要責任。
六大任務將成為“必修課”
今年初,商務部部署2021年促消費任務,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是“加快推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建設”。對比以往政策文件中關于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提法,“加快”二字既是一種發展態勢,也是一種競進過程。
事實上,這項工作與“十三五”以來國家推動消費升級與創新等相關要求一脈相承。
2019年10月,商務部等14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競賽鳴了槍。
《指導意見》提出,利用5年左右時間,指導基礎條件好、消費潛力大、國際化水平較高、地方意愿強的城市開展培育建設,基本形成若干立足國內、輻射周邊、面向世界的具有全球影響力、吸引力的綜合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帶動形成一批專業化、特色化、區域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認為,眼下社會各界在討論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時,更多強調“消費”,但對“國際”和“中心”的討論較少。
“國際消費中心與消費國際化有所不同。”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醒,并不是打造一條全部售賣國外商品的街區,再吸引一些外國人來,就能稱之為國際消費中心,“我們應該要形成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外國友人和國人既是消費品的提供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并且,這個消費不僅僅局限于商品消費,還有服務消費。”
此外,白明認為,“中心城市”意味著具有排他性。
“中心城市需要在相關區域有一定的聚集力,多了就不是中心城市了。”白明指出。
那么,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具體應該如何建設?
按照《指導意見》的思路,聚集優質消費資源、建設新型消費商圈、推動消費融合創新、打造消費時尚風向標、加強消費環境建設、完善消費促進機制等六大任務,將成為候選城市的“必修課”。
具體來說,包括發展品牌經濟,吸引國內外知名品牌新品首發;重點開展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促進傳統百貨店、大型體育場館、閑置工業廠區向消費體驗中心、休閑娛樂中心、文化時尚中心等新型發展載體轉變;培育發展一批博覽會、購物節、時尚周、消費展等國際產品和服務消費新平臺;新建和改造社區便民服務中心和街區生活服務集聚中心等。
“我國最終預計有2至3個比肩世界一流的綜合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以及6至8個區域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王微認為。
GDP十強城市均提出建設目標試點城市名單公布進程加快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我國已有20余個城市提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推動消費升級,其中既有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也有杭州、南京、重慶、成都等新一線城市,以及沈陽、太原等二三線城市的身影。
記者梳理后發現,從2021年地方兩會披露的經濟成績單來看,GDP十強城市均提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將成為一個新‘標簽,即除GDP規模之外,有望成為中國城市繁榮度與全球吸引力的評價標準。”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果如是說。
從區域角度來看,目前長三角地區積極性最高。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寧波、蘇州、無錫七座城市加入競賽,可以說,長三角的“精銳”基本投身其中。
從2020年消費數據來看,上海市以1.59萬億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位居全國第一,優勢遙遙領先,北京市和重慶市緊隨其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突破1萬億元。
從國際經驗來看,可以發現國際性消費城市共同的特征皆是經濟體量在一國之中占比較高的城市。
不過,王微提醒,并不是所有的大型城市都有可能成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目前,我國各地積極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但對比國際中心城市仍有提高空間。特別是新興服務業的標準體系建設還略有滯后,以及與消費直接相關的新興服務行業對外開放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王微表示,近期商務部會加快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試點城市的選擇。
對標國際和突出特色改善硬環境、提升軟環境
細看各地實踐路徑,提升步行街區及商圈品質、開展購物消費節、打造多元化消費場景等成為不約而同的舉措。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建設過程中,突出特色是應有之義。
“在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出特色,避免千篇一律。”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稱,根據自身獨特的優勢形成獨特消費環境,實現差異化消費體驗,才能提高對全球消費者的吸引力。
具體實施方面,趙萍認為,一方面城市要做到目標差異化,即充分考慮本地綜合實力,確定創建目標是區域性還是全球性;另一方面,依托本地優質消費資源,形成獨特的商品和品牌供給能力,特別是要增加特色產業、知名品牌、獨特的文化資源等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吸引國內外知名品牌新品首發,加快培育和發展服務消費產業。
不過,找到特色、錯位發展絕非易事,每個城市都在實踐中尋找著自己的答案。
記者注意到,杭州市表示,將利用自身優勢,打造直播電商發展高地、新零售示范支撐、數字生活新服務標桿城市;近期公布的《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也為南京爭創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注入強勁動力;廣州市在2020年的汽車產量全國第一,因此提出大力促進汽車消費,推動汽車平行進口、二手車出口創新發展;成都市三年來一直在積極打造“現代商貿產業生態圈”,意在匯聚全球資源、引導集群成鏈、創新要素配置、推進產城一體,鞏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產業支撐……
此外,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提醒,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不僅需要硬環境的提升,更需要軟環境的建設。
記者注意到,《指導意見》提出,圍繞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從原則角度要“把握我國主要城市在消費領域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破除體制機制障礙”。
“從我國來看,日常消費品市場隨著發展日漸飽和,消費面臨突出短板集中在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陸銘說,“這些通常在購物節中是沒有的,也存在一定供給制約。”
(《中國城市報》202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