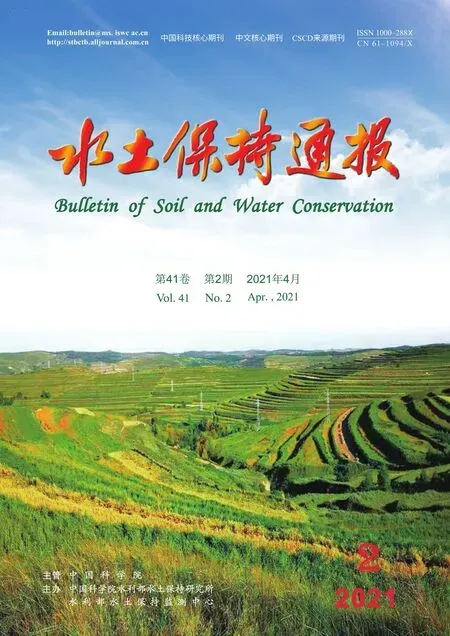城市濕地公園建設的生態效應
——以濟西國家濕地公園為例
楊 霄, 劉 森, 賈 超, 劉 揚, 于翠翠, 朱恒華
(1.山東大學 海洋研究院, 山東 青島 266237; 2.山東省地質測繪院,山東 濟南 250002; 3.山東省地質調查院, 山東 濟南 250014)
天然濕地系統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類提供了持續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但天然濕地的數量有限,且主要分布于城市周邊區域,城市濕地生態系統的建設成為建設生態城市的重要因素[1-2]。經精心規劃、設計、建設和運營的城市濕地生態系統具備與自然濕地相似的生態功能,例如凈水、固碳、泄洪、防止土壤流失和蓄水等[3-4]。城市濕地公園作為人工濕地或自然濕地的集合,能夠為野生動物提供棲息地,同時在美化環境、旅游觀光和科普教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實現了資源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平衡[5-6]。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在《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發〔2015〕25號)明確提出,“樹立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統籌考慮自然生態各要素進行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增強生態系統循環能力,維護生態平衡”的要求。在這樣的環境下,城市濕地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國內外眾多學者對城市濕地進行了研究,如徐燁等利用“壓力—狀態—響應”模型建立了雄安城市濕地生態系統的健康評價指標體系,討論了濕地公園內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7];萬媛媛等采用樣方法和組平均法對天津臨港城市濕地的植物群落進行了調查和聚類,分析了城市濕地物種的多樣性格局[8]。以上研究對城市濕地公園建成后的生態情況進行了分析,肯定了濕地公園良好的生態作用。但關于城市濕地形成前后生態效應的定量化分析研究卻略顯不足。由于可參考借鑒的研究較少,大部分濕地公園保護工作尚未形成體系。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造、耕地的種植等強烈的人為活動,產生了一系列的生態問題[9-11]。因此,定量分析城市濕地形成前后的生態效應對于響應生態保護的部署和科學規劃城市濕地公園具有重要的作用。
濟西國家濕地公園(以下簡稱“濟西濕地”)是濟南市最大的城市濕地[12],由于2001年玉清湖水庫建成后的側滲以及周圍特殊的水文和地形條件造成的區域性匯水而成為常年性濕地。本文以濟西濕地為研究區,通過搜集和調查等方法獲取水文地質、DEM、遙感影像等基礎數據,選取1990—2019年遙感影像數據對土地利用類型進行分類;分析1990年以來濕地土地利用類型、景觀指數、水文氣候、動植物的演變特征;結合水文氣候和建設活動資料,對其驅動機制進行探討,系統給出濟西濕地景觀格局和演變特征及其主要驅動因素。研究成果能夠為類似濕地的保護和濕地公園內生態環境的發展建設提供科學依據和理論指導。
1 研究區概況
濟西濕地位于濟南市中心城區的西部,地理坐標范圍為116°45—116°50′E,36°37′—36°41′N,西部緊靠黃河干流,北面有黃河下游最大支流玉符河穿過,東側為南水北調東線引渠,濕地內有玉清湖水庫水源地,區域內水資源豐富,面積約33.6 km2[13-14]。濟西濕地地貌單元屬于玉符河沖洪積扇,地貌類型單一。研究區土壤為潮土,土層深厚,土體發育完全,呈中性至微堿性。耕層質地多為中、輕壤,保水保肥易耕作。年均降水量698.6 mm,變化范圍312~1 051 mm;年均蒸發量2 257.6 mm,變化范圍1 912~2 315 mm。年均氣溫13.4 ℃,變化范圍12.8~14.3 ℃,年變化以7月最熱為27.3 ℃,1月份最冷為-2.7 ℃;平均無霜期198 d;年平均日照總時數為2 640.2 h。濟西濕地水資源補給包括大氣降水、玉符河水、玉清湖側滲水及引進的黃河水。地下水流總體由東南向西北徑流,由于懸黃河的天然分水嶺作用,近河以側滲補給為主,遠河以降水入滲為主,并輔以少量的灌溉回滲,地下水排泄以蒸發和人工開采為主。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的選擇與處理
使用的數據主要包括: ①濟西濕地1990,1998,2000,2004,2008,2012,2018和2019年共計8期Landsat影像,遙感影像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土地利用數據由支持向量機(SVM)使用Landsat圖像提取[15]。 ②DEM數據,DEM影像采取無人機實地勘測與影像結合校正,利用ENVI 5.4專業遙感圖像處理軟件,對遙感數據進行輻射定標、大氣校正、鑲嵌、波段組合、增強等處理,編制遙感影像圖。 ③水文氣象數據,研究資料來源于山東省地質測繪院在濟西濕地附近的長期水文觀測站和地下水水位觀測井。選取氣溫和降水資料,計算出其年平均值的時間序列,采用線性傾向趨勢估計統計分析方法,對自1990年來的濟南氣候變化趨勢進行研究。
對獲得的不同時期的Landsat OLI圖像應用最大似然監督分類和視覺解釋技術[16-17],配合濕地實地調查,將土地利用類型細分為16種(6大類):草地、耕地、林地、沼澤林地、人工表面(壩體、工業用地、公路用地、火車站、建設用地、農村建設用地、鐵路用地)、水域(水庫水面、水面、河流水面、坑塘水面、養殖水面)。本次研究中,我們收集了100多個樣本作為訓練數據,這些樣本已在最大似然分類器中用于執行分類,總體分類準確度大于95%。
2.2 土地利用動態度
本次土地利用變化的速度采用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和空間動態度來定量描述。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是特定土地利用類型在給定時間段內的變化率,而空間動態度是不同土地利用類型轉入轉出的變化率[18-19],其表達式分別為:
(1)
(2)
式中:K,K′表示研究時段內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和土地利用變化空間動態度;Sa,Sb分別表示研究時段始末期某一種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km2);Sin,Sout分別表示研究時段某一種土地利用類型轉入和轉出的面積(km2);T為時間段(a)。
2.3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與景觀指數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來源于系統分析,能夠反映研究期內土地利用的結構特征和各類型之間的轉化情況和方向,提供了詳細的“轉入”和“轉出”信息,是比較不同來源地圖的最常用方法[20]。使用下列公式進行計算:
(3)
景觀指數可以描述景觀格局的復雜性和變化[21]。本次研究利用ArcGIS平臺和Fragstats軟件,計算了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蔓延度指數(CONTAG)和香農多樣性指數(SHDI)。其中,CONTAG描述的是景觀不同斑塊的聚集性程度或延展趨勢。SHDI反映了景觀元素的數量及其比例的變化,其值越大,多樣性越高[22]。
2.4 碳匯潛力
固碳是濕地提供的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在地球大氣輻射平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近年來在氣候情景中最受關注的濕地功能。濕地植被的碳儲量是其現有生物量中存儲的碳[23],水文地貌和植被的類型以及景觀位置都會影響區域的碳匯能力,在水資源豐富的濕地地區,其土壤肥沃,更有利于刺激濕地植物的生長。
碳儲量計算公式為:
(4)
式中:i表示不同植被類型;Ai為不同植被類型種植面積(m2);Ci為不同植被區域類型下的碳密度[24-26](kg/m2)(表1);Cs為濕地區域內總碳儲量(kg)。

表1 各類型植被碳密度數據 kg/m2
2.5 關聯度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是一種識別和確定關鍵因素優先級的改進方法,適用于變量獨立性分析。根據灰色關聯度理論分析了濕地與驅動因子之間的相關性。由于每個序列中因子的維數不同,無法對不同序列進行比較。因此,為了確保結果的可靠性,使用等式(5)對參考序列和比較序列進行了無量綱處理。無量綱處理后,計算關聯系數和灰色關聯度[27]。
(5)
ζk(k)=
(6)
(7)
式中:Xi(k)為原始數據;xi(k)為無量綱處理后的數據;ζi(k)為灰色相關系數;γi為灰色關聯度;ρ為分辨系數,0<ρ<1 ,通常取0.5。i=0,1,2,…,n;k=1,2,…,m。
3 結果與討論
3.1 濟西濕地的演變
3.1.1 土地利用類型的演變
(1) 土地利用動態度。自1990年以來,在氣象、水文、地質地貌、植被、土壤、地下水、人類工程活動、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下,濟西濕地土地利用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圖1)。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主要分4個階段(表2),分別為水庫建設前的變化期(1990—1998年)、水庫建設期間的穩定期(1998—2000年)、濕地初步形成期(2000—2004年)以及濕地快速發展期(2004—2019年)。1990—1998年期間,濟西濕地單一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速度最快的是公路用地(38.78%),其空間動態度達到155.12%,城市化道路發展極為迅速。1998—2000年為水庫建設期,受政府的控制和影響,在此時間段內土地利用類型保持不變。2000—2004年,坑塘成為增加速度最快的土地利用類型(71.46%),但空間動態度最大的是建設用地(166.78%)。2004—2019年,年變化率最快(26.33%)和空間動態度(36.12%)最大的均為草地。

表2 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K)和土地利用變化空間動態度(K′) %

圖1 濟西1990-2019年濕地土地利用類型
(2)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在濕地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的是土地利用類型是生態用地,由于耕地對于濕地內動植物生長的貢獻有限,本研究將林地、草地、沼澤林地和水域視為主要的生態用地[28]同時由于1998—2000年的土地利用類型保持不變,重點分析了1990—1998年、2000—2004年、2004—2019年土地利用轉換矩陣(表3)。1990—1998年,自然狀態下的生態用地增加緩慢(5.58%),耕地(11.79%)主要轉化為人工表面用地。2000—2004年,生態用地的轉入比例迅速增加(66.04%),這主要得益于玉清湖的建成,此時濕地初步形成。2004—2019年,生態用地轉入的占比仍然很大(47.91%),濕地不斷發展。總體來看,耕地與生態用地之間的相互轉換是主要的土地利用變化類型,建設用地與生態用地之間的相互轉換是次要的土地利用變化類型。焉恒琦等[29]在研究多個濕地的人為脅迫性也指明,耕地和人工表面是人工干預引起濕地內部變化的主要類型,對濕地生態系統有很大的影響。

表3 濟西濕地1990-2019年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hm2
3.1.2 植被覆蓋類型及碳匯情況的演變 土地利用是人類對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使用狀況,而土地覆蓋(植被覆蓋)主要表達的是土地表層以植被為主要覆蓋物的自然類型和狀態。濟西濕地目前植被覆蓋類型主要有4種,分別為草地、耕地、林地、沼澤林地(圖2)。整體來看,1990—2019年濟西濕地植被覆蓋類型變化主要表現為耕地減少,轉變為草地、林地和沼澤林地。其中耕地減少了45.20%,林地增加了13.64%,沼澤林地增加了11.78%、草地增加了1.85%。林地和沼澤林地的增加成為濟西濕地演變的主要特征。濕地形成前,區域內耕地面積占比最大,碳儲量也最多。在濕地形成和建設的過程中,由于濟南市“退耕還林還濕”政策的實施,濕地區域內部分耕地改變為林地、草地和沼澤林地等具有高固碳能力的植被類型,較少的生態用地就能夠提供更多的碳儲量,使得濟西濕地的碳匯能力在不斷增強。

圖2 濟西1990-2019年濕地植被類型及碳匯情況變化
3.1.3 景觀指數的變化 濟西濕地內的CONTAG呈下降趨勢,景觀破碎化程度變高,連通性變低(圖3)。而SHDI一直呈現增加的趨勢,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濕地景觀類型的多樣性增加,并有向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發展的趨勢,這是由于人類干擾的增加。此外,CONTAG的減少和SHDI的增加,說明作為主要土地利用類型的耕地逐漸減少,已變得更加零碎,在景觀中的優勢也越來越小,這意味著在濕地公園的建設過程中,“退耕還林還濕”政策得到有效實施。

圖3 濟西1990-2019年濕地景觀指數變化
3.1.4 水文氣候的演變特征
(1) 氣溫演變特征。由圖4可知,濟西濕地形成后的趨勢線比形成前的趨勢線明顯降低,對于局部氣候的調節作用明顯,但由于城市社會的發展,氣溫仍呈現波動上升狀態。年平均氣溫大部分為正距平,最高平均氣溫為15 ℃,出現在2019年,相較歷年平均氣溫高了0.83 ℃;最低氣溫出現在2011年,年均溫為13.4 ℃,相較歷年平均氣溫低了0.77 ℃,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間相差1.6 ℃。根據2000年后的氣溫趨勢線,氣溫將繼續呈現波動上升狀態。該區域的變暖和與玉符河的季節性洪水會使濕地的地表水水源供給不穩定,導致濟西濕地中蒸發量的增加,引起土壤含水量減少和地表水補給減少,不利于城市濕地的自然發展。

圖4 濟西1990-2019年濕地年均氣溫變化和降雨量變化
(2) 降水和地下水水位變化特征。根據濟西濕地年均降雨量變化圖(圖5)和監測孔組逐月的監測資料(圖5),濟西濕地的降水量和地下水水位趨勢基本一致。1993年、1994年連續兩個豐水年后,孔隙水水位上升至近30 a最高水位,此后水位逐漸下降,至2003年枯水期,水位降至最低點。2003年以后,濟西濕地進入連續的豐水年份,降水量較多年平均值多100~150 mm左右,孔隙水水位快速回升,進入相對的高水位期。從孔隙水多年動態曲線可以看出,一場較大的降水,對孔隙水水位的影響十分明顯,如1996,1998,2003,2004,2010,2013和2016年,降水量集中,月內降水量均在300 mm以上,孔隙水水位在短期內迅速回升至當年最高水位或數年最高水位。由于濟西濕地存在較厚的第四系松散沉積物,因此該區域降水量增加可有效增大地下水的補給量,使得地下水水位的變化趨勢呈現出10 a左右的波動周期。

圖5 濟西1991-2019年孔隙水動態與降水量關系曲線
(3) 相關性分析。將濕地面積作為參考序列,而長期監測的降雨、溫度和地下水水位作為比較序列,分析了濕地面積變化和氣象序列相關性。其中,用負值表示負相關,正值表示正相關。由表4可知,3種因子中地下水水位是影響濕地面積的最主要因素。濕地面積與地下水水位、降水量呈正相關,地下水水位和降水量對城市濕地的自然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而氣溫與濕地面積變化之間呈負相關,即隨著區域溫度的升高,濕地的面積減少。由于濕地本身具有冷濕效應,區域溫度升高將降低城市濕地的冷濕作用。鄭慧禎等[30]在研究閩江濕地時也發現了隨著濕地溫度的上升,濕地面積減少,降溫效果減弱。杜培軍等[31]在研究濱海濕地土地利用與地表溫度響應時也有一致的結論。這表明水文氣候因素對城市濕地的影響與天然濕地類似。

表4 濕地面積與驅動因子的灰色關聯度
3.2 演化的驅動力
濕地公園中的自然的水文氣候的變化和外部的人為干擾是影響濟西濕地演變的主要因素。
3.2.1 水文氣候 基于灰色關聯理論,采用長期連續監測的降水數據和氣溫數據分析了水文氣候對濟西濕地的影響。降水和地下水補給作為濕地的重要水源,與濕地面積變化呈正相關。溫度與濕地變化呈負相關。這與Wu等[16]在紅河自然濕地中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表明在不受人為影響的情況下,城市濕地的發展演化同樣受水文氣候因素的控制。因此,水文氣象因素對城市濕地的自然演化起著重要的作用,濕地內的水文循環是城市濕地成為常年性濕地的關鍵。從降水、地下水水位、溫度等氣象條件的演變特征趨勢線分析,景區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降水量和地下水水位呈下降趨勢,氣溫呈上升的趨勢,處于偏暖階段。溫度升高將使地表水蒸發量增加,而隨著蒸發過程的加速和濕地水資源量的減少,會導致濕地面積的喪失。該階段維持時間2~3 a后轉入降雨量增加階段,周而復始的呈波動變化。此外,濟西濕地及臨近區域年均降水量、年均氣溫和地下水水位的特征不存在突變現象,這將對景區植被的生長發育、水分補給更為有利。
3.2.2 人為干擾 當“濟西國家濕地公園”建立時,農業活動受到限制,導致耕地面積大幅減少,這表明農業開墾對濟西濕地的形成有最直接相關性。人為開采大量地下水澆灌農田也會影響區域內水資源的補給,不利于濕地的發展。由于濕地生態系統的高脆弱性,若濕地區域內的林地遭受破壞,耕地增加,則濕地區域內的碳匯能力將極大降低。而水作為濕地的主要景觀和關鍵要素,水量和水質對于濕地的發展極為重要。濕地公園內農田化肥和居民生活用水若未經處理直接排放,會影響著水生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并且由于玉清湖水庫為直引黃河水的水庫,水質情況直接受到黃河水水質的影響。未經處理排放到黃河內的城市工農業用水將加重濕地公園內水質的污染程度。于洋等[13]也在其研究中指出,濟西濕地受到人為因素的強烈干擾,不合理的處置措施將導致濕地不斷減少。李文清[32]和胡乃利等[33]的研究也揭示了城市濕地區域內農藥化肥的使用和土地利用類型的不合理的導致濕地內較嚴重的水質污染和水土流失現象。水庫建設前,該區域未受干擾,植被覆蓋類型只有耕地和林地。玉清湖水庫建設期間,由于政府的規劃和控制,植被覆蓋類型并未發生變化。玉清湖水庫建設后的過渡期,水庫逐漸向外滲水,加上居民對于黃河水和玉符河水的引灌,濕地初步形成。從2004—2019年,由于城市的規劃,強制性和激勵性政策的實施,至2011年濟西濕地被列為國家濕地公園的試點公園后濟西濕地“退耕還林還濕”政策的有效實施,濕地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具體表現為耕地大幅度減少,轉變為林地、草地、沼澤林地等生態用地。
4 結 論
(1) 耕地的減少、林地和沼澤林地的增加是濟西濕地土地利用類型演變的主要特征。耕地與生態用地的相互轉換是主要的土地利用變化類型,建設用地與生態用地的相互轉換是次要的土地利用變化類型。“退耕還林還濕”政策得到有效實施,具有高固碳能力的植被類型的增加使得濟西濕地的碳匯能力不斷增強。景觀指數和動植物的變化表明濕地生態多樣性增加。
(2) 灰色關聯度分析顯示,地下水水位是影響濕地自然演變的主要因素,降雨的影響次之,而氣溫與濕地面積變化呈負相關。水文氣象特征的趨勢線表明現階段呈溫度升高和降水減少趨勢。這些因子的變化過程主導著城市濕地的自然演變,并控制了濕地水文循環的變化,研究區內的水文循環是常年性濕地形成的關鍵。
(3) 土地利用的主次要轉換類型以及人為對碳匯能力的增強表明了城市規劃等人為干擾是城市濕地演變的主導因素,而水文氣象因子則更多影響城市濕地穩定后的自然演變。氣候變暖、水資源量的減少以及地下水水位的降低,都將不利于地表水的儲存。濟西濕地內地表水補給了地下水,減少了地表水的量,增加了濕地的脆弱性。因此,為了保護濕地,必須限制耕地的擴展和人為不合理的施工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