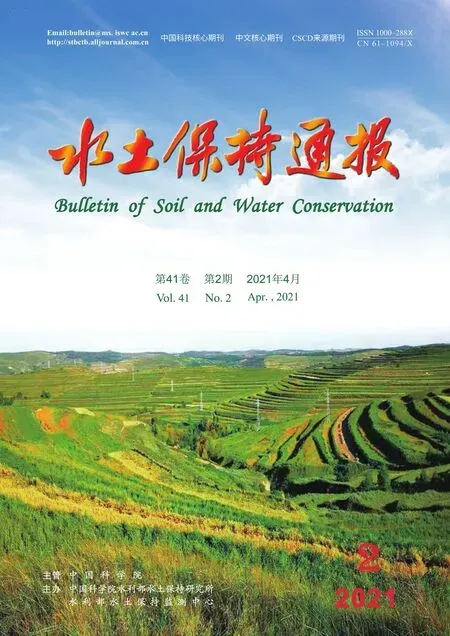基于耦合FLUS-InVEST模型的廣州市生態系統碳儲量時空演變與預測
朱志強, 馬曉雙, 胡 洪
(安徽大學 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碳儲量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中的重要環節,植被和土壤是陸地生態系統最重要的兩大碳庫,其固碳功能在緩解氣候危機上發揮著重要作用[1-3]。碳儲量變化受到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等多個組織的高度關注。國外學者對碳儲量研究較早,20世紀末Simpson[4]核算出北美東部和北部陸地針葉林碳儲量以及不同植被類型的固碳能力,Hurtt等[5]采用森林資源調查的方法研究區域碳儲量變化特點。近年來對于大區域的碳儲量研究更多的使用模型核算,如李傳華[6]采用改進的CASA模型計算石羊河流域的植被凈第一生產力(NPP),揭示影響植被碳儲量變化的驅動因子。相較于CASA模型只能計算植被碳儲量,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型可評估包含植被地上地下、土壤和死亡有機質碳儲量[7]。該模型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世界基金會(WWF)和大自然保護協會(TNC)共同開發,2010年后國內學者使用InVEST模型研究區域碳儲量變化,在白龍江、太行山等區域都取得較好的科研成果[8-9]。榮月靜[10]基于“全國生態環境遙感調查”的數據在InVEST模型中核算太湖流域碳儲量演變,指出林地和濕地轉入建設用地是太湖生態系統碳儲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土地利用變化是造成生態系統碳儲量變化的重要原因,導致大量的碳從陸地生態系統流向大氣生態系統[11]。城市建設用地擴張通過侵占林地、耕地和草地等引起的土地利用變化,使得城市生態系統面臨嚴峻的碳流失問題。城市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是近年來生態學領域研究的熱點,陸地碳儲量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環節也是眾多學者關注的目標[12]。目前關于碳儲量研究大多集中在碳儲量總量變化上的分析,鮮有模擬未來城市土地利用與碳儲量的相關研究。土地利用變化的預測可以分為數量預測和空間預測,現有模型在模擬中大多未考慮多種土地類型在轉換中的相互影響,忽略了土地類型的競爭關系。FLUS(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model)模型基于神經網絡訓練的土地適應性概率分布,提出自適應慣性競爭機制,能較好的模擬未來多種土地類型的分布[13-14]。已有多位學者使用FLUS模型在預測未來城市土地變化方面的研究,如劉小平等[15]采用該模型預測珠三角城市群的開發邊界,林伊琳[16]預測昆明市未來建設用地的擴張和景觀格局變化。最近的一些研究中也試圖在將未來土地變化與碳儲量模型鏈接起來作為評估土地變化對未來生態系統的影響,如Zhao[17]使用CA-Markov耦合InVEST模型評估生態工程對中國西北黑河流域碳儲量影響,預測實施生態工程后,2015—2029年該區域碳儲量可增加1.00×107t,證明耦合模型在評估未來碳儲量研究中具有一定科學價值。對于未來城市土地預測已有相關研究,但對于鏈接未來城市土地變化與碳儲量的研究尚少。探討城市建設用地擴張下土地利用變化對碳儲量的影響,揭示碳儲量時空演變和未來空間分布趨勢,能為城市規劃和生態脆弱區實施精準保護提供科學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介紹
廣州市地處珠江下游,瀕臨南海,位于東經112°—114°,北緯22°—24°之間。屬于丘陵地貌,東北高西南低,北部植被覆蓋密集,南部為沖擊平原。受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影響,光熱充足,降水豐富,境內河流眾多,水域面積廣闊。廣州是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樞紐城市,我國重要的經貿中心。該市下轄11個區,總面積約7 400 km2,2018年常住人口達到1 500萬,城鎮化快速發展使得建設用地逐年擴增。研究所需要的數據包括土地利用數據和土地驅動因子數據,土地利用數據:經過遙感解譯得到1990—2018年5期土地利用數據,分為林地、耕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用于土地預測的驅動因子數據有:氣象數據,包括降水和氣溫;地形數據,包括DEM(數字高程)和坡度;社會經濟數據,包括行政區劃矢量、交通網絡、人口密度和GDP;NDVI(歸一化植被指數)數據。
1.2 研究方法
1.2.1 InVEST模型 InVEST模型旨在權衡土地利用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關系,目前已經發展到包含水源涵養、生境質量、碳存儲等多個模塊,形成多種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功能為一體的重要模型[18],其中碳儲存服務模塊在美國、南美洲、非洲、東南亞等全球多區域成功運用到實際研究中。生態系統的碳儲量包括植被地上碳儲量、植被地下碳儲量、土壤碳儲量和死亡有機質碳儲量[19],即:
Ctotal=Cabove+Cbelow+Csoil+Cdead
(1)
式中:Ctoatl表示總體碳儲量;Cabove表示植被地上碳儲量;Cbelow表示植被地下碳儲量;Csoil表示土壤碳儲量;Cdead表示死亡有機質碳儲量。由于死亡有機質碳儲量含量非常低,一般不考慮[20]。
InVEST模型需要輸入研究區土地利用數據和各土地類型對應的碳密度值(即“碳密度表”),通常是借助文獻查閱得到研究區的碳密度數據。前人研究中認為處于同一氣候帶的土地類型碳密度差異較小[21-22],以榮檢[23]、朱鵬飛[24]研究中得到的廣西地區土地類型碳密度成果為主要參考,在土地類型碳密度選擇上,采用降水和氣溫因子通過公式修正本地化土地類型碳密度數據,反演得到廣州市的碳儲量。修正因子計算公式[25-26]為:
(2)
(3)
(4)
式中:KBP,KBT分別表示植被碳密度降水因子和氣溫因子修正系數;KB表示地上地下植被碳密度修正系數;KS表示土壤碳密度修正系數;C′,C″分別表示廣州和廣西地區的碳密度,由年均溫和年降水量代入公式計算得到:
CBP=6.798e0.005 4MAP
(5)
CBT=28MAT+398
(6)
CSP=3.396 8MAP+3 996.1
(7)
式中:MAP表示降水; MAT表示氣溫;CBP,CBT分別表示根據降水量和氣溫得到的植被碳密度;CSP表示根據降水量得到的土壤碳密度。綜合所得的各土地類型的碳密度值詳見表1。
1.2.2 FLUS未來土地預測模型 FLUS模型是在元胞自動機原理的基礎上耦合馬爾科夫鏈和神經網絡模型預測未來土地利用,在預測中考慮到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對土地變化的多重影響,可以模擬多類用地的演變過程,對土地類型變化的預測結果更加精確。模型主要分為兩部分:第1部分基于ANN網絡的樣本訓練得到土地適宜性概率,ANN包括輸入層、隱藏層和輸出層,通過反向傳播算法不斷更新各層之間的權重系數來達到最優估計目的,第2部分為自適應慣性和競爭機制,核心是在迭代中自適應調整慣性系數〔公式(8)〕,最終模擬結果不僅取決于神經網絡得到的土地分布概率,還受到鄰域和轉換成本等限制,體現出土地類型變化中相互作用的競爭模式[27]。
(8)


表1 研究區土地類型碳密度t/hm2

表2 土地驅動樣本數據來源
模型中設置的成本矩陣表示當前土地類型轉為其他用地的難易程度,參考自然發展條件下城市土地轉移的規則,通過探索性試驗獲得成本矩陣。根據研究區的實際情況及土地轉移概率矩陣,設置鄰域因子權重參數范圍為0~1,越接近1表示該地類的擴張能力越強[28],參考歷史土地轉移特征,經過調試和驗證,得到模擬精度較高的鄰域因子參數表(表3)。依據上述步驟,分別計算出每個柵格的總概率,將預測的土地類型分配到柵格,計算公式為:

表3 鄰域因子權重
(9)

將所有驅動因子重采樣到相同分辨率,進行標準化處理,神經網絡隱藏層設為12,先通過神經網絡樣本訓練得到研究區土地類型適宜性概率分布,標準偏差為0.226,再基于土地類型適宜性概率分布,在自適應慣性和競爭機制模型下預測未來土地分布。模型的驗證以2010年土地類型作為訓練集,預測2018年土地類型分布,總體精度94.89%,Kappa系數為93.93%,表明模型預測和真實地物分布有較高的一致性。此外,通過Precision(精確率)、Recall(召回率)和F1綜合分數進一步評價模型的預測表現,指標的計算見公式(10)—(11),各土地類型精度的綜合評價結果詳見表4。綜合以上評價結果,表明模型預測精度達到要求,可作為預測研究區未來土地利用變化。

表4 各土地類型預測精度的綜合評價結果 %
(10)
(11)
式中:tp表示真陽性記錄百分比;fn表示假陰性記錄百分比;fp表示假陽性記錄百分比。
2 結果與分析
2.1 廣州市1990-2018年土地利用與碳儲量變化
2.1.1 土地利用變化 表5—6分別為研究期內廣州市土地類型面積和土地類型動態度。從表5可知,林地是廣州市的最大景觀類型,面積所占比例在42%以上,是研究區的優勢土地景觀類型。其他土地類型面積所占比例依次是耕地、建設用地、水域、草地、未利用地。1990—2018年土地類型變化中,耕地面積的減少量最高,1990年耕地面積所占比例接近40%,2018年所占比例下降到30.15%,總共減少681.0 km2。其次是林地,減少158.5 km2,草地減少11.1 km2,未利用地減少0.9 km2,水域增加59.84 km2。面積增幅最大的是建設用地,增加791.8 km2,年均增加40.02 km2,面積所占比例從8.60%上升到19.64%,城市擴張特征明顯。建設用地是變化量最高的土地類型,其次是耕地和林地,其他地類變化量相對較小。

表5 廣州市1990-2018年各時期土地類型面積及所占比例
土地利用動態度表示研究區某一定時間范圍的土地類型變化情況,用來反映區域土地變化的幅度和速度,通過各時期動態度變化來研究土地利用變化特點。
表6是土地類型面積和動態度變化,1990—2005年土地利用動態度較高,土地變化劇烈,2005—2018年土地利用的動態度逐期下降,土地變化相對緩和。耕地在2005—2010年和2010—2018年減少量分別占2000—2005年減少量的36.69%和15.67%,研究時期的動態度分別是-0.82%,-2.25%,-0.93%和-0.42%,2005年后變化有明顯下降趨勢。1990—2018年林地動態度為-0.18%,是所有土地類型動態度最低的地類,由于林地面積所占比例最高,面積減少量仍然較高,僅次于耕地。建設用地各時期的動態度最高,分別是3.11%,9.20%,2.64%和1.08%,1990—2010年建設用地的增量較大,2010—2018年擴張趨于穩定,增量減少,增加量趨于穩定,只占2000—2005年的19.36%,建設用地迅速擴張且擴張能力明顯下降。草地在2000—2010年減少7.78 km2,受到退耕還草政策的實施效果,2010—2018年草地面積增加1.27 km2。1990—2000年水域變化明顯,面積增加81.27 km2,未利用地的面積變化較小。1990—2018年的土地變化情況來看,建設用地的動態度遠高于其他地類,研究時間內廣州市土地類型變化的主要特征是建設用地面積的快速增加,耕地和林地大量轉入建設用地。

表6 廣州市1990-2018年土地類型面積和動態度變化
2.1.2 碳儲量變化 通過查閱相關文獻以及公式修正獲得廣州市土地類型碳密度數據,結合當年土地利用數據導入InVEST模型碳模塊下運行,得到1990—2018年5期碳儲量數據及其變化。圖1是根據模型運算得到碳儲量結果。結果表明1990—2018年廣州市碳儲量減少2.48×106t,降幅6.2%,年均下降8.86×104t。其中2000—2005年的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2.18×105t,2010—2018年下降幅度為0.8%,年均下降3.74×104t。1990—2000年廣州市建設用地擴張能力較強,進入21世紀后,廣州市城市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高峰,隨著珠江新城的開發和周邊區域的城市擴張,2000—2005年碳流失達到高峰。總體上1990到2010年區域碳儲量的變化比較劇烈,該時期廣州市經濟快速增長,城鎮化速度加快,對于土地開發需求也較為強烈。2010年后建設用地擴張趨于緩和,土地變化逐漸趨于平穩,這一時期廣州市嚴重碳流失逐步得到緩解。

圖1 廣州市1990-2018年陸地碳儲量變化
2.1.3 碳儲量空間變化特征 從碳儲量空間分布來看,廣州市碳儲量空間分布具有顯著的空間異質性,圖2分別是1990,2005和2018年陸地碳儲量分布情況。由圖2可知,高密度碳儲量主要分布在東北部一帶,該區域海拔較高,擁有高覆蓋的森林面積,植被覆蓋率高;低密度碳儲量主要分布在珠江下游,該區域主要為平原,城市化程度較高;南部主要覆被農田等,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大,碳儲量維持在較低水平。東北部海拔較高,主要是山區林地覆被,碳儲量較高。高海拔決定了坡度和坡向,限制了城市用地的擴張和開墾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植被類型的分布和土壤的性質,且在水源涵養、森林資源等方面更容易占據優勢的生態位;南部屬于沖擊平原,地勢平坦,水系豐富,適合人類社會生產活動,因而固碳能力相對較弱。

圖2 廣州市1990-2018年碳儲量分布
圖3為1990—2005年和2005—2018年陸地碳儲量空間變化情況。從碳儲量空間變化來看,變化的區域具有大集聚和零星分布的特點。1990—2005年碳儲量顯著下降的區域分布在花都區、番禺區和黃埔區,主要集中在東南和西部區域,這一時期建設用地擴張劇烈,番禺區、海珠區、黃埔區和花都區擴張明顯,大量耕地和林地轉為建設用地,靠近城市中心附近的碳儲量顯著減少。2005年后建設用地擴張能力相對下降,土地類型轉移趨于穩定,區域碳儲量下降也逐漸緩和,受城市東擴影響,碳儲量顯著大面積下降的區域主要是黃埔區和增城區西南,城市中心區域的周邊也有零星的減少,如白云區和花都區等。東北部區域的從化區和增城區北部碳儲量較為穩定,該區域覆被大量森林資源,城鎮擴張能力較低,碳儲量相對穩定,珠江下游區域受城市發展影響,碳儲量變動較大。總體上廣州市碳儲量在2005年之前有明顯的下降,2005年后下降幅度低于前期,2005—2018年碳儲量總體變化較之前緩和。

圖3 廣州市1990-2018年陸地碳儲量空間變化
2.2 未來建設用地擴張與陸地碳儲量變化
2.2.1 未來土地預測與碳儲量潛力 從預測的2034年土地分布來看,建設用地會進一步擴張。從2018年1 409.11 km2增加到2034年的1 683.48 km2,面積增加274.37 km2,年均增長17.14 km2,動態度1.22%,耕地與林地面積持續下降,預計分別下降173.6和91.8 km2,低于1990—2018年土地類型變化程度,總體上未來廣州市土地變化趨于穩定。預測結果表明建設用地仍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擴張,分析未來建設用地擴張對碳儲量變化影響,揭示在自然發展條件下未來廣州市碳儲量分布變化。從廣州市2018—2034年土地利用變化預測情況分析(圖4),未來白云區和花都區的交界處建設用地的擴張能力仍較強,交界區域的城市擴張明顯,中心城區與花都區和白云區具有較高可能性連成一個整體,建城區的斑塊聚集度提高,散落在中心城區外圍和周邊區域的耕地在未來有較大的可能性會轉為建設用地,聚集成更大的斑塊。且擴張侵占的土地上,可能會進一步侵占更高碳密度的土地類型,如分布在從化區、白云區和增城區的林地等也有轉為建設用地的趨勢。2034年廣州市碳儲量仍會進一步降低,預計將會減少1.20×106t,降幅3.2%,年均下降7.50×104t,低于1990—2010年的年均下降1.09×105t,高于2010—2018年的年均下降6.00×104t,表明在自然發展條件下,廣州市碳儲量流失整體上已經沒有1990—2010年劇烈。預測2034年從化區碳儲量所占比例將上升到40%,廣州市北部和中部森林資源豐富,北部受制于地形因素,城鎮建設較為緩慢,未來仍是廣州市乃至珠三角重要的碳匯區域,中部林地靠近市區,受到城市建設用地擴張風險較大,碳儲量比重進一步降低。預測碳儲量減少的區域在花都區和白云區的交界較為顯著,未來這一區域的碳儲量最易流失,增城區西部和黃埔區也會存在較大的碳儲量流失風險,主要原因可能是該區域的林地有較大的概率轉為建設用地。碳儲量下降最高的區域分別是增城區、白云區和花都區,預計分別下降2.95×105t,2.10×105t和1.83×105t。黃埔區和白云區交界處的白云山是臨近中心城區的較大森林覆蓋區域,擁有豐富的林地和生物資源,對于保護中心城區的碳平衡和生態系統的穩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圖4 廣州市2018-2034年土地利用與碳儲量變化
此外其他區域也會發生不同程度的碳儲量變化,從化區南部有一定碳流失風險,北部碳儲量微量增加,南沙區整體較為穩定。未來部分區域碳儲量流失仍然較為嚴峻。
2.2.2 建設用地與低密度碳儲量重心遷移 城市建設用地擴張與碳儲量生態系統服務是碳儲量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城市建設用地擴張造成耕地林地等高密度固碳土地類型轉成低密度固碳土地類型,加重碳儲量生態系統功能的危機。在計算得到的碳儲量分布圖上劃分碳密度等級,選擇低密度碳儲量空間分布,通過不同時期的重心遷移分析建設用地與碳儲量的關系。圖5為廣州市1990—2034年不同時期建設用地與低密度碳儲量的重心變化,從重心遷移結果看,1990—2000年建設用地擴張的整體朝向東南部,2000—2010年重心向東北方向遷移,2010到2018年城市持續向東北擴張,但遷移距離減小,隨著西部花都區等區域副中心城鎮的擴張仍充滿潛力,向西遷移趨勢有所增加。總體上城市重心整體在向東北偏移,且逐漸由東北偏向正北,遷移距離先增后減。預測2018—2034年建設用地重心朝向西部,遷移距離在減少,說明城市擴張幅度在波動中趨于穩定,低密度碳儲量空間重心遷移與建設用地擴張方向基本吻合,表明建設用地的擴張與低密度碳儲量空間演變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圖5 廣州市1990-2034年建設用地與低密度碳儲量重心變化
3 討論與結論
本文在預測未來土地的驅動參數上選擇有限,對人文因子僅考慮人口、GDP和交通分布,人文因子是一個復雜的指標,包括工業產值、工廠分布、政策制定、開發紅線等,今后在驅動因子選擇中可以構建科學的人文因子模型作為預測條件。未來城市土地變化中受到耕地紅線、生態紅線的限制,本次預測中暫不考慮政策因素,只考慮了自然情景下未來土地類型的預測,沒有針對生態保護、耕地保護等限制條件下的情景模擬,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慮在受到“三生空間”政策影響下不同情景的未來城市生態系統功能變化。
(1) 1990—2018年廣州市土地利用變化的特征表現為建設用地的快速擴張,增幅128.3%,變化量最高,其他用地均有不同程度變化,其中耕地面積減少量最高,其次是林地。1990—2005年是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較大的時期,2010年后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顯著下降。
(2) 廣州市碳儲量分布具有空間差異規律,總體上表現為高值集聚在北部,低值集聚在西南。北部森林覆蓋面積大,海拔高,是碳儲量分布的主要位置,從化區、花都區和增城區是廣州市重要的碳匯區域;西南部城市化程度高,城市擴張活動頻繁,城市中心碳儲量比較低。1990—2005年是碳流失較嚴重時期,與城市擴張密切相關,2010—2018年碳流失相對緩和。
(3) 預測未來建設用地面積仍會繼續增加,擴張幅度將會下降,擴張重心朝向西部花都區和白云區等。預測未來碳儲量會進一步下降,碳儲量減少的區域主要位于廣州市西北和主城區東部附近。西北區域建設用地未來可能與主城區形成大面積的低碳儲量區域,對于城市生態系統穩定是較大的威脅,未來廣州市部分區域仍會存在一定的碳流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