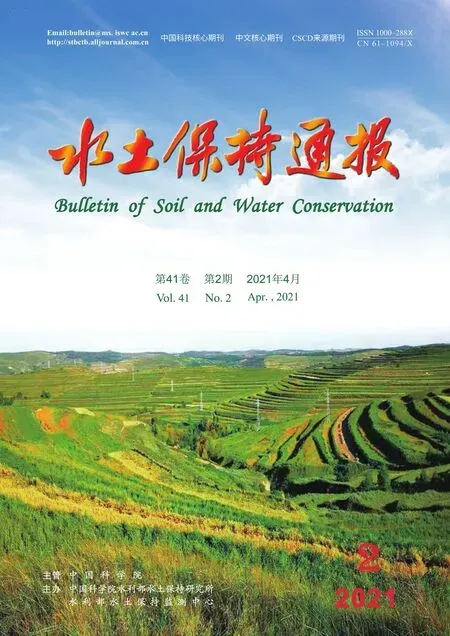基于景觀結構的黃河沿岸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時空變化分析
——以河南省為例
張 鋒, 陳偉強, 馬月紅, 耿藝偉
(河南農業(yè)大學 資源與環(huán)境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2)
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評價是針對土地利用過程中發(fā)生不利生態(tài)影響可能性的評價,對認知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產生機制,降低生態(tài)風險概率以及優(yōu)化土地利用具有重要意義[1-2],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fā)展,導致環(huán)境管理目標的轉變,多風險源、多受體及區(qū)域景觀水平階段已經成為當前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評價研究的重點[3]。而基于人類開發(fā)導致的景觀格局轉變、土地利用類型變化的生態(tài)風險評價更加關注生態(tài)風險的時空異質性,其重點為評價人類活動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產生的不良影響[4]。近年來,由于大、中型城市建設以及“城鄉(xiāng)融合”等戰(zhàn)略的實施,土地開發(fā)活動愈加頻繁,導致各種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的出現,生態(tài)風險評價逐漸成為研究和解決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要手段。國內大量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區(qū)域生態(tài)風險進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生態(tài)風險評價模型:包括基于P-S-R模型設計土地利用生態(tài)安全(LUES)分級標準構建生態(tài)風險模型[5-6],利用土地類型面積比重構建生態(tài)安全評價模型[7-8],從景觀結構角度利用景觀擾動指數與景觀脆弱指數構建模型對區(qū)域生態(tài)風險進行評價等[9-11],其中從景觀角度出發(fā)進行生態(tài)風險的研究越來越多,研究尺度大到城市群[12]、市域[13-15]、小到縣域[4]、濕地公園等[11],研究區(qū)域包括流域[16-17]、干旱區(qū)[10]、海岸帶[18]、丘陵區(qū)[19]以及農林交錯帶等[9],盡管前人研究尺度以及研究區(qū)域包含甚廣,但對黃河沿岸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的研究還有所缺乏,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民族的發(fā)源地,從西到東橫跨9個省區(qū)以及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黃淮海平原4個地貌單元,由于河水沖積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類型變化頻繁。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量發(fā)展座談會并發(fā)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和生態(tài)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刻闡明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量發(fā)展的重大意義,因此研究黃河流域沿岸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變化特征,對加強黃河治理保護、降低黃河沿岸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具有重大意義。為此,本文以河南省黃河沿岸7個城市為研究對象,以2005,2010,2015以及2018年4期土地利用數據為基礎,根據景觀擾動指數與景觀脆弱指數構建生態(tài)風險評價模型,借助土地轉移矩陣與空間自分析方法對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進行分析與評價,研究結果可為正確認識黃河流域沿岸城市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對土地景觀資源保護、生態(tài)系統(tǒng)優(yōu)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管控措施制定等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1 數據和方法
1.1 研究區(qū)概況
黃河流域途徑河南省7個市區(qū),包括三門峽市、洛陽市、焦作市、新鄉(xiāng)市、鄭州市、開封市以及濮陽市,屬北亞熱帶向暖溫帶過渡的大陸性季風氣候,南北過渡性明顯。研究區(qū)域大多為平原、丘陵地貌,耕地是主要的景觀基質,林地和草地主要位于研究區(qū)的西南方向,以鄭州為中心的7個市區(qū),近幾年來發(fā)展迅速,建設用地面積快速增長。
1.2 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2005,2010,2015和2018年土地利用類型柵格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huán)境科學數據中心。所用數據的分辨率為30 m,在此基礎上參考《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21010-2017)》并結合研究區(qū)實際情況將研究區(qū)土地類型分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以及未利用地(見封3,附圖4)。
1.3 研究方法
1.3.1 構建生態(tài)風險指數
(1) 景觀擾動指數(Ei)。同一地區(qū)的生物多樣性、生態(tài)環(huán)境整體結構和功能、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更新和演替受到不同景觀類型構成的影響,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同時生態(tài)系統(tǒng)抗干擾能力的大小也與該地區(qū)景觀類型的構成密切相關[4]。景觀擾動指數(Ei)用來反映外界干擾(主要是人類活動)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由不同的景觀類型組成)的影響程度,可以通過對景觀破碎度指數(Ci)、景觀分離指數(Ni)和景觀優(yōu)勢指數(Di)三者賦予權重累加獲得,以反映出不同景觀構成的干擾程度,景觀擾動指數的大小主要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受人類開發(fā)活動影響越大,擾動指數越大,隨之生態(tài)風險越大,反之則越小[2,4,9-10],景觀擾動指數(Ei)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Ei=aCi+bNi+cDi
(1)
式中:a,b,c為各景觀指數權重,且其和為1,根據前人研究結果[9-11]并結合研究區(qū)特點,認為景觀破碎度的分布特征比較重要,分離度重要程度,結合專家打分法將景觀破碎度權重賦值為0.5;分離度賦值為0.3;優(yōu)勢度賦值為0.2。
景觀破碎度指數(Ci)可表示為:
(2)
景觀分離指數(Ni)可表示為:
(3)
景觀優(yōu)勢指數(Di)可表示為:
(4)
式中:Ai為景觀類型i的面積;A為景觀總面積;ni為景觀類型i的斑塊數;Qi為斑塊i出現的風險小區(qū)數/總風險小區(qū)數;Mi為斑塊i的數目/斑塊總數;Li為斑塊i的面積/風險小區(qū)的總面積[2]。
(2) 景觀脆弱指數(Fi)。景觀脆弱指數用來表示不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易損性,不僅反映了土地本身的自然屬性,更是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景觀脆弱指數越大,表明對區(qū)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干擾越大,區(qū)域生態(tài)風險越高。結合前人研究以及研究區(qū)實際情況認為建設用地最為穩(wěn)定,不易產生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故將建設用地賦值為1;未利用地是指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荒草地、沙地、裸巖、裸土地等,受環(huán)境變化、人類活動影響較大,土地利用類型改變相對容易,其景觀脆弱性最強,最為敏感,故將未利用地賦值為6;水域、耕地、林地、草地則根據前人研究結果和各自脆弱性特點分別賦值為5,4,3,2[2]。進行歸一化處理后得到研究區(qū)的各土地類型景觀脆弱指數。
(3) 生態(tài)風險指數(ERI)。在對上述景觀擾動指數和景觀脆弱指數研究分析的基礎上,為了描述樣地內生態(tài)損失的大小,通過采樣方法將空間格局轉變?yōu)樯鷳B(tài)風險變量,以此構建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指數ERI。
(5)
式中:n為景觀類型數量;Ski為第k個風險小區(qū)第i類景觀組分的面積;Sk為第k個風險小區(qū)總面積。
1.3.2 空間自相關分析
(1) 全局Moran’sI指數。空間自相關分析的目的是度量某一變量是否在空間上相關,并描述其相關程度如何。本研究采用Moran’sI指數圖對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全局空間自相關進行分析描述。具體計算公式[20]為:
Global Moran’sI=
(6)

(2) 局部Moran’sI指數。利用局部Moran’sI指標局部空間自相關性,對空間集聚和空間異質進行識別,并生成LISA聚類圖。局部Moran’sI指數計算公式為[20]:
(7)
(8)
式中:yi,yj是標準化后的空間單元觀測值; 其余變量與全局Moran’sI指數變量含義相同。
1.3.3 基于格網的生態(tài)風險小區(qū)劃分與生態(tài)風險空間分析 本文根據研究區(qū)特點,在參考前人研究以及考慮研究區(qū)空間異質性和斑塊大小的基礎上[4,9,12],借鑒傳統(tǒng)景觀生態(tài)學中關于景觀取樣大小的方法,即網格劃分大小應當為斑塊平均面積的2~5倍,為減少網格對大斑塊的切割,選取耕地平均斑塊面積的5倍,利用GIS軟件將研究區(qū)劃分6 km×6 km的采樣網格,采樣方式為等間距系統(tǒng)采樣法,共計1 737個生態(tài)風險小區(qū)。在利用空間自相關分析證明了生態(tài)風險評價值有空間自相關性的基礎上,在GIS中計算每個生態(tài)風險小區(qū)的生態(tài)風險值,然后將每個網格的值賦予該網格的中心點,最后采用克里金插值法進行空間插值得到研究區(qū)生態(tài)風險的空間分布值。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通過2005—2018年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表(表1)分析可知,從總體上看,13 a間,研究區(qū)域內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38.05%,增長趨勢較快,這與城市化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城市的擴張是分不開的,其中草地面積減少了10.70%、林地面積減少了2.41%,一部分是土地開墾導致的面積減少,還有一部分是建設用地的擴張占用了城市周圍的草地和林地;水域面積減少了4.81%,這可能是由于河流水位的逐漸下降,開墾河畔導致水域面積減少;未利用地面積減少了34.75%,大部分是由于開墾耕地導致的。從土地類型轉變上看,13 a間有277 495.47hm2耕地轉化為建設用地,這是建設用地增加的主要來源,表明早期的城市擴張大多是以犧牲耕地為主;在研究時期內,有96 759.81 hm2的建設用地轉化為耕地,其中主要是農村居民點用地轉化為耕地,這是由于在“城鄉(xiāng)融合”、“美麗鄉(xiāng)村建設”和“鄉(xiāng)村振興”等戰(zhàn)略的實施下,河南省開展大量村莊規(guī)劃、整治工作,在土地整治、遷村并點等具體工程中使得原本凌亂分布、用地浪費的農村居民點變得更加集中,同時將廢的宅基地復墾為耕地,使得耕地面積增加;而草地、林地和水域分別有44 580.87,35 392.32,31 014.36 hm2轉化為耕地,是補充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的主要來源。

表1 研究區(qū)2005-2018年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hm2
2.2 景觀格局指數變化分析
由表2景觀指數統(tǒng)計結果可知,2005—2018年,耕地是研究區(qū)域內最主要的景觀,班塊面積最大,分布最為廣泛;其次是建設用地。從破碎度和分離度來看:在研究期限內耕地的破碎度先減小后保持不變,分離度先減小后增加,減小的拐點都出現在2010年,這是由于在2010年耕地斑塊數量出現較大幅度減少;建設用地面積和斑塊數量不斷增加,破碎度和分離度相對2005年都有所降低,這是由于建設用地的擴張占用了周圍其他用地類型,使的建設用地集聚性不斷增強;林地面積和斑塊數量在2005—2010年期間減少較快,2010—2018年期間變化幅度較小,所以其破碎度和分離度先減小后基本保持不變;草地面積整體上在減小,而斑塊數量變化幅度不大,因此其破碎度和分離度整體上在增大;水域面積先增后減,而斑塊數量一直在增多,這可能是水位下降導致水域連通性減低,導致其破碎度和分離度在不斷增加。

表2 黃河沿岸各景觀類型景觀指數統(tǒng)計
2.3 生態(tài)風險分析
2.3.1 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空間自相關分析 根據每個網格計算的生態(tài)風險值,利用GeoDa軟件計算出研究區(qū)域內生態(tài)風險指數的2005,2010,2015以及2018年4期全局Moran’sI值,分別為0.561 9,0.573 7,0.568 2以及0.566 3,且通過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值在空間上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存在空間集聚特征,同時為下一步的插值分析奠定了理論前提。與全局自相關相似,利用GeoDa軟件對4個時期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指數的局部空間聚集情況進行分析,得到LISA聚類圖(圖1),由圖1可知,研究區(qū)域內以“高—高”、“低—低”聚集模式為主,說明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急劇變化的區(qū)域相對較小,“高—高”區(qū)域主要分布在黃河沿岸以及農村居民點散亂分布的區(qū)域,“低—低”區(qū)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區(qū)域邊界處,主要是大面積的林地以及草地分布區(qū)。

圖1 黃河沿岸2005-2018年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值LISA聚類圖
2.3.2 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時空變化分析 根據每個網格計算的生態(tài)風險值,將值賦予網格中心點,采用克里金插值法進行空間插值得到4個時期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值的空間分布圖(圖2)。利用自然斷點法將研究區(qū)劃分為5個生態(tài)風險等級:低風險區(qū)(0.047≤ERI<0.087),較低風險區(qū)(0.087≤ERI<0.105),中風險區(qū)(0.105≤ERI<0.119),較高風險區(qū)(0.119≤ERI<0.131),高風險區(qū)(0.131≤ERI<0.151),結果見圖2。從生態(tài)風險值大小來看:2005—2018年,4個時期生態(tài)風險最小值依次為0.047 2,0.047 5,0.047 4以及0.047 6,最大值依次為0.147 9,0.150 5,0.146 2以及0.150 7,最小值和最大值大致呈N形變化,并且變動幅度較小。從空間分布來看,在4個時期內,高風險區(qū)分布區(qū)域大致相同,呈條狀和塊狀分布,條狀大多分布在黃河沿岸,由于黃河水位的變化以及河水對兩岸土壤的沖擊,土地利用類型不斷變化,大部分在耕地和水域之間轉變,使得人類干擾活動增強,導致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較高;塊狀高風險區(qū)大多分布在農村居民點零散分部的平原區(qū),由于居民點斑塊分布過于零散,破碎度以及分離度較高,使得干擾度較高,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值也高。低和較低風險區(qū)大多分布在研究區(qū)域四周以及西南大部分區(qū)域,其中西南、西北區(qū)域大部分為大面積的林地和草地,受人為干擾較小,生態(tài)風險值低;其他低和較低風險區(qū)所處的區(qū)域耕地和建設用地是主要的景觀基質,并且農村居民點面積都較大,耕地和建設用地破碎度和分離度較小,生態(tài)風險值較低;在較高風險區(qū)包裹的研究區(qū)域中部出現部分較低風險區(qū),大多位于各城市建成區(qū),由于大面積都是建設用地,受人類干擾后的損失度低,生態(tài)風險值相對較低。

圖2 研究區(qū)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空間分布
由表3各年份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等級面積分析可知,在研究時限內,較低風險區(qū)和較高風險區(qū)所占面積最大,其次是低風險區(qū)和中等風險區(qū),面積最小的是高風險區(qū);從面積變化來看,低風險區(qū)和中等風險區(qū)面積在逐年增加,分別增加了335 223.45和149 024.16 hm2,較低風險區(qū)面積先減少后增加,總體上較2005年減少了143 642.72 hm2;高風險區(qū)和較高風險區(qū)面積在逐年減少,分別減少了179 419.86和161 185.05 hm2,風險區(qū)面積變化說明,研究區(qū)內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整體上在不斷改善;由表4各類風險區(qū)面積轉移矩陣分析可知,有342 231.48 hm2的較低風險區(qū)轉化為低風險區(qū),是低風險區(qū)面積增加的唯一來源;中等風險區(qū)主要向較低風險區(qū)轉化,占中等風險區(qū)轉出面積的98.4%;較高風險區(qū)轉出對象涉及到3個風險區(qū),最主要是中等風險區(qū),面積達到325 801.08 hm2;50%左右的高風險區(qū)全部轉化為較高風險區(qū),其中塊狀高風險區(qū)面積減少較多,主要是因為城鎮(zhèn)居民點斑塊在擴張,農村居民點小斑塊數目減少,大班塊數目增加,耕地和建設用地的連通性都在增強,破碎度和分離度降低,生態(tài)風險值隨之降低,其他塊狀高風險區(qū)面積減少的原因也與之相同。從總體轉移方向來看,各風險區(qū)主要向相鄰風險區(qū)轉化,僅有少量地區(qū)出現跨區(qū)轉移,說明研究區(qū)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變化相對穩(wěn)定,生態(tài)風險急劇變化的區(qū)域較小。

表3 研究區(qū)各年份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等級面積hm2

表4 2005-2018年各類風險區(qū)面積轉移矩陣 hm2
3 討論與結論
(1) 2005—2018年,從地類變化來看:研究區(qū)域內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且增長趨勢較快;其他幾類用地面積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從地類轉移來看,耕地是建設用地增加的主要來源,林地、草地和水域主要轉化為耕地,不同程度上補充了建設用地對耕地的占用。
(2) 在研究時段內,研究區(qū)域內四期生態(tài)風險指數全局Moran’sI值分別為0.561 9,0.573 7,0.568 2以及0.566 3,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在空間上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存在空間集聚特征;且LISA聚類圖顯示研究區(qū)域內“高—高”、“低—低”是生態(tài)風險主要的空間聚集模式,說明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急劇變化的區(qū)域相對較小。
(3) 2005—2018年,生態(tài)風險最小值和最大值呈N形變化,且變化幅度較小;4個時期內,高風險區(qū)分布區(qū)域大致相同,呈條狀和塊狀分布,條狀大多分布在黃河沿岸,塊狀高風險區(qū)大多分布在農村居民點零散分部的平原區(qū);低和較低風險區(qū)大多分布在研究區(qū)域四周以及西南大部分區(qū)域,這些區(qū)域大部分為大面積的林地和草地。在研究時限內,低風險區(qū)和中等風險區(qū)面積在逐年增加,其中較低風險區(qū)是低風險區(qū)面積增加的唯一來源,中等風險區(qū)轉入的主要來源是較高風險區(qū);較低風險區(qū)面積先減少后增加,總體呈減小趨勢;高風險區(qū)和較高風險區(qū)面積在逐年減少;各風險區(qū)主要向相鄰風險區(qū)轉化,僅有少量地區(qū)出現跨區(qū)轉移,說明研究區(qū)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變化相對穩(wěn)定,生態(tài)風險急劇變化的區(qū)域較小。
研究區(qū)地勢西高東低,除三門峽和洛陽兩市有大面積集中分布的林地和草地外,其余各市林地和草地面積相對較少,因此研究區(qū)內低和較低風險區(qū)主要集中分布在三門峽和洛陽兩個地區(qū);黃河沿岸高風險區(qū)主要位于焦作、新鄉(xiāng)、鄭州和開封4個地區(qū),主要是由于這4個地區(qū)黃河沿岸多為耕地,河水沖積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并且水位下降使得沿岸土地類型在耕地和水域之間轉變,受人為干擾活動較大,生態(tài)風險較高,并且在13 a間面積變化不大,非黃河沿岸的高風險區(qū)多處于農村居民點斑塊破碎,且斑塊面積較小的地區(qū),主要分布在洛陽、新鄉(xiāng)和開封,建設用地和耕地連通性弱,破碎度和分離度大,生態(tài)風險值較高,在研究時限內高風險區(qū)面積減少部分多來源于塊狀高風險區(qū),尤其是焦作和新鄉(xiāng)兩市,自2010年開始高風險區(qū)幾乎全部轉化為較高風險區(qū),這部分地區(qū)耕地和農村居民點用地是主要土地類型;在河南省開展遷村并點、土地整治等活動下,建設用地和耕地斑塊總數量在減少,但大斑塊數量在增多,因此連通性增強,生態(tài)風險值在降低,因此科學的村莊規(guī)劃、整治工作在改善農村人居環(huán)境的同時也可以降低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洛陽、三門峽兩個地區(qū)黃河沿岸多為林地和草地,可以降低水土流失風險,減小了土地類型轉變的頻率以及人為干擾活動的影響,生態(tài)風險值較低。因此就研究區(qū)而言,洛陽、三門峽兩個地區(qū)應注重林地和草地的保護,穩(wěn)定該地區(qū)黃河沿岸土地利用低風險現狀,同時開展科學合理的村莊規(guī)劃,可以有效降低平原地區(qū)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值;焦作、新鄉(xiāng)、鄭州和開封應注重對黃河沿岸水土流失的治理,穩(wěn)定黃河沿岸土地類型,降低人為活動干擾,同時對散亂分布的農村居民點進行科學合理的規(guī)劃、整治,提高建設用地連通性,降低耕地破碎度,以達到降低土地利用生態(tài)風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