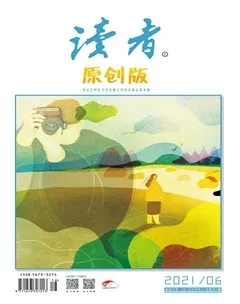夏至:晚風來去吹香遠
王選
一
冬至餃子夏至面。這碗面,該是漿水面。
漿水,能調中引氣,開胃止渴,解煩去燥,調理臟腑,亦能利小便。夏至時節,烈日炎炎,來一碗漿水面,或飲一碗涼漿水,真是人間至味,即便佳肴滿桌,也可拂袖不理。漿水里撒白糖,攪勻,喝一氣,酸酸甜甜,勝過一切飲料。有年麥黃,我們提鐮下地,父親給我們提了一罐糖漿水。我們頭頂驕陽,身陷麥浪,大地如蒸籠,能把人蒸個半熟,割倒一片麥子后,我們一人灌了一氣糖漿水,感覺全世界一瞬間涼了下來。
我至今懷念那金黃色的午后和酸酸甜甜的味道。
夏至,在古時叫“夏節”。夏至時值麥收,古人慶祝豐收、祭祀先祖,北祈雨,南求晴,以期豐年消災,又祈獲得“秋報”。
夏至這天,是北半球一年之中白晝最長的一天,太陽運行至黃經90°,直射地面的位置到達一年中的最北端。夏至后,太陽直射地面的位置逐漸南移,北半球的白晝日漸縮短,民間有“吃過夏至面,一天短一線”的說法。唐代詩人韋應物在《夏至避暑北池》一詩中也曾用“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來形容夏至這一天的獨特。

夏至雖表示炎夏已至,但還不是最熱的時候。夏至后的一段時間內,氣溫仍會繼續升高,再過二三十天,進入小暑、大暑節氣,酷暑才算真正來臨。
二
除了漿水面,在我老家西秦嶺一帶,夏至,吃一碗鍋鯫是必不可少的。鍋鯫,又叫面魚、漏魚兒。
做漏魚兒,我們叫跌鍋鯫,跌有“掉落”之意。跌鍋鯫要有專門的工具—漏馬勺。漏馬勺早年多是黑陶制品,中間有孔。但陶易碎,漏馬勺常在灶臺磕碰,時有破裂。破裂后修補需用錐子打孔,再用細麻繩將裂縫固定。如此修補一番,又可用三年五載。后來有鋁制漏馬勺,銀色,結實,但愛粘面團,不太好使。
大火燒水,水滾,往鍋里邊撒玉米面邊攪動。要讓面在指縫間均勻灑落,否則會煮成面疙瘩,外熟里生。還要不停攪動,一開始用筷子攪,后來面糊逐漸黏稠,得換短搟面杖。金黃的玉米面糊糊在鍋里冒泡,撲哧一個,撲哧又一個。等面團稠度合適以后停止撒面,再攪動一陣,直到提起搟面杖面團能扯絲,稀稠即可。余火再攪拌三五分鐘,待面團溫熱。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做馓飯。
再炒臊子。鍋鯫的臊子分兩種,漿水臊子和醋臊子。漿水臊子的做法和熗漿水一樣,準備紅辣椒或蒜瓣,熱油熗好;醋臊子講究就多了,切蒜薹丁、洋芋丁,用肉炒,加水,等半開,放木耳、黃花菜,最后撒一把蔥末。
然后跌鍋鯫。用大鋁盆接半盆涼水,放地上,漏馬勺在涼水中一蘸,防粘。用木勺把面舀進漏馬勺,蹲在盆前,用木勺背擠壓面團,面從圓孔中鉆出,形如小魚,光溜溜,滴滴答答,跌入涼水。一進水,浮游片刻,后沉入盆底。如此反復,把鍋中面團全部用完,盆里就落了一層面魚。它們有憨胖的腦袋、細長的尾巴,在清水里沉沉睡著,像夏至的孩子。
把鍋鯫控掉涼水,舀入碗中,澆上臊子,調鹽,調辣椒。一定要紅油辣椒,并且要多放,紅艷艷,油汪汪。端起碗,面魚滑爽,入口不用咬,滴溜溜,全游進喉嚨,進入肚子。鍋鯫不占肚子,有的人能吃四五碗,但吃多了脹。吃脹了,院子里溜達幾圈,就好了。院子里,梨樹葉稠,大麗花開得正艷,母雞帶著換過毛的雞娃蹦跶著捉一只蝗蟲。
天真藍,烈日懸空,白花花一片,泥土中升騰出熱氣。扯一把破躺椅擺在屋檐下,抱著滾圓如瓜的肚子睡一會兒。夢里,成百條魚兒,在胃里嬉戲。
三
古代將夏至分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蟬始鳴;三候半夏生。
麋與鹿雖屬同科,但古人認為,二者一屬陰一屬陽。鹿角朝前生,屬陽,夏至日,陰氣生而陽氣始衰,陽性的鹿角便開始脫落;而麋屬陰,在冬至日角才脫落。知了在夏至后因感陰氣之生便鼓翼而鳴。半夏為一種喜陰藥草,因在仲夏時節出生而得名。由此可見,在炎熱的夏天,一些喜陰生物逐漸出現,而陽性生物開始衰退。
在我老家,麋和鹿自然難以遇見,蟬亦不多,每入夏季,有零星之聲,粘在槐樹之上鳴叫,并無聒噪之音,想必是老家海拔高、氣溫較低的緣故。而半夏,就很常見了。
夏至時節,半夏抽芽,生兩枚或三枚葉片,葉面嫩黃且油亮。半夏多生在麥田或玉米地中,隨手一挖,潮濕的泥土中便出現一根嫩白的根,粗細如火柴桿,根的中部有一兩處隆起,是半夏的幼小胚胎。到麥收后,大暑時節,半夏長大,葉面變墨綠,在麥茬中間異常顯眼。我們扛著鋤頭去挖半夏,一挖一窩,一個下午能挖三五斤。半夏提回家,去皮,淘洗,晾曬,待秋天得空便去集上賣掉。也賣不了幾個錢,五六十元,添補點兒油鹽醬醋,或攢起來,秋季開學交學雜費。
夏至以后地面受熱強烈,空氣對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陣雨。這種熱雷雨驟來疾去,降雨范圍小,人們稱“夏雨隔田坎”。長江中下游地區,此時正處于“梅子黃時雨”,黃淮平原則是“云來常帶雨”。充沛的雨水可滿足作物生長要求,也創造了一個水熱同季的有利環境。而這種情況下,田間雜草和莊稼一樣,生長也很快,不僅與作物爭水、爭肥、爭光,還攜帶多種病菌和害蟲,需盡快鏟除雜草。因此農諺說:“夏至不鋤根邊草,如同養下毒蛇咬。”
此時,在東北、關中平原,冬小麥開始收割;貴州等地的玉米、高粱抽穗吐絲;產棉區的棉花已經現蕾,營養生長和生殖生長兩旺;高原牧區則進入草肥畜旺的季節。
四
關山應是一道門檻。夏至時節,門檻東邊,關中平原上麥子已黃,萬畝良田如金色地毯平展鋪開,收割機吐著黑煙,也吐著突突聲,在麥地往返。門檻西邊,麥子以10天為期,往西漸次成熟。在老家麥村,割麥尚需時日,但麥子已呈杏黃色,麥穗飽滿,麥稈微綠。我們站于梁頂,遠眺麥田,麥田繡于蒼翠的草木中間。風吹麥浪,如手帕招搖,似乎在說,快了,快了。

我們去趕集。起個大早,睡眼蒙眬,涼水胡亂一擦臉,父親領著,一步步朝山下走去,步行40分鐘才到集上。集市是條街,貨物擺于街道兩側。集上已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背著背簍,或提著化肥袋,或胳肢窩里夾著舊書包。我們從右側沿貨攤而行,父親邊走邊詢問價錢,不時停下,拿起貨物端詳一番。再行,到集市末端折回,靠另一邊,也是邊走邊看邊問。貨比三家,一個來回,質量、價錢,父親已了然于胸,再折回,挑遂意的討價還價一番,最后買下,裝入舊書包。父親買了三張刃片,買了磨石,還買了兩頂草帽,割麥時用的;買了30個化肥袋,裝麥子用的;買了兩根麻繩,馱麥時用的。父親還買了少許蔬菜,給我買了一頂涼帽,給妹妹買了一雙粉色涼鞋。有一雙膠鞋,質量好,割麥時能穿,父親摩挲了許久,嫌貴,沒舍得給自己買。
我們出了集市,路口有小吃攤,賣麻花、韭菜盒子、面皮、牛筋面、涼粉等。經過攤位,瞥一眼,再聞一下香味,我便挪不動腳了。父親已看穿我的心思,問:“想吃啥?”我毫不含糊地說:“涼粉。”“坐下吃吧!”又轉頭跟攤主說,“來一碗涼粉!”
我要了一碗蕎麥涼粉,辣椒多,醋多。辣椒和醋都是農家自產,味道極香。攪拌后,一根根涼粉軟嫩剔透,裹著紅油辣椒。我咽一口唾沫,舉起筷子,狼吞虎咽。一碗涼粉下肚,渾身清爽,暑氣已消,胃里踏實妥帖。我把碗底的醋汁也一飲而盡,伸著舌頭,把嘴唇上的辣椒油舔干凈,用袖子一抹嘴,余香依然在口中彌漫。父親站在一側看著我吃,嘴角含笑。我那時年幼,不懂父親心境,他舍不得為自己花一塊五毛錢。臨走前,他給妹妹買了一根麻花。
我們回家去,父親接過包背上,我跟隨在后,頭戴新涼帽,蹦蹦跳跳,如一只螞蚱。再有一周,我們就該割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