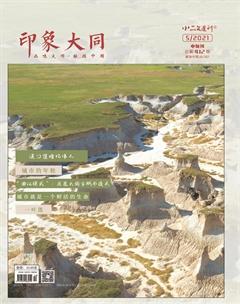大同馬市、晉商出現(xiàn)的標(biāo)志,大明落魄的開始
佚名


“馬市”是明、清兩代為了邊境貿(mào)易而設(shè)立的市場,內(nèi)地的綢緞、鐵器、糧食等貨物可以在“馬市”內(nèi)與蒙古部落的牛羊、馬匹進(jìn)行交易。而位于大同市北40公里的長城腳下、與內(nèi)蒙古交界的得勝堡“馬市”則是明清兩代交易的主要地點(diǎn)。
明正統(tǒng)三年(1438年)4月,明王朝為了減少刀兵和戰(zhàn)爭,羈縻北方強(qiáng)悍部族,批準(zhǔn)了當(dāng)時(shí)大同巡撫盧睿的請求,在得勝堡開設(shè)“馬市”進(jìn)行平價(jià)駝馬交易,朝廷還派出懂得蒙語的“翻譯”協(xié)助,與以脫歡為首的瓦剌部落進(jìn)行交易。
“馬市”的開設(shè)可以說是當(dāng)時(shí)明朝廷和瓦刺雙方都比較滿意的措施。明朝廷需要邊境的和平和瓦刺部落的牛馬,而瓦剌需要內(nèi)地的糧食、鐵器和綢緞。這樣,盧睿的主意換來了十多年的安寧和和睦。
而得勝堡“馬市”也開啟了中原漢民族與長城外蒙古各部落的友好貿(mào)易和往來,一直持續(xù)了11年。
到了明正統(tǒng)14年7月,因蒙古瓦剌部落首領(lǐng)也先認(rèn)為明朝官吏裁減馬價(jià),便舉兵大肆入侵中原,主力直逼大同。明英宗在王振鼓惑和挾持下,不顧臣僚勸阻,決意親征。由于王振貽誤軍機(jī),明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被瓦剌軍包圍。1449年8月31日(正統(tǒng)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瓦刺軍發(fā)動進(jìn)攻,明軍全線崩潰。在混戰(zhàn)中,王振被明將樊忠以錘擊死,英宗被瓦剌軍俘虜,50多萬明軍死傷過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使明朝國力受到嚴(yán)重削弱,成為明朝由前期進(jìn)入中期的轉(zhuǎn)折點(diǎn)。
“馬市”三起三落
飽受戰(zhàn)爭之苦的明朝廷和瓦剌部落同樣都損失慘重,亟需休養(yǎng)生息。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大同總兵仇鸞與大臣嚴(yán)崇嵩秘密派人賄賂瓦刺首領(lǐng)俺答義子,以求重設(shè)馬市,平息戰(zhàn)爭。朝廷也撥出10萬兩白銀在大同鎮(zhèn)羌堡和宣化兩地再開馬市。
然而,不平等的委曲求全也注定了二次開啟“馬市”的短命。貿(mào)易中,俺答要用次等馬匹換取與優(yōu)等馬同樣的物品,得不到目的就經(jīng)常在大同開馬市時(shí)領(lǐng)兵攻打宣化,宣化開市則打大同。明朝廷一氣之下,第二年便再次關(guān)閉了馬市。
之后20年,明蒙邊境戰(zhàn)爭頻繁不斷,雙方疲憊不堪。尤其是蒙古方面,“各邊不許開市,氈裘不納夏熱,鍛布難得,戰(zhàn)火又使邊外野草燒盡,冬春牲畜餓死無 數(shù)。”一方急需布、絹等日用品,一方要補(bǔ)充馬匹、耕畜。在這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漢韃兩利”的原則使俺答明白了和平和友好的重要性,雙方促使“馬市”第 三次開啟。
第三次“馬市”依舊主要選擇在得勝堡,并同時(shí)在沿長城一線的新平堡、守口堡開設(shè)。瓦剌諸多部落分散在各個(gè)馬市進(jìn)行交易。此后50多年再無戰(zhàn)爭。
戰(zhàn)爭因“馬市”起,也由“馬市”而落。同樣,貿(mào)易和戰(zhàn)爭在此消彼長后找到了它的歸宿。
晉商足跡遍布邊關(guān)“馬市”
“凡是麻雀能飛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自古善商的晉人自然不會放過這邊關(guān)星羅棋布的“馬市”生意。就在明嘉靖年間戰(zhàn)爭頻繁之時(shí),正規(guī)的“馬市”關(guān)閉,但 商業(yè)需求依舊存在。長城沿線的蒙、漢人民依舊驅(qū)趕牲畜,帶著糧鹽茶帛等偷偷聚于長城一線,暗中交易。這其中,晉商的身影成為解決蒙族人民經(jīng)濟(jì)困難的中堅(jiān)力 量。
雖然得勝堡位于蒙漢邊陲,地勢偏遠(yuǎn),但“大同士馬甲天下”,得勝堡一直是山西商人活動的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成為漢族農(nóng)耕民族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的橋梁。
在明代中、后期的和平時(shí)期,以得勝堡馬市為中心,沿長城一線,有包括守口堡、殺虎口、鎮(zhèn)羌堡、新平堡等大大小小10多個(gè)貿(mào)易“馬市”。此時(shí),正是晉商在邊關(guān)的鼎盛時(shí)期。
據(jù)記載,晉商從中原地區(qū)大舉采購茶、綢緞和日用品,然后運(yùn)往大同諸多“馬市”,換回馬匹牛羊和牲畜制品又運(yùn)往中原南方各省。
可以說,晉商是在家門口做生意。
及至清代,晉商更是跨出長城,走串帳篷,送貨上門,甚至把貨物賒銷給蒙族群眾,生意越做越大。
作為明代全國最大的“馬市”之一的得勝堡“馬市”,交易旺季,店鋪林立,旌旗飄揚(yáng),商市戲場人頭攢動,其熱鬧景象是我們現(xiàn)代人也無法想象的。
另外,當(dāng)時(shí)的大同炭也成為晉商對蒙族貿(mào)易的主要物資。于謙在任山西巡撫首次巡查大同時(shí)寫道:“灶頭熾炭燒黃鼠,馬上彎弓射白狼。”準(zhǔn)確地概述了大同炭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成為貿(mào)易的主要物品。
正是這種集聚在邊關(guān)的貿(mào)易,使蒙漢民族展開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而晉商,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起著穿針引線的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馬市”凄美的愛情故事
那吉是瓦剌首領(lǐng)俺答第三子鐵背臺的獨(dú)子,那吉自幼喪父,由俺答妻子克哈屯一首撫養(yǎng)成人。俺答夫婦視那吉為掌上之珠,倍加疼愛。那吉與禹扯金自幼青梅竹馬 并私定終身。俺答為了聯(lián)合部落襖兒都司對抗明朝廷,遂要強(qiáng)行將禹扯金嫁給襖兒都司。那吉一氣之下,與禹扯金穿著漢服深夜出逃,跨過長城進(jìn)入得勝堡“馬市 ”。得知那吉逃婚后,大同總督王崇古收留了兩人,二人與王崇古的女兒又成了好朋友。
俺答之弟窺視首領(lǐng)之位,派刺客混入得勝堡欲刺殺那吉,以造成與明朝的戰(zhàn)爭。
那吉、禹扯金和王崇古女兒三人游華嚴(yán)寺時(shí),刺客箭射那吉,被王崇古女兒舍身救下。
王崇古忍受著失去愛女的痛苦,堅(jiān)持與俺答和談。
王崇古的行為感動了俺答首領(lǐng),雙方簽約談和。那吉也攜未婚妻戀戀不舍地回到部落,并發(fā)誓決不與明朝開戰(zhàn)。
從此,長城內(nèi)外迎來了持久的和平。兩個(gè)近百年相互仇視、兵戎相見、戰(zhàn)事不斷的民族一釋前嫌,為中華民族的大團(tuán)結(jié)創(chuàng)造了條件,從而使兩種文化在這里融會浸 潤,出現(xiàn)了“東自海臺,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里,無烽火警”的局面。在以后長達(dá)半個(gè)多世紀(jì)里,“沿邊曠土皆得耕牧”、人民“醉飽謳歌,婆娑忘返”,其功績彪 炳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