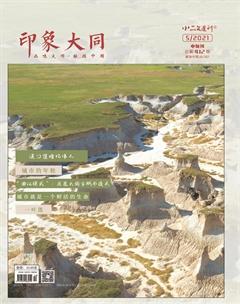古堡滄桑話當年
吳天有


一到助馬堡,我就被那歲月雕刻出來的堡門吸引住了,滿身的疲勞頓時變作振作起來的精神。稍事休息后,便急急地走進那歷史歲月里。
這是一座明代古堡,史書記載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歷史的風吹了幾百年,堡門上的磚雕仍然清晰可見。雖然有的地方殘破剝落,但仍然可以見證當年軍事要塞的雄壯。
城堡開有三門,即南門、東門和西門。現在,西門已被堵死。與其它地方城堡不同的是,在城堡的中間,也就是東西門之間,還設有一座城門,使整個城堡形成“日”字形結構。包括中間城門在內,四座城門中,有三座保持尚好。
走在助馬堡,你會發現,歷史發展的層次遞進感,在這里顯得尤為突出。這里有門前置有抱鼓石的明清院落,殘破中彰顯著當年的輝煌與顯赫。表明它的擁有者曾經非富即貴。也有民國時期的宅邸,像是專為歷史的過渡而設置的,顯示出那一時期北方民宅的特有風格。還有在歷史基礎上翻修的房舍,或者將舊的基礎徹底推翻,重新建置的房舍,經濟適用,門第感全無。當然,更多的是改革開放后在城堡外的新建房舍,透露著一種現代農家氣息。而街面上不知關閉于何時的老商鋪,則彰顯出古堡當年的繁華,這里曾經商旅云集,交通蒙漢。
還有兩件東西讓我駐足很久,就是位于西城路北街邊的兩座石旗桿。兩座旗桿,一座保持較好,一座剩有下半截。那座保持較好的旗桿呈圓形,上面曾雕有兩個旗斗,其中下部的一個已經脫落,上部的一個還在。依據材質和風格,應該是清代遺存。在清代,旗桿是功名的象征。科舉考試取得功名后,大戶人家就會在宗祠或宅院前樹立旗桿的。旗斗則表示考取功名的等級。鄉試中考取舉人的,旗桿上有一個旗斗,殿試中考取進士(第一名為狀元)的,旗桿上有兩個旗斗。由此,可以推斷,在助馬堡曾經有人考取過進士。
夏日的下午,街上人很少,只有零零散散的老人坐在墻蔭下拉家常,顯得十分靜逸。我獨自在街上走著、瀏覽著、欣賞著、查看著。也許是見慣了我這樣的旅行者,拉家常的老人隨便看看我,或者看也不看,繼續著他們的家常。這樣一個靜逸的山村小堡,有誰會想到,它曾經是一座軍堡呢?有誰會想到,這里曾經刀槍劍戟、戰馬嘶鳴,上演過一幕幕戰爭的大片呢?
歷史的狼煙早已散去,鐵銃、火炮早已成為古跡,刀槍劍戟也都去了博物館。居住在這里的人們,一代一代,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但那厚實的城門洞,像歷經滄桑的老者,似乎是在喋喋不休地向人們述說著當年的兵火歲月。那置有抱鼓石的院落,那被護窗板堵起來的店鋪,似乎也在向人們顯耀著當年的市井繁華。而那久久矗立不愿倒下的旗桿,似乎還要向人們展示古堡深厚的文化底蘊。
助馬堡筑于明嘉靖二十四年,為塞外五堡之一。明人王士琦所著《三云籌俎考》記載:“助馬堡,嘉靖二十四年土筑,萬歷元年磚包。本堡東接拒門等堡,西連保安所,謂外五堡也。堡東地勢平曠,虜易長驅,而馬頭山迤西,又邊在山內,無險可恃。”其規模及駐防范圍等,在同樣由明人楊時寧所撰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中記載:“周二里四分,高三丈八尺,原設守備官一員,內駐扎本路參將,除援兵外,守備所領見在旗軍六百三十四名,馬三十匹,分邊沿長二十里三分,邊墩二十五座,火路墩八座,市場一處。”與駐馬堡同期筑的還有鎮羌、拒墻、拒門三堡。《明世宗實錄》載:嘉靖二十五年二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等言,大同迤北二邊西自大同左衛馬頭山起,東至陽和柳溝門止,創鎮羌、助馬、拒墻、拒門四堡,乞設官兵防御。兵部議覆,得旨鎮羌、助馬二堡設守備官二員,拒墻、拒門二堡設操守官二員。”
但助馬堡為什么筑成“日”字形呢?這恐怕與“內駐扎本路參將”有關。這里的“本路”是指北西路。
為了便于設防和調動指揮,大同鎮的防守主要是按“路”分防的。嘉靖以前,分為東、中、西三路,各路設參將負責指揮。
嘉靖時期,由于蒙古吉囊部、俺答部特別是俺答部的頻繁侵擾,于十八年,在大同鎮城的正北修筑鎮邊、鎮川、宏賜、鎮虜、鎮河五堡,統稱宏賜五堡,并設參將對五堡的防御進行統一調動指揮,自此增設北路,北路參將駐宏賜堡。
嘉靖二十一年吉囊死,其部落為俺答所控制,勢力大增,從而加大了對大同鎮等地的侵擾。為應對俺答的頻繁侵擾,從嘉靖二十二年起,至嘉靖二十七年,又在大同北部緣邊增筑了包括助馬堡在內的許多軍堡,北路的防御范圍向東西兩個方向延長。這樣,北路的指揮就顯得鞭長莫及了。
為此,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請,將北路參將由宏賜堡移駐新筑的得勝堡,并改北路為北東路,同時將原駐應州的南路參將,移駐助馬堡,設北西路。這一條,在《明世宗實錄》里是這樣記載的:“移北路弘賜堡參將于得勝堡,為分守北東路,分轄鎮羌、拒墻、弘賜等八堡。移南路應州城參將于助馬堡,為分守北西路,分轄保安、拒門等七堡。”
增設參將府后,移駐助馬堡的兵力大增,這樣,原來做為守備的軍堡就難以容納新增的兵力,也就需要擴大軍堡的規模了。
傳統上,助馬堡人稱位于西面的城堡為堡城,東面的城堡為關城。可見,先筑的應該是西面的城堡,東面城堡是依西面的城堡而續筑的。實際上,助馬堡的西面緊臨一條沙溝,而東面卻是平展綿延的土地。所以,也只能向東擴展。助馬原堡開有東西二門,也符合當時守備堡的一般特征。續筑后,除繼續開東門外,又加開了南門。從而形成現在遺存下來的格局。
依據《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北西路分轄助馬、拒門、滅虜、威虜、寧虜、保安、破虜、云西、云岡九堡。其中,守備五堡,操守四堡。分邊東自北東路的拒墻堡,西至中路的破虎堡。期間長城(邊墻)七十七里,邊墩一百零三座,火路墩七十座。總統見在官軍五千九百六十九員,馬騾一千二百八十五匹。
這里,云西堡與云岡堡增設于嘉靖三十七年。高山城地面,在明代同樣也分屬北西路,但高山城做為大同鎮的右翼,不屬北西路管轄,而是直接受大同鎮鈐制。
做為北西路參將府,隆慶議和后,在助馬堡,還有一處馬市。其規模僅次于得勝堡馬市。期間,大批的蒙古馬匹、珍貴皮毛、玉石等從這里流向明朝內地,而明朝的絲綢、陶瓷、茶葉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由此進入蒙古。時有“金得勝,銀助馬”之說,可見當年商貿之繁盛。
到了清代,官方的馬市被取消了,但民間的貿易卻傳承了下來。其商旅云集的盛況,一直到清末和民國初年,才因交通的滯后而蕭條了下來……
在助馬堡,我多次陷入沉思。在每座堡門前,在置有抱鼓石的舊式庭院門前,在關閉已久的老店鋪前,在石旗桿前,我一次次駐足停頓。“黯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商旅車馬也早已成為過去。今天,助馬堡失去了曾經的紛亂、忙碌,歸于寂靜。
歷史,總在其進程中不斷取舍,一些地方成為關鍵所在,一些地方變得無關緊要;一些地方繁榮了,一些地方衰退了。這就是歷史的進程。
在來助馬堡的路上,我看到長城旅游專線正在修筑。我相信,隨著長城文化熱的欣起,隨著大同長城旅游路線的修設,助馬堡將會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并將會因成為旅游目的地之一而再次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