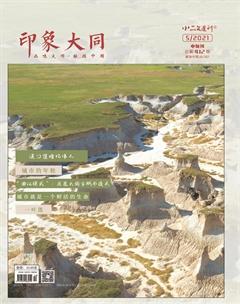盧宗孚縣長與大同



去年位于古城東南隅縣樓北街的一處古院落在重新修繕之后成為眾多網紅的“打卡”之地。因為民國時期時任大同縣縣長盧宗孚曾經在此居住,因此老大同人稱這個大院為 “縣長大院”。盧宗孚系浙江人,1934年至1936年任大同縣縣長。此人為人耿直、兩袖清風,他曾寫有一副特別出名的對聯:“興利除弊見義勇為者請進來,甘謁以私關說詞訟者滾出去”。在大同主政期間特別有建樹,大同的不少現存建筑就是在他任上修建的。
本期,小編就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篇由時任盧宗孚縣長的收發,李廣昌先生口述,劉存善先生記錄整理的一篇文章——《曾任大同縣長的盧宗孚》,來共同回顧盧縣長在大同期間的一些所作所為。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盧宗孚由晉城縣縣長調任大同縣縣長,我隨盧擔任收發。盧在任只有一年多,但有些事卻令人難以忘懷。
盧宗孚,字伯雄,浙江省海鹽縣瞰浦鎮人,浙江高等學校及北京大學畢業,北京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大約是民國八年,由北京政府分配來晉任事,那年他二十八歲。盧宗孚初到山西時,閻錫山正推行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天足、剪發(男人剪辮子),三事:種棉,造林、畜牧)乃委盧為政治實察員,視察五臺、崞縣、定襄三縣村政。
盧看到各地都在張貼“告諭”、“訓詞”,浪費錢財,收效不大,遂給閻上一條陳。內云:“條教張帖通衢,縉紳且怠于率讀,何論一般不識文字者,不如訂立明白易曉之村禁約數條有效。”閻閱后當即批示:閱盧某條陳,讀至條教張貼通衢…等語,本省長不禁汗流,多年辦理村政,可謂“白費力”三字。于是,他采納盧的意見,訂出簡明扼要的村禁約。從此,閻錫山對盧另眼看待,不久即擢升盧為絳縣知事。之后,盧曾任趙城和寧武縣知事、宣化和晉城縣縣長。他是舊社會一個公正廉明、不畏權勢、不徇私情的好官,且看他在大同縣的所作所為。
當時大同縣除縣警察局的警察外,縣政府還有數十名直屬警察。這幫人惡習很深,他們不辦事,而是雇用“狗腿子”替他們跑腿。他們一方面敲詐勒索,魚肉村民;一方面怠慢公庭,該傳的人故意不傳,該要的東西要不回來。對他們,群眾恨之入骨,官府們莫可奈何。
盧宗孚到任后,決心革除積弊,打算先從革除這些人入手。前任縣長嚴廷揚(后任省民政廳長)說辦不到,少惹是非,但盧卻執意進行,將舊警察分別考察,除留用仝相卿一人外,其余全部開除。然后公開招收高小畢業生充當警察,報名者160余人,擇優錄取40人。經過短期訓練,分為政務警察和司法警察兩個班。從此,史治一新,鄉民稱快。
大同當時的街道本來不寬,特別是東街大戶人家的臺階等多伸至街面,形成蛇形,行走不便。盧為整理市容,派人在街道兩旁畫出直線,進行整修。他自己首先帶頭出資10元,雇用一個姓馬的工頭帶人將關帝廟旗桿后移,然后責令各戶自行整修。
南街有閻錫山父親的一處宅院,門前雙斗旗桿超出線外,應該后移,閻家管事人請人說情。盧說:閻家不移,旁人怎么會移!他們自己如不動手,我就派人移動。管事人見盧不講情面,兩天后派人自動將旗桿后移。其他民戶原抱觀望態度,見閻家亦頂不住,遂相繼動工,整修街道順利完成。
大同錢糧每年只能收到三、四成,遠遠不能完成任務。主要原因是有地的人不納糧,沒有地的人納不起糧。原來舊社會的地主之流,有一種惡習,買窮人的地不帶錢糧。窮人把地賣了,但是錢糧還在自己名下。沒有地,生活都沒存保障,哪里還能納得起糧,所以每年的錢糧不能全部收齊。盧宗孚決心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他制訂表冊,派員持錢糧名冊,分頭到各村挨門逐戶驗地契,對糧冊,發現土地與錢糧不相符的,都予改正。歷時數月,全部改正,人民無不稱頌。
大同云岡石佛,管理不善,佛像被僧人勾結外國人盜賣者甚多。盧宗孚得悉后,派我帶兩名警察逐洞清點,發現失頭而為新跡者(風化者未計)共約5000左右,可見損失之嚴重。
盧得報后,派警察看管,才基本上剎住了破壞之風。下華嚴寺兩個侍女像,據說已被賣給日本人,價值兩萬銀元。盧登記管理云岡石佛,壞人聞風斂跡,盜賣下華嚴寺文物才未成為事實。
大同縣衙門的大堂等處,當時掛滿了牌匾,什么“愛民如子”呀,“明鏡高懸”呀,都是給過去在大同做過官的人歌功頌德的。其實,牌匾上寫的多數與本人的所做所為是兩回事。盧宗孚討厭這種做法。那時,大同縣政府里的辦公桌凳和床鋪等不敷應用,盧宗孚于是命令把所有的牌匾都摘下來,做了家俱。他這樣做,有些人看不慣,背地里難免有些閑言碎語,但知道他是個雷厲風行的人,也沒有敢出來公開反對。
他看到大同周圍樹木很少,便叫馬工頭買了五千斤小葉楊嫩枝,壓在護城河邊。后來都發芽成活,但是否成材,因為我們調離,就不知道了。
盧于1934年調任太原市政公所所長(相當今市長),1935年又就任到太原任山西禁煙督辦公所坐辦(閻為督辦,趙戴文為會辦,馬駿為襄辦)。抗日戰爭開始后,盧送家屬回鄉,滯留上海,以后未任公職,在一家私人公司擔任總務處長。解放后情況不明,據說于八十年代初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