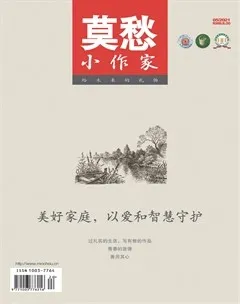且說“真性情”
? P敏
魯迅先生說過,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西諺也云:“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他們所強調的,都是不同閱歷、個性和思想認知能力的讀者的審美差異,及其對藝術的不同再造,而根本的原因則是《哈姆雷特》和《紅樓夢》中藝術形象的豐富性和深刻性。我由此想到的,則是創作《紅樓夢》和《哈姆雷特》的人,即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散文家)們,也是一個個閱歷、思辨、想象力和生命體驗形色各異的人。他們筆下的生活和人事,豈復還是本來面目?他們文本的風格和類型,他們抒情、敘事的方式,必然也各有千秋,異彩紛呈。他們的創作也將呈現為一個個“哈姆雷特”,欣賞或看待他們的創作,豈復還能以某些類型化的創作理念來規范或強求?
當然,這不等于就不能對文藝作品進行分析評判,相對的標準也對這種評判有著指導意義。不過它的前提是,你評價或欣賞的,首先是一部有著真正藝術價值的作品。遺憾的是,當今貌似雄渾博大、意象紛紜的散文世界里,雖然也佳作迭出、風生水起且不斷涌現個性化、精英化、文藝化的好作品,但給讀者的總體印象仍有點“雷聲大,雨點小”,浩如煙海的各類各式散文家和散文,泥沙俱下。平庸之作有如三月飛絮,迷亂心目,而內涵豐美、富有特色的佳作或藝術形象,卻相對不夠豐富。我們常見的是千部一腔或千人一面,陳陳相因或人云亦云,云山霧罩或不知所云,無病呻吟或故作高深。所以,至少我,漸漸地心生厭倦或迷惑,日益不愛讀“時文”而寧肯讀些史上有定評的經典佳作了。而其實,正因為這種厭倦,我亦更期盼多多邂逅那些有內涵、有個性的好散文。也正因為這種厭倦,我們才更要踏踏實實、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文章寫好。
新近,有個文友問我對散文寫作有什么高見。我回他曰:有一千個散文家,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創作上似無統一的高招可資所有人借鑒。至于我個人,更沒有高見,亦無秘訣,唯有八字心得:真誠為文,見性見情。
是的,我始終這么認識來著。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我欣賞和寫作散文的一個基本要求。雖然散文是一種最為自由寬泛和便利(以至常常被人誤解為好寫,實質上恰如詩歌一樣易寫難工)的文體,散文方家們也是高家莊的地道,各有各的招。但不論你藝術上是什么主義什么派,風格上是婉約還是豪放,類型上是先鋒實驗還是傳統的衛道者,拿出來的東西終得要有著鮮明個性和豐沛情感、真實自如而有些獨到體悟的。如果還要再說得具體一些,我想強調的是:好散文不能淪為任何工具或敲門磚,好散文不能人云亦云,空洞無物,更不能跟風撒嬌,裝瘋賣傻。好散文應是特立獨行者的歌吟,先天長著一雙慧眼;好散文的脊梁上插著風骨的標簽;好散文渾身洋溢著“真性情”。即:表露著真實的自我和心靈,吟詠著作者的個性和特識,蘊含著歌者的深情與大義。
具體而言,我對自己的期許是:
一、“真”:題材、立場和態度是真實而合乎邏輯的,經得起推敲和審詰的。但我并不強求機械的“真”,也不反對符合本質真實的串寫,或把過去的事、別人的事說成今天的事、自己的事等適度的虛構與組織。但不敢恭維某種任意過濾生活與“灑脫不羈”的虛構化。這樣的話,何如直接去寫小說或戲劇?而且,我更看重的是寫作者要有真實的自我和姿態。雖然這本是散文創作的應有之義,但許多人仍然痛詈當今文壇充斥“虛假平庸”之作,其因用魯迅的話說就是:“人們失去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最近,著名學者董健先生也強調:“真實是一切文藝的最高原則。真善美中,真是核心——沒有真的善是偽善,沒有真的美是虛假之美。追求真實就是追求真理。”我深以為然。一些作品虛飾自己或社會,張揚的不是真實的自我,而是任意拔高的自己或生活,甚至是作假的歷史。這在我看來尤不足取。
二、“性”:即無論是取材、敘述還是結構、語言等等,總得要見出點個性和特色來。散文的取材范圍十分廣泛,大千世界幾乎無不可寫,所以郁達夫說:“散文清淡易為,并且包括很廣,人間天上,草木蟲魚,無不可談。”“散文作為一種文體,一石之嶙,可以為文;一水之波,可以寫意;一花之瓣,可以破題,實在自由。”此言不差。但我們也不可因此而忽視魯迅先生“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箴規。現今很多散文,從選材開始就失之隨意或人云亦云、流于一般。我當過幾十年文學編輯,最多見的就是某種套路或曰模式:“我母親、我老公,我的七大姑和八大姨”“我旅游,我鄉愁,我那優雅、傲人的好日子”,或者便是“杯里乾坤大,茶中日月長”——一個從古到今就被各代文人泡得淡出鳥來的茶葉,高手自然仍有文章可做,但有些人動輒便連篇累牘、大書特書——這類題材和這愛那愛,本可謂文學永恒的主題。只是當我下筆時,如果沒有一丁點特別的感受和獨到的再發現,如果不是在寫命題作文或應景文章的話,我希望我會先問上自己一句:別人老嚼的饃,我真的還能嚼出滋味來嗎?它還有幾多新意和特色?它還能容下幾分我的真情實感和個性?如若不能或勉強,能不能把腦袋抬高些,或把目光放開點,試著讓自己有新的發現、新的表現方式或語韻,或則慷慨激昂、性情畢露上一回,或則“長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艱”一把?
想再強調的一點是,文章的“性”,首先也應該是真實的,本質的。人的性格和萬事萬物一樣,也有陰晴圓缺,亦是高下并存。光明與陰暗,高尚與卑劣,往往是一個人的兩個側面。寫作者無疑也應該力戒浮夸、虛飾而不事矯情。坦率地敞開真我,真誠地宣泄自性。這樣的作品才可能成為好作品。
三、“情”:這無須贅述。散文之所以被稱為美文,首先要有真實的情感和靈魂。散文特別強調個人體驗,抒寫親身經歷,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所以應有真摯而濃郁的情感和靈魂深度,才能感人。“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臺城柳是無情的,詩人韋莊卻是深情的。而這樣的情感在我看來,才是好散文不可或缺的血與魂。有情、無情,或是寡情、矯情,亦成了我區別散文優劣的重要標尺。無奈的是,我們見得多的,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反復強調的是境界:“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他相當科學地分析了“景”與“情”的關系和產生的各種現象;而薄情或寡味,意境也無從談起。王國維還強調,“景”與“情”要交融成一體。他認為這是上等的藝術境界,只有大詩人才能創造出這種“意與境渾”之境界。我們盡管不都是大詩人或大散文家,起碼也該做一個有感而發、情深意切的真文人吧?
說句題外話: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不斷發育、成長,網文和自媒體日益繁盛、發達。當下中國散文世界幾可謂已分成特征鮮明的兩個世界。一是以紙介報刊、出版業為代表的傳統主流世界,一是以浩如煙海的網文、博客及方興未艾的微博和公眾號為代表的另一世界,它們雖非主流,甚至不太為“文壇”所待見,卻正以見性見情、生龍活虎的姿態風起云涌、睥睨文壇,日益凌厲地橫掃讀者的視野、搶奪紙媒的受眾。雖然其中多有泥沙,但僅以我的視野而論,由于互聯網極大地開啟了民智,方便了表達,許多不見經傳的草根智者的佳作良篇也如野火春風,大有燎原之勢。他們沒有沾沾自喜、自以為高明的套路,不畏“婆婆”且很少自我禁忌,生就一副桀驁不馴、言所欲言且活潑潑、凈灑灑的“壞小子”脾氣,而個性和風骨,特色與新意,卻很青睞這些人。竊以為,主流媒體不妨更多投注或吸納其中的優良成分。
姜琍敏: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協理事,江蘇省散文學會會長。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