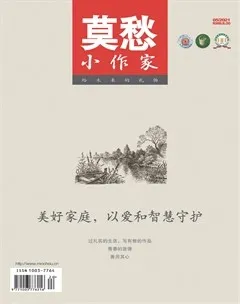他鄉的二月蘭
生活節奏越快,人的流動性越大,植物也概莫能外。我們要用很長時間,才會認識那些遷居的植物,要用更長久的歲月,等待它們蔚然成林。每遇河邊合抱不過來的大樹,心中頓生親切之感,它們與我一般,活得有了年歲。如與百歲以上的老樹相對,我就心生敬畏,天災、戰火、人禍,都不曾將之奈何。人老了不好看,但樹必須要有年齡。那些新植下不久的纖細苗木,須等到我鬢白齒落,才會有些端凝風姿。
伏地長成的花要簡單許多,它們是不需要年紀的物種,只關乎美。每年,它們都擁有一次嶄新的生與死。
第一次見到二月蘭,是數年前的五月初。在一處不高的山中,我被這種成片成片的紫色小花驚艷了。絢爛的紫色從山坡燒到谷底,襯著陽光,深深淺淺,像一場夢,也像一個謊言。
知道這種紫色小花名為“二月蘭”后,我便時常在身邊看見它,又在書里讀到它。
季羨林先生這樣寫:“二月蘭是一種常見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間。花形和顏色都沒有什么特異之處。如果只有一兩棵,在百花叢中,決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卻以多制勝,每到春天,和風一吹拂,便綻開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兩朵,幾朵。但是一轉眼,在一夜間,就能變成百朵,千朵,萬朵。大有凌駕百花之上的勢頭了。”季先生住在燕園,其中頗多二月蘭。季先生說,花開之勢有“大年”“小年”之分,小年花開零星,大年則烏泱泱滿坑滿谷。
我可以想象大年光景,燕園里紫白相間,花海隨風起浪。先生相伴的人,在其間行過;先生摯愛的貓,在花叢中玩耍。一個人和一種花,相伴幾十年,成了彼此生命的見證。
我與二月蘭只算新相識。這次出行,本是沖著跟它并居的梨花而去。連著七八年時間,我都去小城西南角的果園看花,今年換個地方賞梨花白。
頭一天風大雨急,到我們進入三臺山梨園時,枝頭白花零星,綠葉萌出小指長短,不復滿樹堆雪的驚艷。
好在,樹下還有大片二月蘭。
園子里,二月蘭隨處可見,或幾株或一叢。較之山中所見,這里的花挨挨擠擠,不算靈動,也沒有季先生筆下“凌駕百花之上的勢頭”,只安心化作一處布景,供人們在紫色花海前做各種擺拍。花叢中踩出小道,綠莖紫花零落成泥碾作塵。
二月蘭在這里是沉寂的,凝滯的。但它們會在一瞬間活泛起來,靈動起來。
風,是風。風手里有指揮棒,風一來,花們聽話地躬下腰,略做停留,再扭轉一圈,立起來,急速抖動花和葉,又偏向另一邊。一連串的動作活潑任性,我似乎看到它們腮邊的竊笑。殘余的梨花隨風飄逝,低處的二月蘭,跳舞時握緊小手,珍重著每一片花瓣。
“呼啦啦,呼啦啦”,到處都是它們的動靜,二月蘭恣肆地擺動身體。沒有它,只有它們,在風里攜手舞蹈,去承接陽光和風。在這異鄉,“它”必須壯大成“它們”,才可以經得住觀望打探。在喧鬧中萌芽、開花、結果,完成短短的一生。
二月蘭,還會憶及故鄉嗎?或者每一處土地都是它們的原鄉,植物們沒有鄉愁,只負責生長。
同樣在風里搖擺的,還有拔節的油菜花,貼地的蒲公英,一些白的、紫的、藍的不知名的野花。它們和我,和二月蘭一起,吹一樣的風,曬一樣的太陽。雖則生也有涯,長短不同,但同樣有生有死、有榮有衰。
他鄉與故鄉,又有什么區別?此刻的故鄉,更早前或許也是他鄉。就像人,在哪里安了家,哪怕腳底是沙礫巖石,也得扎下根去;就像花,種子撒到哪里,都會開出一樣的清麗美好。
這一天,我與二月蘭,像草原上的小王子和狐貍,但不是我馴服了它們,是我們都被風馴養。我與它們,一樣在風中凌亂又欣喜,調皮又慌張。等下一次見面時,我與二月蘭,就是真正的舊時相識。
程果兒:小學語文老師,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見于多家報刊。
編輯 ? ?沈不言 ?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