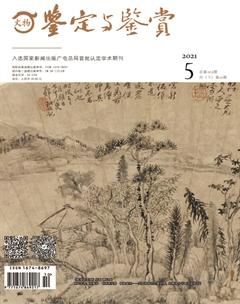從考古資料看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
魯雪艷



摘 要: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迅速,主要表現(xiàn)在農(nóng)業(yè)勞動力增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進步、農(nóng)田水利事業(yè)進一步發(fā)展、地主莊園經(jīng)濟興起四個方面。首先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與這一地區(qū)原有農(nóng)業(yè)基礎較好有關,其次得益于兩漢時期中央王朝注重邊郡管理、輕徭薄賦的政治措施,最后最為重要的則是牛耕技術的廣泛應用和鐵農(nóng)具的普及推廣。牛耕節(jié)省了人力,提高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效率,而冶鐵業(yè)的發(fā)展使鐵農(nóng)具得到了廣泛普及,兩者都為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關鍵詞: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
兩漢時期既是中國的大一統(tǒng)時期,也是社會經(jīng)濟繁榮發(fā)展、民族融合進程不斷加快的時代,更是中國古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時期,西南地區(qū)在漢中央王朝有計劃、有組織的持續(xù)開發(fā)中,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取得長足發(fā)展。秦漢時期蜀地已是國家糧倉,西漢初年蜀地生產(chǎn)的糧食就多次用于接濟周邊地區(qū)的饑荒。《漢書·食貨志》載:漢初“民失作業(yè),而大饑饉……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①體現(xiàn)這一時期農(nóng)業(yè)發(fā)展進步的鐵質農(nóng)具,以及體現(xià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進步的耕作俑、畫像磚等,在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等地的考古發(fā)掘中不斷被發(fā)現(xiàn),成為我們了解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進步難得的實物資料。下文通過對這一地區(qū)考古發(fā)掘出土相關文物進行分析,對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狀況做部分還原,一窺其貌。
1 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概況
秦統(tǒng)一巴蜀后持續(xù)將北方邊郡居民②及原六國舊貴族移民至巴蜀地區(qū),以鞏固其統(tǒng)治。兩漢時期災民③、流放罪人④、豪強⑤及部分自發(fā)的移民⑥又大批遷入巴蜀地區(qū),使巴蜀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勞動力大量增加。據(jù)《漢書·地理志》所載,僅成都一縣元始二年戶口已有7.6萬余,人口僅次于長安。大量北方移民的到來,增加農(nóng)業(yè)勞動人口的同時,也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
此外,東漢時期的軍屯也是兩漢時期巴蜀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1976年,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四開鄉(xiāng)發(fā)現(xiàn)了東漢末期至蜀漢時期的屯田遺址,見證了這一歷史史實⑦,20世紀80年代,在該鄉(xiāng)還發(fā)現(xiàn)了東漢初平三年(192)石表,其上的“百人以為常屯”⑧都表明東漢時期在四川地區(qū)實行了軍屯。
2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進步
2.1 牛耕的應用
秦漢時期牛耕技術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和進步。首先,從這一時期開始,制作的鐵犁犁鏵多呈三角形,鋒呈銳角,前高后低,斷面中部凸起,較漢以前的犁鏵寬大,既能破土又能翻轉泥土,解決了秦漢以前鐵犁只能破土不能翻轉泥土的問題,開啟了深耕細作的時代。
其次,犁駕結構日趨完善,考古資料表明這一時期的耕犁主要部件已經(jīng)齊全,其牽引方式在早期多為“二牛三人”,后期逐漸發(fā)展為效率更高的“二人二牛”,或“一人二牛”。四川木里藏族自治縣曾出土10多件鐵鏵和鑄有銘文的鐵鍤①,1987年,云南昭通城郊東漢墓中出土一塊畫像磚,磚面繪制雙角上翹的黃牛,牛與人之間有繩索相連,繩子一端系在牛鼻上,另一端牽于披氈男子之手,牛穿鼻系繩,當屬牛耕無疑。②
以上考古發(fā)掘成果表明漢代牛耕技術已在西南地區(qū)得到廣泛普及和運用。牛耕技術的使用大大節(jié)省了人力,極大地提高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
2.2 冶鐵技術的提高
整個西漢時期,巴蜀地區(qū)鐵器的使用進一步普及,且范圍進一步擴大,鐵農(nóng)具的插、鐮、铚、鋤、斧、犁鏵等已經(jīng)普遍使用。③
到了東漢時期,鐵器在整個巴蜀地區(qū)已經(jīng)全面普及。①1936年,云南昭通出土刻有“蜀郡”“成都”字樣鐵?;1958年,貴州赫章可樂鎮(zhèn)出土“武陽傳舍比二”銘文漢代鐵爐④;西南大學歷史博物館收藏了鑄有“蜀郡”二字的兩件鐵鍤(圖1),上述表明這一時期蜀漢地區(qū)冶鐵業(yè)已相當發(fā)達,不僅滿足供給本地區(qū)的需求,而且出口至云貴地區(qū)。云南曲靖珠街西漢墓出土的鐵斧⑤,更是表明當時這一地區(qū)的人民已掌握了生鐵鑄造工藝。考古發(fā)掘出土的鐵農(nóng)具遍及巴蜀地區(qū),現(xiàn)簡略列表(表1)。
據(jù)測定四川和云南出土西漢中期鐵農(nóng)具中有一部分屬“高碳鋼”,相比之前的“塊煉鋼”,其優(yōu)點是強度更大、硬度更高。⑥牛耕節(jié)省了人力,提高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而冶鐵業(yè)的發(fā)展使鐵農(nóng)具得到廣泛普及,兩者都為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2.3 分工明確,精耕細作
俑,是指古代用以陪葬的偶像,其中的農(nóng)耕俑是指表現(xiàn)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形象的陶俑,一般赤足或穿草鞋,手中持有鍤、鋤、鐮刀、鏟及鍘刀等農(nóng)具。
從東漢中期開始,西南地區(qū)漢墓中這種表現(xiàn)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形象的農(nóng)耕俑開始大量出現(xiàn),這既是漢代“事死如事生”喪葬觀念的具體體現(xiàn),也從另一個側面真實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狀況,也是對漢代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程的體現(xiàn)。不同的農(nóng)業(yè)勞作俑的類型適應于不同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⑧,是研究當時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珍貴實物資料,現(xiàn)列舉如下。
2.3.1 持鍤俑
鍤,最早流行于戰(zhàn)國時代的長江中游地區(qū),是漢代的一種起土、挖土工具,因此持鍤俑多表現(xià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程中起土、挖土的場景。重慶豐都鎮(zhèn)江沙包M28∶2曾出土一件持鍤俑(圖2),此俑頭戴笠帽,面露微笑,身穿右衽窄袖長衣,腳穿翅頭履,右手持鍤立于胸前,左手置于腰間。⑨由這件持鍤俑,可知圖1鑄有“蜀郡”二字的鐵鍤即是流傳下來鍤的實物。
2.3.2 持?俑
?,多為長條形,其功能應與今天農(nóng)村中使用的鐵?頭相似。因此持?俑多表現(xiàn)的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程中刨挖的場景。重慶豐都縣林口2號墓M2∶55曾出土一件持?俑(圖3),頭戴平上幘,面帶微笑,身穿窄袖束腰短衣,腳穿圓口靴,左手持箕,右手持?。①四川新都出土播種畫像(圖4)中左側一人手中所持之物應是這類農(nóng)具,畫面中共有三人,皆身著短衣,左側一人手中持?,躬身刨挖,右側二人同樣躬身下俯,似是在播種。
2.3.3 持棒俑
學者們多認為持棒俑表現(xiàn)的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中播種或薅秧的場景,如四川新都出土的畫像磚上②,一位播種者一手執(zhí)“點種棒”在農(nóng)田中插洞,另一手在點播谷種,表現(xiàn)的應該是播種的場景。
然而另一種觀點卻認為其也可用來表現(xiàn)水田的薅秧作業(yè)場景③,四川新都縣(今新都區(qū))就曾出土了一塊東漢薅秧畫像磚(圖5),左側兩位農(nóng)夫均柱棍支撐身體,雙腳交替著將雜草踩進泥里,學者多認為這是水田薅秧作業(yè)的場景。持棒俑有男俑和女俑之別,他們或站立或躬身,手持棒,呈勞作狀,三臺新德鄉(xiāng)東漢崖墓曾出土一件持棒俑(圖6),此俑頭帶樸頭,身上穿著束腰短衣,躬身而立,右手持短棒。④
2.3.4 持鐮俑
持鐮俑從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為收獲環(huán)節(jié)。《釋名·釋用器》:“鐮,廉也,體廉薄也。其所刈稍稍取之,又似廉者也。”⑤漢代的鐮多為鐵質,從漢代持鐮俑和畫像磚中持鐮人物的形態(tài)來看,自漢代以來鐮的形制變化并不大,并一直沿用至今。四川新都出土這塊薅秧畫像磚(圖5)的畫面共有四人,左側兩人正用腳薅秧,右側兩人正用鐮清理禾田,⑥手中所持的鐮與今日的鐮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
2.4 農(nóng)田水利事業(yè)進一步發(fā)展
早在秦朝時期已在成都平原興修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保障了成都平原農(nóng)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兩漢時期,巴蜀地區(qū)的水利工程事業(yè)進一步發(fā)展,農(nóng)田的灌溉用水得到了保障。如漢文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⑦2008年,在四川南充發(fā)掘出漢代“泰合尚渡”水井遺址群;⑧2013年,成都市郫縣(現(xiàn)郫都區(qū))波羅村遺址發(fā)現(xiàn)了漢代“溉田疇之渠”等。⑨上述發(fā)現(xiàn)都是這一時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用使用過的灌溉遺存。
此外,在今四川、重慶等地出土模型明器和畫像磚中都發(fā)現(xiàn)了反映東漢時期稻作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狀況。稻田都與水塘相連,大量的稻田都緊鄰著魚塘。⑩如四川新都出土采蓮畫像磚(圖7),二人駕小舟在蓮塘中采蓮,塘中還養(yǎng)有魚、蟹、鴨等。
2.5 地主莊園經(jīng)濟興起
早在西漢時期,官僚地主就已經(jīng)開始“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chǎn)業(yè),蓄其積委”③,逐漸形成了豪強地主這一階層。至東漢中后期,幾乎全國各地都出現(xiàn)了“豪人之室,連棟數(shù)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的豪族地主的莊園。④西南地區(qū)自東漢中后期開始以成都、重慶為中心的廣大區(qū)域大量出現(xiàn)反映莊園生活的模型明器,如城堡、樓房、畜圈、田疇等建筑模型,還有陶車、陶船等交通工具模型,還有表現(xiàn)家庭勞作的庖廚俑等,表明這一時期西南地區(qū)地主莊園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地主莊園經(jīng)濟的出現(xiàn)和高度發(fā)展客觀上促進了農(nóng)業(yè)、商業(yè)等方面的進步與發(fā)展,成為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環(huán)。墓葬中出土的各類陶俑和模型明器則是對一個個地主莊園的重現(xiàn)。⑤
3 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快速發(fā)展的原因分析
3.1 已有的農(nóng)業(yè)基礎
漢代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迅速發(fā)展,是建立在西南地區(qū)原有的農(nóng)業(yè)基礎上的。⑥早在先秦時期,巴蜀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已經(jīng)很高,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史料中尋找到痕跡,公元前308年,“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⑦此時距離秦滅巴蜀不過短短8年的時間,在8年時間里巴蜀地區(qū)能夠為秦軍提供如此眾多的糧食軍需,可見此時巴蜀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已十分可觀。
3.2 牛耕技術廣泛普及
羅開玉先生認為:“秦人早在春秋至戰(zhàn)國早、中期已推行牛耕,秦滅巴蜀后,牛耕必迅速傳入巴蜀。”⑧四川理縣佳山⑨、茂汶羌族自治縣石棺葬墓⑩都發(fā)掘出土了戰(zhàn)國晚期至秦末的鐵器,其中包括鍤、鐮、鋤等鐵質農(nóng)具。牛耕技術節(jié)省了人力,提高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而冶鐵業(yè)的發(fā)展使鐵農(nóng)具得到廣泛普及,兩者都為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3.3 有效的政治措施
兩漢政府都非常注重邊郡管理。西南地區(qū)幅員遼闊,各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地理環(huán)境都差異較大,兩漢政府為對這一地區(qū)實施有效管轄,采取了靈活多樣的管理方式,實現(xiàn)了郡縣鄉(xiāng)里制和屬國制。這種因地制宜、靈活多樣的管理方式穩(wěn)定了當?shù)氐纳鐣刃颍瑸檗r(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提供了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更有相對寬松的賦稅政策。漢初全國實行“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景帝時更是減少至三十稅一。輕徭薄賦的政策對西南地區(qū)的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產(chǎn)生了明顯的積極作用。
4 結論
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在秦及先秦時期原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基礎上,通過增加農(nóng)業(yè)勞動力、改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輕徭薄賦等措施,使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有了長足的發(fā)展,這些措施的實施既是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表現(xiàn),同時也是兩漢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取得長足發(fā)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地主莊園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造成了大量小農(nóng)的消失,使這部分人不得不依附于地主莊園,但不可否認的是地主莊園經(jīng)濟的發(fā)展從總體上來說,對地區(qū)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是有促進作用的。今天大量考古資料的發(fā)現(xiàn)和公布,為我們了解這一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現(xiàn)狀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使我們對這一時期西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狀況有了直觀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