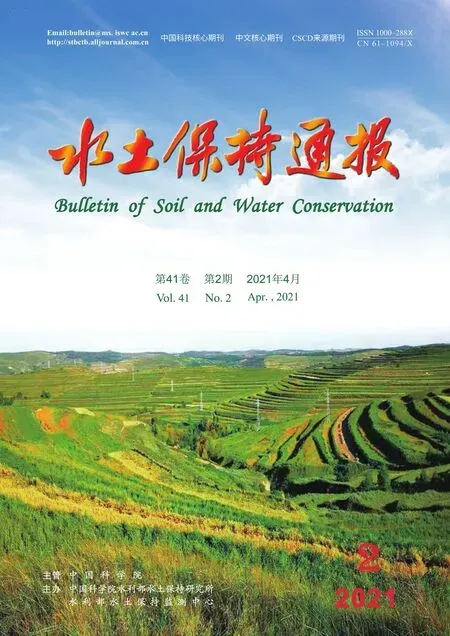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及障礙因子診斷
文高輝, 袁 泉, 趙 懿, 熊子昕, 張 漫
(1.湖南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2.地理空間大數據挖掘與應用湖南省重點實驗室, 湖南 長沙 410081)
耕地是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也是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重要物質基礎[1]。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口的持續增長及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人地矛盾日益尖銳,耕地生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耕地生態安全關乎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和社會穩定,維護耕地生態安全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實現鄉村振興、建設美麗鄉村的重要手段。因此,耕地生態安全問題受到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2-3]。近年來,學術界持續關注耕地生態安全問題,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國外學者主要關注耕地數量的變化,以及耕地利用活動對土壤、水文等的影響[4-5]。例如,Gibson等[6]分析了社會政治對伊拉克耕地面積變化的影響;Bateman等[7]研究了氣候變化對耕地利用的直接影響,以及誘發耕地利用變化對自然環境的間接影響。國內學者對耕地安全的研究主要關注耕地數量、質量和生態安全等方面。例如,鄧楚雄等[8]分析了長株潭城市群地區耕地數量時空變化及其驅動因素;劉洪彬和呂杰[9]基于農戶微觀視角分析了大城市郊區耕地土壤質量變化的驅動因素;鄭華偉等[10]采用集對分析法診斷了1999—2013年四川省耕地生態安全狀況。特別是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國內學者開始更加關注耕地生態安全問題。劉寶濤等[11]評價了2000—2016年吉林省耕地生態安全狀況;袁零和楊慶媛[12]評價了生態退化區甘肅省環縣2005—2016年耕地生態安全變化狀況;韓磊等[13]和馬年圣等[14]分別評價了云南和西藏地區耕地生態安全狀況并進行了預測;韓逸等[4]則以南方丘陵地區為研究區域,進一步分析了耕地生態安全的影響因素;也有學者從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等視角來探討區域耕地資源安全等問題[15]。在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方法選擇方面,主要采用熵值法[16]、物元分析法[2]、能值生態足跡模型[17]、隨機森林算法等[18]方法;耕地安全評價指標體系也主要是依據PSR[10,12-14,19]模型進行構建。PSR模型反映了人類活動對耕地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耕地生態系統狀態變化以及人類對于耕地生態系統狀態變化的響應三者之間的關系,但隨著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等方面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以及自然環境的自身特征和屬性的復雜性,PSR模型不能科學而準確地反映經濟、社會、自然之間的關系與存在的問題[20]。因此,本文在PSR模型基礎上加入驅動力因素與影響力因素,建立基于DPSIR模型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洞庭湖平原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但同時存在著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極大影響了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洞庭湖區域生態文明建設。湖南省啟動并實施3個“洞庭湖生態環境專項整治三年行動計劃”和洞庭湖水環境治理五大專項行動等系列工程。因此,研究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狀況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總體來講,耕地生態安全相關研究取得積極進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①現有研究大多分析某一研究區域耕地生態安全的時間規律,以縣級尺度為評價單元來揭示耕地生態安全狀況的空間格局的研究較少,而以縣(區、市)為單位的研究可更直觀地反映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狀況;②基于DPSIR模型對耕地生態安全評價的研究較少。基于此,本文以洞庭湖平原湖南省部分的21個縣(區、市)為研究區域,基于DPSIR模型構建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從縣域尺度采用改進的TOPSIS模型和障礙度模型評價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時空狀況,并診斷其障礙因子,以期為洞庭湖平原耕地合理利用和耕地污染治理提供參考依據。
1 研究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洞庭湖平原是以洞庭湖為中心的河湖沖積平原區,位于湖南省東北部和長江中游荊江以南,地跨湘、鄂兩省,北部與江漢平原相接,面積約1.88×104km2。本文以洞庭湖平原湖南省部分的21個縣(區、市)為研究區域。洞庭湖平原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是我國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研究區域21縣(區、市)糧食總產量由2007年的8.00×106t增至2017年的8.22×106t,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由2007年的701.19億元提高至2017年的1 330.15億元。洞庭湖平原區域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耕地生態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存在著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有研究表明,1991—2015年,洞庭湖TN和TP濃度呈顯著上升趨勢[21];根據統計年鑒數據匯總,研究區域21縣(區、市)農用化肥、農藥和農膜投入強度一直處于高位,單位農作物播種面積化肥、農藥和農膜使用量分別由2007年的1 131.56,15.64和10.38 kg/hm2變化至2017年的1 170.99,14.17和10.98 kg/hm2。因此,研究洞庭湖平原的耕地生態安全問題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1.2 數據來源
本文所需數據主要來源于《2008—2018年湖南省統計年鑒》《2008—2018年湖南省農村統計年鑒》,以及各縣(區/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
2 研究方法
2.1 利用DPSIR模型構建指標體系
耕地是一個自然、經濟、社會的經濟綜合體。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的準確性、科學性和合理性程度,會直接影響到評價結果的科學性以及提出對策的全面性。當前關于土地生態安全評價的模型有很多,其中歐洲環境署于1993年基于PSR和DSR框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模型具有綜合性強、邏輯清晰的優點,該模型還強調經濟方面對生態安全的影響和兩者之間的聯系,能更好地揭示人類的活動與生態之間的關系(圖1),現該模型在生態安全研究領域已得到廣泛應用[20-22]。故本文依據DPSIR模型構建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表1)。

圖1 “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概念模型

表1 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
(1) 驅動力(driving forces,D)是指引起耕地生態安全發生變化的潛在原因。選取人口密度、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化率、第三產業產值比重4個指標來反映人口變化和經濟社會發展對耕地生態安全的潛在驅動力。
(2) 壓力(pressure,P)是指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等因素對耕地生態安全的直接影響。選取化肥施用強度、農藥施用強度、地膜使用強度、農業自然災害成災比例4個指標來反映了農業污染和自然災害對耕地造成的壓力。
(3) 狀態(state,S)是指在驅動力和壓力的共同作用下,耕地生態安全的現實狀態。選取耕地墾殖率、有效灌溉率、人均耕地面積、人均糧食占有量、復種指數5個指標來反映耕地資源利用現狀。
(4) 影響(impact,I)是指耕地生態安全狀態發生變化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選取農民人均純收入、糧食單產2個指標來反映耕地資源利用帶來的經濟效益和農業生產效果。
(5) 響應(responses,R)是指為了實現耕地生態安全,人類所提出的應對措施和對策。選取中低產田改良比例、測土配方施肥比例、秸稈還田比例3個指標來反映農戶對耕地可持續利用所采取的措施。
本文依據DPSIR模型的內涵和相關文獻[1,19,23]對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安全趨勢進行綜合研判。耕地生態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含義及安全趨勢詳見表1。
2.2 改進的TOPSIS方法
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是一種有限方案、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1]。它依據評價指標的最優、最劣值分別構成正、負理想解,計算各評價目標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進而獲得各方案與理想解的貼近度,并進行排序,以此判斷方案的優劣[1]。鑒于此,本文采用TOPSIS模型來測算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耕地生態安全程度。結合本文的特點,在傳統的TOPSIS方法的基礎上進行如下改進: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決策矩陣的建立不是直接基于評價指標層,而是基于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這5個準則層。
2.2.1 指標數值標準化 由于各項指標性質不同,其單位和數量級也有一定差異,沒有可比性,因此要對指標數值標準化處理。本文采用極差標準化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將評價指標分為正向、負向2類指標,分別表示指標對耕地生態安全的影響是積極或者消極的,計算公式為:
正向指標:
rij=(xij-xjmin)/(xjmax-xjmin)
(1)
負向指標:
rij=(xjmax-xij)/(xjmax-xjmin)
(2)
式中:rij為標準化的指標值,其值在[0,1]區間;xij為第i個評價單元第j個指標的原始值;xjmax為評價指標j的最大值;xjmin為評價指標j的最小值。
2.2.2 權重的確定 鑒于熵權法客觀性較強,不受決策者主觀意識的影響,故采用熵權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
(3)
dj=1-ej
(4)
(5)
式中:wj為評價指標的權重;dj為信息冗余程度;ej為指標信息熵;m為評價年數;n為指標個數;zij為第t年第j個指標的指標值比例。
2.2.3 構建規范化決策矩陣 利用權重對各指標加權求和,建立規范化決策矩陣。
(6)
(7)
(8)
(9)
(10)
式中:KD為驅動力安全指數;KP為壓力安全指數;KS為狀態安全指數;KI為影響安全指數;KR為響應安全指數;t=1,2,3表示2007,2012,2017年;r和w的含義同上。
2.2.4 確定正負理想解 在決策矩陣中找出各指標的最優值為正理想解(K+),最劣值為負理想解(K-)。
K+={maxKif│f=1,2,…,5}
(11)
K-={maxKif│f=1,2,…,5}
(12)
式中:Kif為表示第i個評價單元的第f個安全指數;i=1,2,…;q(q為評價單元個數);f=1,2,…,5,分別表示為驅動力安全指數、壓力安全指數、狀態安全指數、影響安全指數、響應安全指數。
2.2.5 確定評價對象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D+和D-
(13)
(14)

2.2.6 計算評價對象與理想解的貼近度Ci:
(15)
式中:0≤Ci≤1,Ci越大,表明耕地生態安全程度越高。當Ci=0時,表示耕地生態安全程度最低;Ci=1時,表示耕地生態安全程度最高。
2.3 耕地生態安全等級標準
運用基于熵權的改進TOPSIS模型測算得到耕地生態安全程度(即貼近度)數值在0~1之間,分值越接近1表明耕地生態安全程度越高;分值越接近0,表明耕地生態安全程度越低。在參考相關文獻對生態安全的分級標準[1]的基礎上,并結合研究區域的實際情況,基于“均分原則”[23]將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程度劃分為5個等級,由低至高依次為非常危險、較危險、臨界狀態、較安全、非常安全(表2)。

表2 洞庭湖平原耕地安全評價分級標準
2.4 障礙度模型
在耕地生態安全評價的基礎上,本文采用障礙度模型對耕地生態安全狀況進行病理診斷,挖掘出影響耕地生態安全程度的障礙因子,為進一步提高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水平提供決策參考。障礙度模型主要采用因子貢獻度、指標偏離度、障礙度3個指標來分析診斷。因子貢獻度(Uj)為單項指標對總目標的權重(wj);指標偏離度(Ij)為單項指標與耕地生態安全的理想解為1的差距;障礙度(Yj,yj)分別為分類指標和單項指標對耕地生態安全的影響程度[24]。計算公式為:
(16)
式中:Ij=1-rj;wj為指標j的極差標準化值。
3 結果與分析
3.1 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時空分析
3.1.1 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時空規律 2007年10月印發的《湖南省“十一五”農業發展規劃》指出,湖南省耕地面積減少,地力下降,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嚴重老化,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生物災害仍然是農業發展的制約因素;該文件同時提出了增產增收、提高化肥農藥利用率等發展目標,提出了加強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主要任務。2012年4月印發的《湖南省“十二五”農業發展規劃》提出了主要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增強、資源綜合利用和循環使用水平不斷提高、農業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資源循環利用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進一步增強等發展目標。2016年8月印發的《湖南省“十三五”農業現代化發展規劃》指出,湖南省農業現代化發展仍然存在著農業結構性矛盾突出,抗御自然風險的能力較弱,農業經營管理水平不高,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農業發展支撐能力不強,農產品質量安全形勢嚴峻,農民持續增收困難等問題和挑戰,并據此提出了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大規模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加強農業產地環境治理,強化現代農業支撐體系等主要任務。從湖南省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3個時期農業發展規劃文件可以看出,湖南省日趨重視耕地保護,采取了推進農田基礎設施建設、高標準農建設、中低產田改造、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等重要舉措,農業生態環境得到了積極改善,但耕地生態安全形勢依然嚴峻。同時考慮到洞庭湖平原縣級層面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用2007年、2012年、2017年為研究時點來分析洞庭湖平原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3個時期初期的耕地生態安全空間格局。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整體呈下降趨勢。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平均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為0.796,2012年降至0.754,2017年進一步降至0.732(圖2)。基于ArcGIS工具,依均分原則將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各子系統安全指數指標分為5個等級。

圖2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變化趨勢
由圖3可知,洞庭湖區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較低的地區四散分布于研究區外圍。從縣域尺度來看,在3個研究時點,武陵區及岳陽樓區的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均明顯低于洞庭湖平原平均水平,這與它們均為地級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關系較大。其中,武陵區為常德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整體水平較低,且惡化趨勢明顯,從2007年的0.500降至2017年的0.236,現已成為全域內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最低地區,這與當地快速增長的人口及較高的城鎮化率密切相關;岳陽樓區為岳陽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其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在研究期內總體呈“先降后升”變化趨勢,由2002年的0.392降至2012年的0.279,此后岳陽樓區人地矛盾問題引起地方政府重視,政府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優化產業結構,2017年驅動力指數微幅提升至0.306。此外,2007—2017年,汨羅市、君山區、湘陰縣、阮江市、南縣等地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均出現降級,人地矛盾問題在洞庭湖平原日漸凸顯。

圖3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指數空間格局
3.1.2 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時空規律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整體呈“先降后升”變化趨勢。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平均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為0.824,2012年降至0.783,2017年升至0.832(圖2)。由圖4可知,洞庭湖平原北部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偏低,東部及南部地區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較高。從縣域尺度來看,在3個研究時點華容縣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均明顯低于洞庭湖平原平均水平。這與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地膜密切相關,資本密集型耕作方式不利于地力養護,直接影響耕地生態系統平衡。此外,2007—2012年,南縣、汨羅市、湘陰縣、鼎城區、澧縣、安鄉縣、臨澧縣等地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明顯下降,2012—2017年,漢壽縣、阮江市、臨澧縣、安鄉縣等地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顯著上升。洞庭湖平原整體耕地生態安全壓力狀態經歷了一個先惡化后改善的過程,這與國家和政府實施測土配方精準施肥、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有機肥推廣,以及農民養地意識的提高等密切相關。

圖4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壓力指數空間格局
3.1.3 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時空規律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相對穩定。2007,2012和2017年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平均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均為0.449(圖2)。由圖5可知,洞庭湖平原大部分縣(區、市)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處于0.4~0.6區間內。從縣域尺度來看,在3個研究時點,岳陽樓區、云溪區、武陵區等地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均低于洞庭湖平原平均水平。其中,岳陽樓區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在研究期內升幅明顯,由2007年的0.107提升至2017年的0.250,相對升幅達134%。這一變化特征與岳陽樓區驅動力安全指數的上升互為映照,說明當地政府在重新認識人地矛盾及耕地生態安全現狀后采取的一系列耕地生態安全改善措施開始顯現成效。此外,2007—2017年,安鄉縣、阮江市、鼎城區等地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明顯下降,桃源縣等地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顯著上升。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的空間分布差異與洞庭湖平原耕地數量、質量異質性密切相關。

圖5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狀態指數空間格局
3.1.4 耕地生態安全影響指數時空規律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影響指數整體呈上升趨勢。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平均耕地生態安全影響指數為0.201,2012年升至0.334,2017年升至0.558(圖2)。由圖6可知,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影響狀態得到顯著改善,各縣(區、市)表現出不同程度升幅,這一變化特征與近年來洞庭湖平原耕作條件改善、農戶耕地利用效率提高密切相關。從縣域尺度來看,在3個研究時點,望城區耕地生態安全影響指數明顯高于洞庭湖平原平均水平,在2007—2017年增幅最為顯著,相對增幅達222%。這一變化與望城撤縣設區、在政策扶持下實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密切相關,具體表現在糧食單產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顯著增長。
3.1.5 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時空規律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整體呈上升趨勢。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平均響應指數為0.128,2012年為0.154,2017年升至0.174(圖2)。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上升趨勢與政府及農戶耕地保護意識的提高密切相關,近年來,國家和湖南省高度重視洞庭湖平原的農地綜合整治(含中低產田改造)、測土配方施肥、秸稈還田等工作,為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狀況的改善創造了條件。由圖7可知,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空間分異日趨明顯。從縣域尺度來看,在3個研究時點,澧縣、華容縣、臨湘市、汨羅市等地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均呈“先升后降”變化趨勢,上述縣(區、市)在2007—2012年,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攀升至0.2~0.4區間內,在2012—2017年降級回跌。此外,在2012—2017年,沅江市、資陽區、岳陽縣、臨澧縣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顯著上升,平均增幅為86%。

圖7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響應指數空間格局
3.1.6 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時空規律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水平整體呈波動上升趨勢,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平均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為0.594,2012年為0.580,2017年為0.618,10 a內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升幅為3.98%(圖2)。由圖8可知,2007—2012年,多數縣(區、市)耕地生態安全水平處于安全臨界狀態;2012—2017年,阮江市、臨澧縣、桃源縣、漢壽縣、赫山區等地耕地生態安全程度從臨界狀態越至較安全及以上狀態。其中,阮江市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在2017年達0.809,實現非常安全狀態。而華容縣耕地生態安全程度在2007年處于非常危險狀態,2012年和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雖略有上升,但仍處于較危險狀態。

圖8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空間格局
3.2 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障礙因子診斷
3.2.1 準則層障礙因素 由表3可知,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準則層的障礙度各有不同且變化趨勢也有所不同。總體而言,阻礙耕地生態安全狀況改善的主要障礙因素為響應子系統,其次是壓力、狀態、驅動力和影響子系統。地方政府和農戶以往更多的是注重耕地的經濟產出,忽視了對耕地質量和健康的生態保護,近年來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以來,地方政府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生態保護的重要性,為改善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采取了諸如測土配方施肥等新型農業生產技術、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中低產田改造等舉措,但實施力度不夠大,仍需繼續加強。未來,為切實提高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水平,首要是加強并改進耕地生態安全響應舉措,加強洞庭湖平原“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整治,加大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同時要緩解耕地生態系統面臨的壓力,確保耕地長期處于一個健康可持續的利用狀態。

表3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態安全準則層指標障礙度 %
3.2.2 指標層障礙因子 由于評價指標較多,根據指標層障礙度大小,本文僅列出排序前50%的障礙因子(表4)。通過對比可得出,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障礙度排序前三的因子均為響應措施。障礙度最大因子均為中低產田改良比例(R1),其障礙度雖有所下降,但仍占最大比重。雖然黨和國家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視洞庭湖平原等糧食主產地區的土地綜合整治建設,投入了大量財政資金,但當前洞庭湖平原中低產田改良工程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力度仍應繼續加大,以提升農田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障礙度第2位的因子為秸稈還田比例(R3),國家大力提倡秸稈還田,這是由于秸稈還田具有培肥地力、改善土壤養分狀況、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減少因秸稈焚燒造成的大氣污染等好處。但倘若秸稈還田方式不當,也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因而很多農戶并未全面實施秸稈還田。對于秸稈還田措施,應加強技術指導與培訓,進而充分發揮秸稈還田的正向效應。障礙度第3位的因子為測土配方施肥比例(R2),當前測土配方施肥并未在洞庭湖平原全面開展,只有少部分地區實施了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可有效解決作物需肥與土壤供肥之間的矛盾,針對性地補充農作物所需的營養元素,提高肥料利用率,減少肥料流失帶來的農業面源污染。障礙度第4位的因子為農藥施用強度(P2),洞庭湖平原農藥施用量占全省總量的1/3,而耕地面積卻只占全省的1/4,農藥施用量過大,嚴重影響耕地生態安全。障礙度第5位的因子為地膜使用強度(P3),地膜使用是提高產量的重要手段,但隨著地膜使用年限的增加,殘留地膜回收率低,造成極大的污染。障礙度第6位的因子為化肥施用強度(P1),化肥使用過量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易造成土壤板結、地下水污染等。障礙度第7位的因子為農業自然災害成災比例(P4),可直接導致耕地質量下降或數量減少,防治自然災害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障礙度第8位的因子為復種指數(S5),當前洞庭湖平原平均復種指數為2.85,明顯高于湖南省平均復種指數2.11的水平,較高的復種指數通常具有較高的耕地利用效率,但洞庭湖平原的耕地也不能一直處于高壓利用狀態,應適時實行稻油、稻肥等輪作方式,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障礙度第9位的因子為人均耕地面積(S3),快速的城鎮化進程及人口增長不斷加劇洞庭湖平原人地矛盾,需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表4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指標層主要障礙因子及障礙度 %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 論
(1)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整體耕地生態安全水平處于臨界狀態,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在研究期內波動上升但增速緩慢。對于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各子系統,影響和響應子系統安全指數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趨勢,狀態子系統安全指數相對穩定,壓力子系統安全指數呈“先降后升”變化趨勢,而驅動力子系統安全指數呈下降趨勢。
(2) 洞庭湖平原各縣(區、市)耕地系統生態安全變化特征不一。多數縣(區、市)耕地生態安全水平在研究期內處于安全臨界狀態,阮江市為研究期內唯一實現非常安全狀態的地區。
(3) 從準則層來看,影響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程度的主要障礙因子集中在響應子系統。從指標層來看,中低產田改良比例、秸稈還田比例、測土配方施肥比例、農藥使用強度、地膜使用強度、化肥施用強度、農業自然災害成災比例、人均耕地面積等是制約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態安全的主要障礙因子。
4.2 建 議
(1) 大力實施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積極推進中低產田改良工程、高標準農田和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增加有效耕地面積,提高人均耕地面積,增強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升農田糧食綜合生產能力。
(2) 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大力實施減藥控肥行動,強化農藥殘留超標治理,全面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提高化肥農藥利用率,實現化肥農藥零增長;開展農作物秸稈、畜禽糞污資源化綜合利用,提高地膜回收率,降低地膜殘留量;大力推廣綠肥種植、增施有機肥等措施,提高耕地質量,進而實現農產品質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