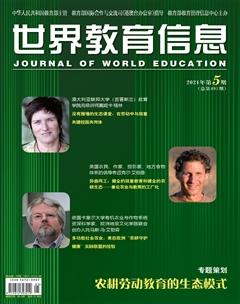多功能社會農業: 來自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的經驗
托馬斯·馮·艾勒森 蕭淑貞



作者簡介:托馬斯·馮·艾勒森(Thomas van Elsen),德國卡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Kassel)有機農業與作物系統資深科學家,歐洲地景文化學院(彼得拉克學院)(Petrarca-European Academy of Landscape Culture)聯合創始人、理事會委員。
摘? ?要:近年來,社會農業(social farming)的理念與實踐在歐洲得到了普遍的發展。現代農場逐漸帶有決策者所要求的農業多功能性的特點,通過提供社會服務,為農村地區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社會農業包含食物供給、社群包容、身心療養、教育培訓、提高生活質量等特征要素,“在農場學習”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文章將探討歐洲具有創新精神、注重社會廣泛參與的一些農場的實踐案例,討論歐洲多樣化的社會農業實踐形式。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成立于2004年,該社群若干工作組的科學家和實踐者為了促進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學習,共同發起了多場活動和研究項目。在歐洲范圍內,德國在這方面發展較為迅速,《關于社會農業附加值的維岑豪森意見》呼吁德國商業、管理、政治及其他公共領域的決策者大力推廣社會農業。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工作組評估歐洲迄今在社會農業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參訪歐洲其他國家的農業企業,強調質量保證所面臨的挑戰。
關鍵詞:社會農業 農業多功能性 質量保證 實踐聯盟
一、引言
2004年4月22至24日,在荷蘭福爾登市(Vorden)的一個農場舉行了以“農耕守護健康”(Farming for Health)為主題的國際會議。“農耕守護健康”這一倡議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學者和實踐者的參與。會議中的討論與分享使各位參與者對歐洲各國的社會農業實踐案例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荷蘭,有幾家全職機構致力于社會農業領域的研究和咨詢工作,他們對“農耕守護健康”倡議行動抱有樂觀態度。
不同國家及不同學科領域對“農耕守護健康”這一概念的解釋存在明顯差異。在會議論文的主題中,“園藝療愈”(gardening therapy)和“關懷農場”(care farm)是主要的議題,還有些主題涉及戒毒康復等治療方法。此外,還有關于“老年人”和“都市農耕”等主題的演講,但沒有提及“農場學校”(school farm)①這個概念。
相關理念很難被精確描述與解釋。一位來自英國的與會者指出,“農業”是一個存在歧義的概念,當今的農業意味著開發與利用土地。也有與會者指出,“社會農業”概念的提出是在社會層面豐富和重新定義“農業”概念的契機,不應該將農業視為生產適銷產品的過程。來自大多數國家的與會者參與了“關懷農場”的相關討論,這一概念在比利時法蘭德斯地區和荷蘭被稱作為“綠色關懷”(Green Care),不過與會者認為“綠色關懷”這個詞與農業的生產要素“差距甚遠”。顯然,為以“關懷”為主、農作為輔的一類活動下準確的定義十分困難。在農業企業(agricultural enterprises)則相反,它們將有特殊需求的群體視為需要額外完成的任務,即“綠色關懷”往往是農業企業的一種補充性活動,但不是其重點關注的工作內容。
大多數與會者具備農業科學或相關學科的教育背景。除了在農場工作的農民之外,還有土壤科學(soil science)、家畜行為學(domestic animal ethology)、農業經濟學(agricultural economics)和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等領域的專家。
自2004年以來,“農耕守護健康”大會在荷蘭瓦赫寧根(2005年)、挪威斯塔萬格(2006年)、比利時根特(2007年)、意大利比薩(2009年)等地區相繼召開,參會人數持續增加。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The European Community of Practice Farming for Health)已經發展成為歐洲跨學科實踐聯盟之一,建立了聯盟網站(www.farmingforhealth.org),逐漸吸納了社會農業領域更多的研究者和實踐者。這些參與者發起了一系列的網絡交流與互動活動,例如,挪威大學的比亞恩·布拉斯塔德(Bjarne Braastad)發起了“歐洲科技合作委員會—農業綠色關懷行動項目”(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ction Green Care in Agriculture),意大利比薩大學的弗朗西斯科·迪亞科沃(Francesco Di Iacovo)發起了“社會農業—多功能農場社會服務”(SoFar/Social Farming-social services of multifunctional farms)項目。
本文將探討以下問題:社會農業在德國和歐洲的現狀如何?重點發展的領域和面臨的主要障礙有哪些?此外,在社會農業、農耕守護健康、綠色關懷等方面,“在農場學習”(learning on the farm)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未來會有哪些機遇與挑戰?
二、歐洲眾國的社會農業實踐
(一)歐洲社會農業的多樣性
“社會農業”這一概念逐漸被一些農場所采用, 這些農場將政策制定者所要求的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付諸實踐,通過提供社會服務,為農村地區創造就業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豐富的多樣性:在荷蘭的一些“關懷農場”,農場工作人員獲得了接受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的資格,并能夠在家中辦公,進行客戶指導,對維持農場收入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法國山區的農場,兒童和殘障青少年可以在農場生活,體驗大自然和農耕,同時讓廢棄的文化景觀煥發新生。
社會農業的形式多樣,有些農業企業和商品菜園接納身心或精神存在障礙的人士;有些農場為社會弱勢群體、少年犯、學習障礙兒童、上癮者、長期失業者和活躍的退休市民們提供機會;此外,還有一些農場學校、農場幼兒園等。社會農業包含食物供給、社群包容、身心療養、教育培訓、提高生活質量等特征要素,“在農場學習”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的科學家和實踐者組織工作坊,促進各國在發展動態、研究項目和研究成果等方面的信息交流,支持互惠學習,并通過聯合行動和項目共建推進社會農業的進程。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開展了兩項研究活動:一是由歐洲協調各國被資助研究項目的平臺——歐洲科技合作委員會倡導的“綠色關懷”行動,二是歐盟“社會農業”(EU research project SoFar-Social Farming)項目。
“綠色關懷”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將“綠色關愛”行動融入農業,增進人們的身心健康、改善生活質量(Braastad et al ,2007)。該行動共設有三個平行的工作組。第一個工作組主要關注“綠色關懷”行動的積極影響,討論與該行動影響與作用相關的概念、理論及方法等。例如,綠色關懷如何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在生物學、醫學和健康科學等領域中,哪些實踐操作方法和研究方法與此相關?第二個工作組重點關注“綠色關懷”行動與經濟發展有關的主題,聚焦就社會農業進行的經濟學研究,其任務是在不同層次的多功能農業背景下,研究經濟和療愈的社會效應。第三個工作組主要討論與“綠色關懷”行動政策相關的問題,包括:如何將“綠色關懷”行動融入國家衛生保健系統?如何發展在地網絡?如何保障農村地區,特別是那些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并且保證各項方案在經濟方面可持續發展?
第二項研究活動是“社會農業”項目(2006—2008年)。來自意大利、荷蘭、德國、比利時、法國、斯洛文尼亞和愛爾蘭的20名科學家參與了這個項目。“社會農業”項目的總目標是改進社會農業的體制框架,加強研究與實踐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協調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經驗,以期為歐洲社會農業籌資政策提出建議。“社會農業”項目除了在所有參與國進行評價和基線調查外,在兩個國家戰略論壇上促進了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人員、政治決策者及從業人員之間的討論。相關調查結果已在布魯塞爾的兩個國際論壇上完成匯編和傳播,以便制定一項國際創新戰略,目前已經完成一本書的編寫及一個視聽文件的制作。
目前還沒有對關于各項倡議行動和社會農業企業總數進行的確切統計。據估計,大多數關懷農場集中在挪威(550家)、荷蘭(430家)、意大利(325家)等國家,德國的社會農場數量為150家。實際上,那些為殘障人士提供培訓的工作坊也應該被納入其中,因此,總數將超出當前的估算值。另外,對不同統計結果背后的衡量與統計標準也存在明顯差異。盡管如此,相關統計結果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特定國家的公眾對社會農業的認可度。在歐洲,社會農業不僅是農業、經濟等領域關注的話題,也為提高人們生活質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二)德國的社會農業現狀和前景
“社會農業”項目為人們了解德國社會農場的發展現狀提供了很好的窗口,同時該項目吸收并應用了在戰略論壇上與會者們提供的寶貴建議。“社會農業”項目組織的第一次公開會議以“社會農業附加價值”(Added value in social farming)為主題,于2007年10月在維岑豪森(Witzenhausen)舉行,由卡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Kassel)有機農業科學學院主辦。參會的各界人士表現出了較大的興趣,認為會議是交流與分享相關經驗的良好平臺。此前,在“社會農業”項目舉行的第一屆戰略論壇上,已經有人建議編制一份關于社會農業附加價值的意見書。
根據大會建議,社會農業附加價值的意見書的初稿于2007年12月起草完畢,并經歷了反復修改與完善的過程,在修改過程中相關工作人員多次向第一次戰略論壇的參會者提供報告草稿,征求意見和建議。在2008年4月舉行的第二屆戰略論壇上對該草稿進行了深入討論。它的英文最終版本(van Elsen & Kalisch,2008)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二屆“社會農業國際論壇”(2nd International SoFar Forum)上發布,引起了公眾極大的興趣。
在這份《關于社會農業附加價值維岑豪森意見書》(Witzenhausen position paper on the added value of social farming)中,作者呼吁商業、管理、政治及其他公共領域的決策者在德國推廣社會農業。意見的第一部分對社會農業多樣性的背景進行了分析,回顧了多功能農業在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在德國,很多農民和一些需要特殊照顧的兒童與青年及其父母對社會農業都抱有積極態度,很多療愈師和社會工作者也在為他們的客戶尋找適合療養的農場,但是他們都面臨著無解的法律障礙,還要面對各州職業素養不同的聯系人、贊助者和行政部門人員。獨立運營的農場學校則為了資金與生存掙扎,它們作為課外學習和體驗場所,拉近兒童與大自然的距離,增加兒童在動植物方面的知識,但這些功能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可。醫生和療愈師經常無法找到合適的農場,因而無法為病人提供在農村進行療愈的機會。有意愿接受這類請求的農場往往不具備專業照料的支持業務,缺乏可以促進社會農業發展的咨詢意見、專業支持、培訓和進修機會、制度支撐和籌資手段。意見書的第二部分提出并闡述了七個方面的要求:一是承認社會農業對整個社會的附加價值;二是在法律框架中建立透明度;三是促進社會農業相關經驗的溝通與交流;四是協調建立中心網絡,提供咨詢服務;五是資助培訓和進修、支持和輔導;六是支持社會農業的跨學科研究;七是支持歐洲國家間的合作。
該意見呼吁政治家、部委、科學家和公眾的廣泛認識,提高對社會農業服務的承認、支持和鼓勵,這些服務不應僅僅被視為農業企業的額外服務,還應被視為推動社會關懷的積極因素。
《關于社會農業附加價值維岑豪森意見書》為其他歐洲國家制定相應的意見提供了參照。2009年3月,在意大利摩德納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對此進行了討論。作為“綠色關懷”政策工作組的一部分,來自愛爾蘭、芬蘭、瑞士、法國、意大利、葡萄牙、德國和荷蘭的專家提出了歐洲宣言的建議和想法。兩個月后,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在比薩舉行國際會議, 與會者共同參與了宣言草案的修改。2009年10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亞的歐洲科技合作委員會會議上,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發布了《社會農業的附加價值歐盟宣言》(European Manifesto on the Added Value of Social Farming)。
三、社會農業背景下的農場學習
(一)青年教育:多功能社會農業的組成部分
社會農業及“在農場學習”與農業多功能性、文化景觀、生物多樣性和社會意識等概念密切相關,這些都被視為土地管理的潛在附加值。1996年,時任歐盟專員、來自奧地利的農民弗朗茲·費什勒(Franz Fischler)敦促他的同事們營造農耕景觀。直到現在,發展多功能農業一直是政治層面一再被提及的要求。弗朗茲·費什勒提出,“景觀保護一度被認為理所當然,不屬于經濟體系……很明顯,這種服務的價值和報酬必須高于過去的一般水平”(Fischler,1996)。2008年頒布的《國際農業報告》(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port)呼吁放棄以大規模生產和單一種植為目標的土地利用方式,提倡保護農村地區生物多樣性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更加經濟的方式(cf. Schimdtner & Dabbert,2009)。
由于社會農業在各國的發展存在差異,加上個體行為者有著不同的背景,對于“在農場學習”活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屬于社會農業,各界持有不同的觀點。羅伯特·赫爾曼諾夫斯基(Robert Hermanowski)多年來一直參與德國殘障人士講習班“綠色空間”(Green Spaces)的宣傳和咨詢工作,他強調了農場學校和殘障人士工作在籌資渠道方面的差異。然而,無論是在德國還是歐洲,人們堅持把農業中的學習、訓練和感官體驗視為社會農業的一部分,但是像“農場度假”(Farm holidays)等的活動,若不帶有教育目的,則不屬于社會農業。當然,這里的界限并非固定不變。
農場學校的目標是教育兒童和青年,且德國的農場學校已經初步體系化。其他國家農場學校的目的是在學生的戶外課程里設置一日郊游活動,在農園或提供戶外活動的農場開展寓教于樂的活動。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目前專門為青年設計,滿足青年需求并為他們提供農業生產體驗的農場僅存在于德國。
(二)農場學校發展文化景觀和自然景觀的潛力
為其兩年的研究項目“實用方法和自然保育:有機農場發展文化景觀的潛力”(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potential on organic farms for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由德國聯邦自然保育機構(Federal Agenc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資助。與傳統的生產企業相比,整合了更多社會和培訓元素的農場視野更寬闊,在維持和促進生物多樣性方面更好地發揮了作用(van Elsen et al, 2003)。本文選取了社會構成不同的若干農場案例,對其自然保育和農場教育舉措進行了分析。
(三)哈茲伯格農場學校
哈茲伯格農場位于靠近巴德索登—阿倫多爾夫(Bad Sooden-Allendorf)的奧伯里登(Oberrienden),農場擁有大約6公頃的耕地和14公頃的草地,采用生物活力農耕方式(biodynamic cultivation),在一些古老的果園草地種有櫻桃、蘋果和梨。在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指導下,學生、教師和家長在農場學習的過程中扮演了真正的農民,分成小組,參與飼養、擠奶、制作奶酪和黃油、烤面包、田間勞動、管理菜地、照料蜜蜂、烹飪等活動,并且學習如何種植食物、手工加工和健康飲食(參見www.hutzelberg.de)。這里的產品幾乎都是用來滿足學習班學生的需要。這家農場使學習者參與到食物種植和生產過程中,提高學習者對農耕價值的認識。
(四)古特·霍恩伯格農場的農場學校與工作坊
典型案例是“生態和農業基金會”(Ecology and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支持的古特·霍恩伯格農場(Gut Hohenberg)的“農場學校與工作坊”。該農場不希望簡單地“保護”或“恢復”當地的歷史景觀環境,而是試圖繼續開發該景觀。這個占地約30公頃的混合農場主要是以養殖哺乳牛、奶山羊、馬等草原農業類型為特色。在農場學校,兒童、青年和成年人都需要學習有機耕作的原則,在農場學校指導下工作,學習食物來自哪里。農場改造后,人們開始整理農場的閑置地,照管傳統的果園,重新開墾閑置的部分耕地。另一個重要活動是保護穿過農田的小水道,還開展了景觀研討工作坊和實地調查(Kruger and van Elsen, 2005)。
(五)全德國范圍的調查
以上案例顯示了農場在社會層面如何將社會參與和自然及景觀融為一體,這些農場在全德國引發了一項有關有機農場學校在自然和景觀保護方面潛力的調查。該調查主要關注農場學校對自然和景觀保護的貢獻、學習者在農場學習與工作時對此作出的貢獻、在他們參與活動期間社會農業話題扮演的角色、農場學校是否因為學生的參與而更加適合進行文化和自然景觀保護工作等內容。研究者共找到116所農場學校,并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有效問卷84份,占72.4%。問卷信息包括農場的結構、學習者的年齡段、學習者所從事的工作等。調查結果顯示,在農場學習的過程中,約93%的農場與學習者就社會農業相關話題進行了互動與交流,主要內容包括打理景觀,物種多樣性,生態循環,畜牧業,處理水、垃圾和殘留物。農場學校表示,學習者與教師在這方面的興趣都有明顯提高。近90%的農場學校推行自然及景觀保育措施。最常提到的是建造和照料樹籬、果園、草地、潮濕的棲息地、河道、湖泊和池塘。另外一些保護和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措施有:種植或維持稀有或本地品種的果樹種群、支持物種豐富的草原等。大約2/3的農場學校讓學習者體驗這類勞作,2/3的受訪者認為農場學校非常適合這類任務。因此,這些農場為自然和景觀保護以及提高兒童、青少年在這一領域的認識作出了重要貢獻。
(六)創新農場的案例研究
“社會農業”項目和“德國有機農場的社會農業”(Social farming on organic farms in Germany)項目都研究了其他社會農業的創新案例,包括那些參與培訓青年的案例。下面介紹三個農場:擁有一家農場幼兒園的丹維世農場(Hof Dannwisch);擁有一家療愈農場學校的施洛特農場(Schlüterhof)以及參與青年福利工作的豪澤農場(Hof Hauser)。
1.丹維世農場
早在1957年,這家農場就轉向生物活力農耕。在當時,就已經招募殘障青年參與農場工作。在之后的發展中,不斷拓寬業務,增加了各類社會工作,農場轉為社群所有,現由30人組成的社群共同經營。農場的目標包括為青年提供培訓以及讓殘障人士融入社會。該社群包括5個家庭及一些培訓生和兼職員工,需要照料116公頃土地、40頭帶小牛的奶牛、300只母雞和40頭育肥豬。農場還擁有一公頃的花園、1100平方米種植蔬菜和草藥的溫室、奶制品制作點、農場商店和農場箱服務。各種各樣的水果和需要大量手工勞動的區域為需要被照顧的人和小學生創造了勞作機會。大部分產品都在附近的漢堡市出售。
薩賓·格利(Sabine Gehle)從2004年開始在丹維世農場經營一家幼兒園(見圖1)。大約有15名年齡在3~7歲的兒童每周上5天幼兒園。基礎設施包括花園小屋、操場和堆肥廁所。幼兒園的教育理念則結合了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的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和森林學校(forest school)托兒所的元素。在農場里有一所幼兒園不僅意味著孩子們能與家畜和植物接觸,還意味著他們能夠與農民和農場社區密切接觸。幼兒園的兒童通過觀察和模仿大人的日常工作來參與勞動。例如,照看屬于自己的花園一角,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喂牛,等等。兒童通過唱歌、做游戲、講故事等來觀察與體驗生活,這里不需要人為編撰的教學材料或概念灌輸,只需要讓兒童融入到農場一年四季的生活和工作當中。
需要被照顧的人也被納入到園藝、加工和照顧家畜等各種工作中。農場每年與學校合作組織兩次為期兩周的工作體驗,在此期間,學習者承擔日常事務之外的任務,如景觀和林地項目、護理樹籬、細木工和建筑任務等。這些工作對農場有益,學習者也能夠學到實際的動手技能。
2.施洛特農場
呂內堡附近的文迪施—埃沃恩鎮(Wendisch-Evern)施洛特爾農場開辦了一所療愈學校。在這個農場,基于華德福教育理念,學校通過在大自然中的實際工作,為兒童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青年提供教育和生活經驗,這所正在發展中的療愈學校于2007年作為呂內堡魯道夫·斯坦納學校的一所特殊分校對外開放。目前,小學一至七年級共有38名學生,分為四個班,有多個年齡組,有時甚至是雙班上課。學校的目標是將規模進一步擴大到中學階段,計劃仍在擬訂中,目的是使青年能夠獲得職業資格。
農場由70公頃農田和40公頃林地組成,有牛圈、耕地和林地,還有專門為教育和治療而養殖的馬、羊和雞。這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真實農場,能夠給學習者提供與以往在書本或網絡中接觸到的農場完全不同的真實體驗。尤根·施洛特爾(Jurgen Schlüter)說:“我不想要一個玩具農場……我們想成為一所強調真實體驗的學校,讓學習者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來了解世界,讓他們卷起袖子說:‘我是一個農民”。農場勞動的特性,使學校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尤根·施洛特爾說:“這就是農場教育的獨特優勢——沉浸在能夠創造規則的活動之中”。農民的真實工作環境與工作內容對學生至關重要:“農民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可見的,是可以體驗的,他能履行他的所思所想……勞動是生活所必須,遵循了事物的本性。”
但對許多學生來說,學校并不是一個很容易實現的選擇。因存在個人行為問題、情感或社會交往問題或一些嚴重創傷性社會事件導致一些學生輟學的問題,有些甚至被貼上“不可教”的標簽。施洛特爾農場認為,這些孩子喜歡在農場學校生活和學習就是一種成功,有些孩子發現動物比人更容易接觸,他們會逐漸允許動物靠近自己,不再那么自閉。患有自閉癥的一位學習者,她與人交談或接觸存在困難,但當撫摸動物特別是奶牛時,會表現出快樂體驗。
須理性地完善由兒童和動物共同創造的協同效應,不要讓任何一方付出代價。因此,尤根·施洛特爾贊成制定行為規范、防護空間及特殊的預防措施。他說,“很明顯,我們不能擁有大型動物房舍。分散的房舍非常適合,牛不需要被拴起來,但學生必須能夠與單獨的動物接觸,而且必須限制學生人數。要為孩子和動物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有幾條規定:不能在動物附近爭吵,不得進入圍欄,禁止追逐、喊叫、打人等(van Elsen et al, 2010)。
3.豪澤爾農場
位于卡塞爾附近的沃爾夫根州的豪澤爾農場(Hof Hauser)是一個擁有五公頃耕地的小型農場。從2001年開始,兩位創始人和學員就開始在農場飼養自己的動物——馬、驢、奶山羊、綿羊、鵝、雞和鴨(見圖2),耕種菜園和草地,還在1.5公頃的林地上勞作,包括制作干葉飼料。這是一個提供“24小時照料”(24-hour care)的療愈型家庭社群,在青年公共福利的框架內,可以為9名學齡兒童和青少年服務。這家農業企業提供了具有多種勞動機會的居所,學習者不僅學習手工技能和種植相關的知識,還學習如何為他人和自己承擔責任。
該農場學校原本是一個磨坊,2001年被收購。從一開始,農場創始人就在尋求一種新的工作方式。他們的愿景包括在生活和工作的場景中通過農業勞動來培訓具有較強實踐技能的教育工作者。曼弗雷德·舒爾茨(Manfred Schulze)從事教師培訓工作多年,他認為“教師如果沒有實踐技能,不利于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農場的目標之一是提供定期的實踐培訓,給來自卡塞爾的師范生提供學習實際生活技能的機會。另一個目標是為沒有安全家庭環境的學習者提供場所,開展療愈教育。農場的名字便取自19世紀的卡斯帕·豪澤爾(Kaspar Hauser),也象征了開辦這所學校的誓愿。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農場作為一個“工作場所”,被照顧的兒童和青年應該與工作人員生活在一起,孩子們應該能夠在這里找到歸屬感,找回人生的希望和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勞動、手工農藝發揮著關鍵作用。
在豪澤爾農場,通過在農場的活動和幫忙,如烤面包、作曲、繪畫、手工、清理牛棚,學習者被引入基本的感官體驗和實際行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兒童和青年在“責任和知識的循序漸進”中得到了一種安全感,家庭結構中體現的勞動分工也有助于學習者找到自己的歸宿。年幼的兒童在做飯時主要做一些切菜之類的簡單活動,年長的兒童則利用他們獲得的經驗,按照食譜準備飯菜,也輔助更小的兒童完成任務。
豪澤爾農場的創辦人并不認為其僅僅是一個照顧兒童和提供活動的機構,他們認為農場更長遠的意義體現在為他們以后的生活做好準備,幫助學習者尋找生活前景和目標。“僅僅把兒童送到農場是不夠的,還需要考慮農夫或教育者應該具備什么樣的能力,在農場學習需要什么,農場學校應該給予學習者什么。”按照曼弗雷德·舒爾茲的說法,很多人不會將勞動當作學習和積累經驗的機會,而認為是來自外部強制的“羞辱個人意志”(humiliates the will)的過程,這一觀點在中歐文化中傳播了幾個世紀。通過各種各樣的手工藝活動和農業活動來形成“勞動文化”(working culture),可以指明一條替代的道路。那樣一來,古老的鄉村手工藝得以保留,并能長期聯合經營。
農場學校的工作原則還強調,勞動不會被當作是一種懲罰,學習者每天在農場幫忙也不會得到報酬。報酬被認為是一種外部激勵方式,這類學校鼓勵從內部激發工作的動機。農耕為教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教學工具,認為與人和動物的接觸能促進學習者責任感、社會技能和自信心的培養。
農場的大部分土地被用作草地和種植飼料,小樹林地也提供動物飼料、農場的柴火和建筑材料。其他區域用于生產供家庭食用的水果、漿果和蔬菜,還有一個小溫室。為了自給自足,農場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一些水果和蔬菜在收獲后被制成果汁、果醬等儲存食品;綿羊和山羊提供奶(特別是用于隨后加工成黃油和奶酪)、肉和羊毛;雞、鴨、鵝下蛋。在夏天,動物主要吃新鮮的草和葉子,冬天吃草地產出的干草和干樹葉。農耕活動有助于傳達生命價值,解釋生命周期和循環。
四、從社會農業到馬戲團農業
上文列舉的“在農場學習”的案例主要體現了社會對農場的預期和目標。在農場的各類體驗有助于學習者融入到農場的日常生活和活動中。農場里的生物、家畜和植物不會被用來滿足特定的學習需要,而是自然地受到尊重。上述案例中的農場都是有機經營的,以這種方式實現的“在農場學習”不僅向年輕一代傳達了真實的感官體驗,還增加了他們與社會的互動。
當然,也有一些對比鮮明的案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比如在一次會議上人們參觀了挪威西海岸的一個農場。這位農民很自豪,農場為孩子們建造了一個游樂園,谷倉被改造成帶有攀巖墻的大型稻草操場;可供飼養的動物有螞蟻、老鼠、小牛、豬、羊和馬等。在一個比較大的區域,安置了蹦床、微型拖拉機和其他游樂設備。農民把其中一幢房子出租給了一家有18個兒童的幼兒園。幼兒園的兒童可以到農場玩耍,但需要支付入場費。場地也被租出去舉辦聚會。一位與會者悄悄地說:“這種馬戲團式的農場(circus farming)與農耕沒有什么關系。”在這里,兒童接觸動物的方式確實應該被質疑,兒童將動物看作是被撫摸的對象,對它們在人類中所起的作用一無所知,人與動物的關系被簡單化為娛樂消費,動物被當作可供娛樂的玩偶和替代品(見圖3)。
五、展望未來: 質量保證的重任
社會農業的實踐具有經濟、就業、療愈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意義。出于這樣的原因,想要成為農場生活的一部分并與大自然一起工作的人們找到了社會農業企業。人們在與動物和植物接觸的過程中找到了有意義的工作,也可以作為體驗的機會。這種“使用”與僅僅把動物和植物作為“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的性質不同,后者的情況在現代農業中較為多見。盡管農場可以作為一個學習和積累經驗的場所,但其對待自然的方式會出現倫理問題,或在一個更基本的層面上,涉及到現代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在如何對待動物的文獻中已有深入探討,參見van Elsen,2008)。因此,質量保證成為基于農場的教育進一步發展的一項關鍵任務。這不應該通過規則、規章和一長串的標準來實現,而是應該通過深入探討“在農場學習”行為的深層動機、指導原則和理想來實現。
2009年10月,在維岑豪森召開的“德國社會農業的實踐和目標”(The practice and aims of social farming in Germany)會議為成立德國社會農業實踐聯盟奠定了基礎,這個團體的目標是交流思想和支持社會農業企業的發展。這一聯盟希望在德國發展各種社會農業,集成現有的網絡,如為殘障人士服務的“綠色空間”工作坊、農場學校協會網絡(BAGLOB)和與荷蘭模式一致的“我們共同創變”(together we can do something)協會,從而為農業保護就業的機會提供者和需要者創建一個中介。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其目的不是制度化,而是一個通過郵件列表將負責各種各樣項目的人聯系起來的非正式協會。
歐洲“農耕守護健康”實踐聯盟采用的這一理念和工作原則有助于協調和保持德國社會農業的創新空間,并確保其社會導向和高質量。“德國社會農業實踐聯盟” 的目的是使社會農業在德國受到重視,像歐洲其他國家已經做到的那樣:讓社會農業作為多功能農業的領域之一受到應有的重視,為一直出于孤立無援境地的先行者和農場提供更多互助交流的機會。在農場學校協會網絡框架內,一些農場的成功合作為“在農場學習”概念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起點。“在農場學習”是社會農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是農業未來能夠更加面向社會的重要議程。
注釋:
①德語Schulbauernhof直譯為“學校農場”,但本文所述社會農業以“農場為學習地點”為案例,并不是附屬于正規學校的農場,也不是指在農場開辦的全日制學校,而是農耕與教育功能的結合體,一般主業是農耕。為避免歧義,根據上下文的意思,有時譯作“農場學校”,有時譯作“農場學習”。
參考文獻(略)
版權信息:本文選自2010年首屆“農場即實踐學校學術倡議”的會議論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1st Conference of the Academic Initiative on Farms as Sites of Learning 2010)第二卷Academic foundation of learning on farms,編者是Johanna Schockem?觟hle。會議由費希塔大學(University of Vechta)與“農場學習聯盟”(BAGLOB)等聯合發起,于2010年6月11—12日在德國阿爾滕基興(Altenkrichen)舉行。英文原題為:Learning on farms between Social Farming and Circus Farming-experiences on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arming for Health。譯文已獲作者授權。
編輯 娜迪拉·阿不拉江? ?校對 呂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