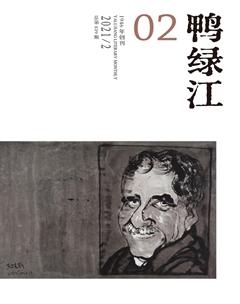“知識信仰”與“20世紀80年代愛情故事” (評論)
在198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賈平凹不無欣慰地提到:1978年,時年27歲的他在文學創作方面“總算摸出點門道了”,“稿子的采用率逐漸在提高”。①事實的確如此,盡管從1971年賈平凹就開始嘗試向報社投稿,并且在此后六七年間他陸續有各類作品在一些報刊發表,但他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影響并有了尋找屬于自己創作道路的自覺意識卻是在1978年——我之所以重提這一點,并非意在回顧他文學跋涉的早期歷程,而是要提請大家注意:賈平凹文學創作真正意義上的發端與“新時期文學”乃至“新時期”政治、思想和文化邏輯之間存在著一種較為明顯的同輻共振關系。賈平凹這樣回顧當時的自己:“我一面讀中外名著,一面讀社會的大書。我開始否定了我那些聲嘶力竭的詩作,否定了我一向自鳴得意的編故事的才能……我要在創作中尋找我自己的路,提出的口號是:打出潼關去!” ②——自我否定想必是有些痛苦的,然而,這對一位有巨大的文學野心并在未來也走得足夠長遠的重量級作家而言,又是極為必要和極其重要的。就此而言,發表于《鴨綠江》1979年第11期的短篇小說《丈夫》,似乎可以視為在經歷了明確的自我否定過程之后,賈平凹試圖調動自己的生活和知識積累并將其轉化為去尋找“自己的路”的作品,也是他逐步形成自己精神內質和藝術風格從而實現自我蛻變的一次創作實踐。
時隔三十多年再去重讀賈平凹這篇“少作”,很容易發現其中存在的諸如矛盾沖突的二元對立傾向、情節設置的人為安排痕跡、價值判斷后顯現出的單一化道德立場、情感與文辭表達的質直淺切等問題,尤其較之今日賈平凹的醇厚、沉穩、樸拙而老辣,其間差距自不可以道里計。但是,作為青年賈平凹自覺嘗試探索個人化文學路徑的產物之一,《丈夫》那飽滿豐富的細節刻畫、隱忍克制的敘事節奏推進、“編故事”色彩的淡化與“留白”與“詩意”等傳統美學意味的凸顯……這些已初步顯示出他在當時文壇的獨特性并讓他具有了較為明顯的辨識度;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作為“新時期文學”發生期的作品之一,與其所產生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脈絡之間天然具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深層糾葛。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文學與其所置身時代背景之間存在著格外緊密、深切的互動關聯,這已是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基本共識。可以說,當時幾乎每一篇作品都是對各類現實問題的直接呼應與想象性應對,也因此無可避免地被深深鏤刻上時代的印跡,即便是那些看似在講述個人愛恨情仇的作品,也無不被涂抹上強烈的歷史與時代寓言色彩——《丈夫》自然亦不例外。①這篇小說看似沿襲了在中國源遠流長且影響深遠的“才子落難、佳人相救”及“薄情郎背義負心始亂終棄”的舊有故事模式,但假如深入其敘事腠理并將“故事講述的時代”與“講述故事的時代”相互關聯,我們會發現,這篇看似意蘊單薄的短篇小說其實攜帶了許多啟示我們深度體察和解析20世紀80年代社會、思想及文化邏輯的信息符碼,比如男女主人公對待愛情和婚姻各自態度背后顯現出的“知識信仰”與階層/權力差序格局,比如男主人公遭遇到的愛情挫折及其“始亂終棄”行為折射出的社會分化與個體選擇遭遇的倫理困境,比如青年人堅韌決絕的個人奮斗與主體性建構的破滅……凡此種種無不向我們昭示,《丈夫》所講述的并不僅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愛情故事”,故事深層的復雜意蘊其實更值得注意,也有待我們進行更為深入的檢視和發掘。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洋溢著濃郁的知識崇拜氛圍的時代,弗朗西斯·培根那句“知識就是力量”的斷言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深入人心并逐步凝聚為時代的共同信條。這既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科學至上”理念在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性復歸,更是國人對“知識越多越反動”之類反智主義思想及其災難性后果進行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之后所建立起來的思想共識。毋庸置疑,這種對知識和文化的崇仰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現實與歷史意義。在當時,知識不僅被視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推動力量,更被“撥亂反正”后的國家政權作為建構其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價值柱石之一,基于此,“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才會相應地被確立為新時期的基本國策,并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后的現實與精神走向。②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氛圍之中,舉國上下很快建構起了一種指向明確、內涵清晰的知識信仰。經由國家政權有意識地詢喚、引領、灌輸與民眾的價值認同與主動參與,原本依托人類理性能力產生從而具有客觀、中立特質的“知識”由此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從而具有了甚為突出的意識形態屬性。自不待言,這自然也會發揮其作為意識形態既有的文化功能和實際效用,知識信仰迅速彌散、輻射于當時中國的現實及精神空間的各個層面與角落,并自然而然地參與到民眾的價值理形與精神圖景構造之中,進而有力地影響和制約著他們對自我人生道路乃至愛情、婚姻關系的抉擇。
從《丈夫》講述的人物愛情與婚姻故事之中,我們足以見其一斑。
小說的男主人公“丈夫”,是一名出身農民家庭而通過個人努力終于進入城市并成為一家大型工廠技術員的“鳳凰男”,同時也贏得了一位“高干女兒”的愛情,“相好了三年”。小說盡管沒有對此正面描述,但可以想象,這名農民之子之所以能夠獲得“高干女兒”的青睞并跨越巨大的階層鴻溝實現愛情逆襲,他真正能夠依恃的除了“人物又齊整”之類非決定性因素之外,最有力的支持性資源恐怕就是他“技術員”的身份及其作為“知識”現實化身的象征性資本。與“高干女兒”建立在這種相對脆弱的根基之上的愛情遭遇失敗之后,小說女主人公、工廠女工“她”主動走進他的生活世界,兩人也很快建立了婚戀關系。但耐人尋味的是,與高干女兒一樣,“她”對“丈夫”之所以傾心相愛,其最為核心的動力源泉其實同樣是來自他作為“技術員”(知識表征者)的身份。尤其是小說對二人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描述,更為醒目地彰顯出了在那個時代“知識者”對于知識匱乏者而言所具有的神秘魅力:
他們結婚了。他似乎沒有對她表現出多大的親熱,只是鉆研技術。但她高興,全部挑起了家務擔子:做飯,洗衣,買菜,拉煤,甚至月月定期把一定的錢寄給他鄉下的父母。每天晚上,忙完了一天家務,她就一聲不響地坐在那里看他在燈下一本一本看那些厚書,覺得自己是世上十分幸福的人。
透過小說設置的“燈下看書”這一頗具儀式感的家庭生活場景,我們會發現,“文化淺”的妻子或許始終都未曾也根本無從走進那名有能力“一本一本看那些厚書”的“技術員”丈夫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她僅僅是在外部對丈夫隔空凝望,已足以讓她感覺充實和幸福,當然,將自己凄冷、孤獨、畸形的婚姻家庭生活狀況與那些“雙雙對對,領著孩子看電影呀,逛公園呀”的“別人”的生活相互參照,尤其是面對自己“三四個月不回家”的丈夫與“幫女的做飯呀,洗衣呀,陪著老婆看電影,一把扇子整夜給她扇風”的“別人的丈夫”之間形成的強烈反差之時,“她”不可避免地也會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而感覺到失落與哀怨,但在“她”心目中,與那些實用卻庸常的“丈夫”們相比,自己正潛心于鉆研科研項目并作為知識化身的丈夫,無疑更為高大偉岸也更令她驕傲,因此,當女伴們將她的丈夫與“隔壁老張”之類的丈夫相比時,她才會“覺得是受了侮辱”,并有足夠的底氣起身而去并在心里說她們這些人“庸俗!”——所有這一切,無疑都來自“知識信仰”所提供的強大精神支撐。
但是,接下來要需追問的是:作為一種象征性精神資源的“知識信仰”,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是否強大到足以挑戰、撼動或者顛覆社會階層分化以及權力結構固化的社會現實?知識水平的提高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地位攀升,究竟能否為那些始終自強不息堅持奮斗甚至為此付出慘烈代價的青年人提供足夠堅實的價值和精神根基,并借此完成自我的主體性建構?知識的累積、提升與良知、德性的喪失是否又存在必然性的內在聯系?其實,這些問題在《丈夫》的情節架構和敘事脈絡中都已顯現端倪,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對“知識信仰”的有效祛魅和“知識神話”的自我拆解。
首先,小說的敘述告訴我們,“技術員”在被“高干女兒”無情拋棄和愛情理想由此破滅之后,他對階層分化的社會結構和自我的命運出身發出了尖銳的質疑和冷峻的拷問:
“為什么農民的兒子就不能娶高干的女兒?我為什么就是農民的兒子?”
她覺得可笑,卻拿寬心話勸他:
“階級社會嘛,什么人沒有呢?”
“高干,為什么就能成了高干?以前還不是和咱一樣嗎?”
“說這些有什么用呢?何必在一棵樹上吊死呢?”
與身為車間女工無知無識的“她”對階層分化和權力結構的無奈認可與心平氣和地接受不同,作為“知識者”的丈夫并沒有就此消弭心中由愛情失敗所激發的憤慨、不公甚至反而由此引燃了他強烈的報復心理,事實上,他后來之所以會冷酷無情地拋棄結發妻子,并試圖再次挑戰和掠取那些“高干女兒”的愛情,這恰恰是其最為強烈的原生精神動力。但問題在于,即便這個“農民的兒子”的確“經過奮斗,終于干出名堂來了”,他就必然能夠成功獲得一個“高干女兒”的愛情和一切嗎?退一步來說,即便他真的“挑戰成功”,他也僅僅是憑借自己的知識者和工程師身份征服了作為個體形態的一位“高干女兒”,但并不能對那些“高干女兒”依然會鄙視、冷落甚至根本無視千千萬萬“農民的兒子”的冰冷現實有任何改變,更不會對社會處處存在的階層分化和無比強大的權力結構有絲毫撼動,他所謂的“為普通的工人、農民爭這口氣”,充其量是一種主觀臆造因而極度虛妄的“精神勝利”而已!
其次,從小說中我們看到,就個人努力的現實目標而言,“丈夫”確實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他為此主動放棄了一個正常人應該享有的夫妻家庭生活,在“科研項目”攻關的最后階段,甚至“三四個月內沒時間回來了”;為了不“影響他的事業”,他幾乎用盡各種手段驅使妻子連續三次刮掉腹中的胎兒……以自身尤其是其妻子的巨大犧牲為代價,他主持的項目終于獲得了成功,他成為慶功會的絕對主角,并獲得物質獎勵,同時還被提拔為工程師。但是,他獲得的這些利益、榮耀以及現實身份地位的迅速提升,并不能為他提供安妥自己靈魂和身心的確定價值體系和堅實精神根基。他依然是階層社會中一個躁動不息的孤立因子,一個人生觀和理想信念錯位的虛無主義者,一個因社會位置不確定和信仰崩塌造就的人格不健全者。他野心勃勃、情緒偏激、心胸狹隘,胸中激蕩著強烈的攫取心和征服欲,因而在具備了一定的現實資本之后便開始著手對權貴階層的個體實施報復性掠奪和占有,然而他并不具備對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及其深層成因進行理性反思和徹底抗爭的意識和能力,反而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完全信服并主動投身其中,這其實在客觀上延續甚至強化了階層分化和權力通吃的不合理現實格局。這也讓他“為普通的工人、農民爭這口氣”的正義宣言顯示出了本質的蒼白無力及其內在的悖謬,他對“高干女兒”愛情的挑戰究其實僅僅是一種“跪著的造反”,這讓他看似勇敢、決絕甚至有些慘烈的抗爭留下的只是一個空洞、蒼涼而無望的姿勢,能夠自由掌控自我精神、意志及命運的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性建構更是無從談起。
最后,《丈夫》對作為被欺騙和傷害者的妻子人生悲劇的正面描述,為她涂抹上了濃重的悲情甚至苦情色彩,對“丈夫”形象的刻畫也顯示出了作者鮮明的道德批判立場。這其實體現了青年賈平凹在文學創作和思想價值理念方面的一些局限。實際上,這種將“知識者”與“薄情郎”一體化的人物設置,與早先的占據主導性的反智主義思想傾向分享的是同一套話語邏輯,只不過將“知識越多越反動”置換為“知識越多越沒良心”而已。但是,這種敘事倫理背后的意味才尤為值得注意:“知識者”與“良知缺失”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其實,這也是小說對“知識信仰”最有力的質疑和拆解力量之一。黃平曾經借用福柯的理論,將路遙《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指認為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利益主體“經濟人”①,在某種意義上,《丈夫》的男主人公身上具有同樣明顯的利益主體“經濟人”氣質。對知識的汲取和對科研的全身心投入讓他終于獲取了更多的現實與象征資本,但知識對他而言只是實現自身欲望和野心的手段,“工具理性”徹底壓倒了“價值理性”,對叢林法則的信奉驅使他精于利害算計并為了實現個人目標變得不擇手段,不惜成為一個冷酷、絕情、虛偽、殘忍的道德敗壞者。艱苦卓絕的努力付出使他成為一個“知識主體”,卻并未能夠讓他同時成長為一個“德性主體”——或許,這也是此類出身于社會底層而在階層固化的世界試圖通過個體努力實現命運轉折的青年人必然要面對的人生難題,也是他們不得不付出的慘痛代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大行其道的當前現實也提醒著我們: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不解決,這種“知識主體”和“德性主體”相互分裂的現象恐怕依然會存在下去。
整體而言,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很多重要的命題在這樣一個短篇小說中尚未能恐怕也不可能得以充分展開,但其講述的20世紀80年代愛情故事卻敏銳地觸及很多當時客觀存在甚至延續至今的社會、思想及文化癥候,這或許也是我們隔著三十多年的巨大時空界限依然對其進行重讀的實際意義所在。
【本欄責任編輯】? 洪? 波
作者簡介:
劉新鎖,山東濱州人,文學博士,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研究。山東省作協簽約評論家,在《文藝爭鳴》《讀書》《江蘇社會科學》《山東社會科學》《揚子江評論》等期刊發表論述3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等多項,研究成果曾獲得山東省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濟南市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