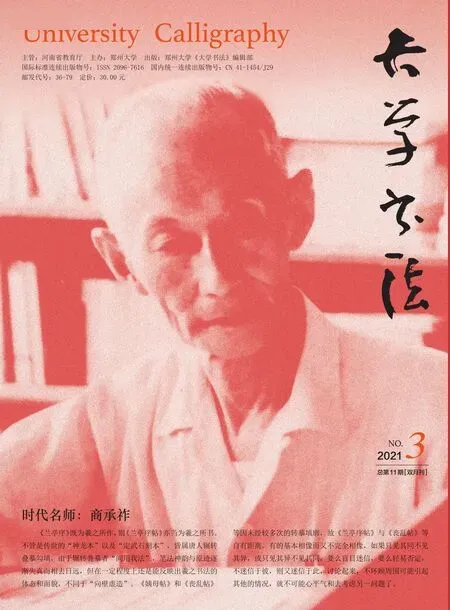高鳳翰隸書硯銘研究
——以《硯史》為例
⊙ 王群方
弁言
高鳳翰(1683—1749),字西園,號南村、南阜老人,山東萊州府膠州城三里河人。他天資聰慧,生于詩書之家,自幼便受到書畫的熏陶。其九歲即能作詩,十幾歲便開始作畫。高氏一生仕途不順,但平生好游歷四方,以詩文書畫會友,后辭官于揚州賣畫為生,后人將其列入“揚州八怪”。因其晚年右臂病廢,便用左手作藝,故而自號丁巳殘人、后尚左生。
“壯士愛寶刀,名士愛寶硯”[1],高鳳翰一生藏硯數(shù)千方,自稱“硯癖”,并從藏硯中選取佳品鐫刻銘跋,著成《硯史》。現(xiàn)存《硯史》是由王相、王曰申、吳熙載摹刻本,原本已佚(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不幸散佚)。陳志平先生《書學(xué)史料學(xué)》指出:“對于書家的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對其生平事跡的研究。主要弄清楚他的姓氏、籍貫、世系、生卒、行跡、創(chuàng)作、交游等。”[2]縱觀高鳳翰《硯史》,不乏其行跡、創(chuàng)作、交游等的記述,其中所蘊藏的史料非常豐富。
高氏所刻硯銘,多有對硯臺的來源、鑒藏的記述。如“此老坑上品,長如拓紙厚,其廣三之一而有奇,通體紫玉……此硯得之濟南朱篠園世兄”[3]。亦有其右手病廢后所銘第一方硯的記述:“夔龍池,南村并題……此余病痿后,左手書銘刻硯第一方也。”[4]除去史料價值、人文價值,高鳳翰極高的藝術(shù)手法,使得每一方硯臺都具備了藝術(shù)性,再加上王曰申傾其畢生所能進(jìn)行翻刻,較好地保存了高氏《硯史》的模樣,有很大的藝術(shù)價值。高氏對每一方硯都細(xì)心銘刻,匯集了其不同時期的不同書體,而其中隸書硯銘最為常見,為研究高鳳翰隸書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材料。
一、硯銘與《硯史》
蘇易簡《文房四譜》有云:“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5]故而古人稱“硯”亦為“研”,在《硯史》中,“硯”和“研”通用。硯臺對于古代文人而言至關(guān)重要,是文房四寶中最易保存、傳承者,蘇易簡云:“終身與俱者,唯硯而已。”所以硯臺對于古代文人而言不僅是研墨的器物,更是一生相伴的雅玩。一方硯臺的最大價值不在于其使用價值,而是背后所蘊含的人文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故而硯貴有銘,硯以銘傳。硯銘指鐫刻在硯上的文字,它是對硯的說明和補充,其主要內(nèi)容有紀(jì)年、題名、贊頌、箴戒、述志、抒情、鑒賞、饋贈等。
銘有名人題款的硯臺價值會大大提升,如高鳳翰曾獲贈得到一方陸游藏硯,硯側(cè)篆有“老學(xué)庵著書第二硯”數(shù)字和鈐印“陸”字。高鳳翰在《硯史》中將其記載:“此硯獲之京師,為余授業(yè)張巡臺夫子所賜……余攜歸滌視得后銘。出劍南,來燕市,歸我南村,文字喜。”[6]這方硯臺又先后被金農(nóng)、黃易收藏并銘文于上。一方宋硯歷經(jīng)數(shù)年,后經(jīng)數(shù)位名家題款收藏,使用價值對于這樣一方名硯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所具備的人文歷史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

大瀛海硯銘拓片 選自三聯(lián)書店《硯史箋釋》
高鳳翰《硯史》得以流傳,一方面是“硯癖”高鳳翰親力而為之。高鳳翰仿照《史記》表、書、本紀(jì)、世家、列傳的體例,并以史稱之。“據(jù)說最初是用彩墨拓印,并在模糊處用筆勾勒填補。原書設(shè)色淺淡,并配朱墨、藤黃、赭石等色,鈐以朱印,色澤古典可愛。若此書得以流傳,必定是一本令人愛不釋手、細(xì)細(xì)把玩的古書。”[7]另一方面,由于高氏死后,《硯史》下落不明,宿遷王相好古,多方搜索,終得之,并請王曰申、吳熙載摹刻編繪成冊。故而,王相等人功不可沒。王相(1789—1852),字惜庵,祖籍山東臨沂,南遷浙江秀水,后隱居宿遷。清代中晚期著名藏書家,家有百花萬卷草堂、池東書庫,藏高鳳翰《硯史》以及歷代別集善本40萬卷。王曰申(1788—1841),原名王應(yīng)綬,字子若,一作子卿,江蘇太倉諸生,王原祁玄孫。王原祁即“清初四王”之一,享譽畫壇,故王曰申工山水,且鐫刻極工,曾為萬承紀(jì)太守縮摹百二十漢碑于研背。惜王曰申僅活54載,沒有完成《硯史》摹本,僅完成其半。覽觀《硯史》,較后半段由吳熙載所用棗木翻刻而言,前半段由王曰申所摹極其細(xì)膩,可見王曰申用心之極。
王曰申《摹刻〈硯史〉手牘》中曾云:“摹研史研摹研史,我摹史研爾摹史。誰驚誰疑誰笑嗔?爾悲我嘆南村喜。萬人海里今惜間,兩生一死三癡子。”[8]據(jù)史料記載,王相出資供應(yīng)給王曰申摹刻《硯史》,但二人從未見面,僅通過書信來往。王相和王曰申訂交在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摹刻《硯史》也就從這時開始,而此時高鳳翰已逝世將近一百年。王相、王曰申用畢生的心血去摹刻南村老人《硯史》,從王曰申尺牘中可以得知王曰申摹刻《硯史》全過程。其對石材的選擇十分嚴(yán)苛,“青石性硬不稱手……如或不可,則仍用青石摹刻,但恐不精耳”[9];為了專心摹刻,謝絕一切應(yīng)酬,甚至“因硯史而暫與親友有形跡之疏”[10];南村氣韻古秀,并融各家之長,子若深知自己不如南村,但其能“謹(jǐn)守其制,竭力追摹,以求一絲不越”[11];再到后來子若病入膏肓仍以此為樂,“雖病重,樂此不疲,每刻石時,轉(zhuǎn)覺心平氣定”[12]。可見,摹刻《硯史》對王曰申而言已與生命融為一體,以至于王子若臨死前還向神靈禱告“愿假一年壽,畢《硯史》工而后死”。這種精神,源于王相對王曰申的賞識,更是三人橫跨一個世紀(jì)的相遇,使得“萬人海里今惜間,兩生一死三癡子”,最后讓《硯史》流傳至今,功德無量。
二、《硯史》隸書硯銘研究
高鳳翰《硯史》中收硯165方,所拓硯圖有112幅,所收硯中,大多為高氏自題硯銘,以隸書、行草為主。據(jù)統(tǒng)計所拓硯中有隸書題銘的硯臺多達(dá)數(shù)十方,數(shù)量相當(dāng)可觀,涵蓋高鳳翰不同時期的隸書風(fēng)格,為研究高鳳翰隸書提供了大量材料。高氏所藏硯臺種類繁多,有端硯、歙硯、澄泥硯、青州紅絲硯、瓦當(dāng)硯等,硯臺材質(zhì)不同會影響高鳳翰硯銘的風(fēng)格。需要指明的是,高鳳翰銘硯是篆、隸、楷、行兼?zhèn)涞模皇枪铝⒋嬖诘摹k`書題硯,行草或楷書落款,是高鳳翰銘硯的主要樣式。
研究高鳳翰《硯史》隸書硯銘,需要注意四個問題。其一,高鳳翰《硯史》中銘、跋、題、制,以及書體眾多,所以做以區(qū)別至關(guān)重要。王相按語皆為正楷,且后都有“惜庵”落款。王曰申皆以隸書記之,工整清秀,與高鳳翰隸書風(fēng)格相差很大,較為容易區(qū)分。其余跋文皆可根據(jù)落款進(jìn)行辨識。其二,《硯史》中所收錄的硯臺有許多是他人所贈,上有隸書硯銘,但并非高鳳翰所銘。如“春草堂世硯”,后有按語:“此硯先生未刻一字,亦未擬銘。”[13]其三,區(qū)別復(fù)題硯,如乾隆二年(1737),高鳳翰曾復(fù)題“紫潭硯”,“紫潭”隸書二字應(yīng)為先前所題,而非乾隆二年所題。這對研究高鳳翰隸書硯銘分期十分重要,不可忽視。其四,《硯史》摹本編排不甚系統(tǒng),較為凌亂。如《硯史》摹本第十四,其左方為高鳳翰早期的“冷云硯”,但右邊則為“田田硯”硯背銘文,而正面則錄在《硯史》摹本第九。兩硯均有隸書硯銘,風(fēng)格雖似,但并不是同一方硯臺,應(yīng)予以甄別。
(一)“八分初學(xué)自先生”
康熙五十九年(1720),高鳳翰銘“冷云硯”,是《硯史》中紀(jì)年最早的一方硯臺,硯銘云:“半硯冷云。蘧然行笈之寶。去冷僧,歸冷宮,吾不能不多爾之耐寒。南村戲作。庚子。”“半硯冷云”四字為隸書題銘,后為行草落款。此硯為高氏38歲所書,從題銘和落款中,能夠發(fā)現(xiàn)此時高鳳翰的書風(fēng)尚為清雅,隸書題銘有漢隸的特點,結(jié)字勻整,用筆方圓結(jié)合,溫文爾雅。目前所見高鳳翰的書畫作品中很難找到有紀(jì)年的隸書題款,而這一方“冷云硯”則恰好有庚子紀(jì)年,是對高氏早年隸書作品的補充。
高鳳翰隸書早年學(xué)畫家馮景夏。馮景夏(1663—1741),字樹仁(一作樹臣),號伯陽,浙江桐鄉(xiāng)人。為人精敏有氣略,好讀史書,工文章,善書畫。高鳳翰《鴻雪集》中有詩《再贈馮司寇公》云:“八分初學(xué)自先生。”[14]雍正十年(1732)高鳳翰得“級硯”,記云:“馮少司寇舊守膠西,余濫竽為門下士,每侍文?,輒比蘇門晁秦……如公之不忘舊契者,幾人哉?此硯為其戲酬潤筆,后方鑿宋式岰堂而未畢者半,公將命選善工完其制,而舁賜之,余請曰,‘層界若戺,有階之處,可勿鑿。’退而銘之以呈公閱。公稱善,為錫佳銘云。鳳翰記。”[15]由此記可知“級硯”由伯陽老人所授,后由高鳳翰銘之,高鳳翰曾求學(xué)于伯陽老人,受到先生的垂青與教誨,而這方“級硯”就是二人關(guān)系最好的見證。
(二)“起作墨池風(fēng)雨聲”
高鳳翰書法擅長楷書、隸書、行草和章草。“18世紀(jì)20年代以后的高鳳翰,以隸書為突破口,進(jìn)入了書壇的流行風(fēng)氣中,他的書法聲譽也首先來自隸書”[16],高鳳翰隸書聞名于世,主要是取法鄭簠。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江蘇上元人。來往于南京、揚州之間,于揚州聲名大噪。其隸書師法漢碑,后在隸書中加入草法,一變唐以來隸書板滯、方整特點,以草隸聞名于世。如黃惇先生所言,鄭簠是清代第一位純以隸書名世的書家,是清初前碑派的代表人物。其學(xué)生張在辛深得鄭簠真?zhèn)鳎⒂绊懥烁啉P翰。故而,我們從高鳳翰現(xiàn)存作品中可以看出,用鄭簠風(fēng)格創(chuàng)作、題畫、銘硯是非常常見的。

曼睩硯銘拓片 選自三聯(lián)書店《硯史箋釋》
楊翰《硯史》序中云:“鑿穿混沌老蛟怒,起作墨池風(fēng)雨聲。”[17]最能夠形容高鳳翰銘硯時意氣風(fēng)發(fā)的狀態(tài)。以乾隆二年(1737)為界限,前期隸書銘硯甚多,多達(dá)數(shù)十方,后期則寥寥數(shù)方。這一時期(1732—1737)高鳳翰隸書硯銘因受到取法淵源、硯材、審美理想等因素的影響,可以分為三種風(fēng)格:秀麗古雅、方拙渾樸、雄秀奇崛。

囊硯銘拓片 選自三聯(lián)書店《硯史箋釋》
其一,秀麗古雅的隸書硯銘是高鳳翰銘硯最常見的風(fēng)格,且不受硯材影響(石制硯和陶制硯皆有)。位置多見于硯背或硯首。如“曼睩硯”硯背:“涵采韜光,蘊精內(nèi)藏。與余目成守山房,文字盼睞生輝煌。雍正壬子銘于問政山堂,東海高鳳翰。”風(fēng)格秀麗古雅,用筆瘦硬勁挺,氣息高古典雅。硯名的由來,是因為硯臺左上方有鴝鵒(八哥)眼,睛凝如點漆,如青云薄雪,故而賜名“曼睩”。“涵采韜光,蘊精內(nèi)藏”的意蘊與秀麗古雅的隸書風(fēng)格相契合。南村老人將詩、書、硯三者高度融合,達(dá)到了一致的審美境界,令人嘆為觀止。再如雍正十一年(1733),高鳳翰銘“紫云硯”,以隸書銘:“亦柔亦堅,亦方亦圓,亦樸亦妍,亦人亦天。”這幾字銘于硯背,字形端莊,用筆平和細(xì)挺,章法緊密。猶如銘文所言,剛?cè)嵯酀⒎綀A結(jié)合,介于古樸與妍美之間,深得漢碑韻味。這主要源于高鳳翰鑿硯“天和”的審美理想,他曾有《鑿硯歌贈徐梅鄰》:“生為我鑿硯,我還為生歌,鑿石慎勿鑿天和。硯成一日三摩挲,生兮硯兮兩不磨。”[18]天作之合才是方好硯,才能達(dá)到“硯貴有銘,硯以銘傳”這一目的。這兩則硯銘均銘于硯背(硯底),這是因為“硯底有更多空間可供銘文呈現(xiàn),一般不影響硯的使用功能”[19]。位置見于硯首者,如“權(quán)輿硯”“菊潭硯”“夔龍池硯”等,高氏以古雅風(fēng)格銘之,是因為硯首這一位置十分醒目、位置有限,銘文不易過大。
高鳳翰是以鄭簠隸書風(fēng)格名世的,但為什么高鳳翰在銘硯時很少用鄭簠風(fēng)格呢?是否與他銘硯時的心理有關(guān)?這一時期的題畫隸書中多以鄭簠風(fēng)格為主,為什么硯銘中不常見?高鳳翰曾在《題自書草隸冊子》云:“眼底名家學(xué)不來,嶧山石鼓久塵埋。茂陵原上昔曾過,拾得沙中折股釵。”[20]可見在高氏眼中,鄭簠的草隸風(fēng)格依舊不抵經(jīng)典古雅的風(fēng)格。草隸是鄭簠將草書筆法運用到隸書書寫中,使得原本靜態(tài)的書體有了動勢,活潑可愛,但若將此銘于硯首,則會顯得不甚莊重。因為在高氏看來“凝于精神、煉其形,是為善成”。秀麗古雅的漢隸風(fēng)格是高氏取法漢隸的證明,高氏在《戲用頃刻帖法雙勾摹制〈西岳華山碑〉記》一文中云:“西岳華山碑,漢代法物,久去人間,苦覓窮搜,僅乃得之,所謂金石大業(yè),歷千百年而不易覯者,亦莫此若矣。余在揚州,從馬嶰谷[21]兄弟致此本,用前法貫以意而營造之,不旬日而古帖就,即真鑒古者有弗廢。”[22]高氏取法漢隸,主要得益于其訪碑活動,以及與揚州鹽商、收藏家的交游。縱觀高鳳翰傳世隸書作品,漢隸風(fēng)格的隸書于書于畫于印皆少見,但《硯史》中隸書硯銘秀麗古雅的漢隸風(fēng)格較為常見,這為我們研究高鳳翰隸書取法提供了新的材料。
其二,方拙渾樸的隸書硯銘,這種風(fēng)格的硯銘常見于拙樸古質(zhì)的澄泥硯和瓦當(dāng)硯中。高鳳翰的“因材作銘”與其制硯“天和”的審美理想相契合,使得硯銘與硯臺宛如天成。從高鳳翰與龔甘泉的書信中得知:“某素有硯癖,而不必其佳,但是斷石片瓦,皆堪入用。”在高氏眼中,對于硯材的選擇并沒有十分挑剔,對于斷石片瓦,高氏皆可銘之、藏之,這也體現(xiàn)了高氏拙樸自然的審美傾向。其次,方拙渾樸的書風(fēng)源于高氏的審美理想。從其詩文“大樸出錘煉,至文生自然”[23],“摩挲愛淳樸,刻畫妙家常”[24],“信哉巧者勞,不如拙者好”[25]等中得知,在高氏的審美理想中“樸”“拙”“自然”十分重要。這種審美理想不僅表現(xiàn)在對硯制和硯銘風(fēng)格的融合上,更體現(xiàn)在他對這類硯臺章法的處理上。如雍正十三年(1735),高鳳翰銘“囊硯”,銘曰:“括其口,便其腹。硯乎硯乎!其始有邊孝先之抱負(fù),而常誦金人之銘,以自撿束者乎?雍正乙卯為大令別駕公銘,南村弟高鳳翰。”此隸書硯銘依硯形而銘,章法別有趣味,結(jié)字方整,用筆渾厚,起筆多方筆,折角方圓結(jié)合,章法茂密,氣息渾樸。“泰州古澄泥硯”,據(jù)硯材而言,因為是澄泥的緣故,硯制本身已經(jīng)略顯斑駁,樸拙古質(zhì)。而其硯背銘文章法最有特色,高鳳翰解釋道:“銘語依硯背之皴圻處折旋回環(huán)書之,覽者按此索之,即得全意。”這種行款所展現(xiàn)的面貌與殘碑?dāng)囗偈窒嘞瘢ㄟ^對高鳳翰尺牘書信的整理,可以發(fā)現(xiàn)其對殘?zhí)f印、破硯斷箋等物件十分喜愛,這對高鳳翰制硯頗具影響。
其三,雄秀奇崛的隸書硯銘。這類硯銘在風(fēng)格上接近鄭簠隸書風(fēng)貌,用筆中糅入草法,不拘一格,雄秀奔放,是高氏的上乘之作。草隸更能表現(xiàn)書家的性情,藝術(shù)性更高。“以草法入隸書,作品更具飛動之勢力。”[26]此類風(fēng)格涵蓋了小字隸書和大字隸書。小字多用于對硯臺的題跋、鑒賞和注解。如硯史摹本第一“長樂未央硯”旁銘曰:“此硯為漢未央宮瓦頭,色黃紫如古玉,字畫渾穆,卻非后人擬造。今藏石城王虙草家。虙老酷貧,每以舉火為奇事,琴書半付米肆,而寶此硯如頭目。自云將攜之謁閻羅王,其癡可笑,亦可愛,可傳也。”
《硯史》中大字隸書不多見,出之,則必是精品,這類硯銘最能夠體現(xiàn)高鳳翰的性情,最具特色。如1735年,53歲的高鳳翰為自己《硯史》自題“墨香開國”四個隸書大字,恢宏大氣,酣暢淋漓,由此可見作者對自己隸書風(fēng)格極其自信。同年,在為祝枝庭作《文心別寄圖》冊中,高氏以隸書題款“文心別寄”四個大字,波挑飛揚,用筆不計工拙,與“墨香開國”風(fēng)格一致。同樣風(fēng)格的還有“大瀛海硯”,高鳳翰極愛此硯,硯臺正反皆有銘文。先生極為自信地用隸書銘“墨鄉(xiāng)磅礴,天空海闊”八個大字于硯堂,此硯不僅匯集了高氏隸書、行草、楷書,而且所書隸書大字風(fēng)格和詩文本身,相互映襯。此硯硯材巨大,鐵筆蒼老,雄厚奇崛。如王相所云:“在《硯史》中足以見先生妙筆之全者,亦此為第一也。”[27]而這種風(fēng)格更接近鄭簠風(fēng)格,少了些文雅靜氣,多了些靈動,沉著而兼飛舞,糅入了草法,用筆更接近篆法。這種恢宏大氣的大字在高鳳翰《硯史》中并不常見,但這是南村老人性情所現(xiàn)。南村老人曾自評道“卓哉高家翁,倜儻負(fù)奇氣”[28],也十分強調(diào)“譬如貌偉人,氣體尚雄貴。磅礴出謹(jǐn)嚴(yán),變色做游戲”[29],甚至也描述自己作大字隸書時“磨墨一石硯如盤,卷袖揚眉作大字”[30]的得意狀態(tài)。

泰州古澄泥硯銘拓片 選自三聯(lián)書店《硯史箋釋》

冷云硯銘拓片 選自三聯(lián)書店《硯史箋釋》
(三)“抵死仍將左手持”
據(jù)高鳳翰年譜可知,乾隆二年(1737)五月二十五日(丁巳),55歲的高鳳翰右手病廢,改號“丁巳殘人”,這對于他而言是右手作藝的終結(jié),但亦是藝術(shù)生涯的重生。面對毀滅性的打擊,他沒有退縮,而是用自己頑強的毅力和超群的智慧屹立于藝術(shù)之林。同年,他曾自題《左手卷》:“兩手其一能寫字,并奪其一可能之。怪渠僵直頑筋骨,抵死仍將左手持。”[31]右手病廢之后,他沒有放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其后半段藝術(shù)生涯中,他用左手作書、畫、印、硯,并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生”“拙”成了高鳳翰的藝術(shù)符號。
據(jù)統(tǒng)計,高鳳翰自丁巳之后制硯、銘硯僅20方,隸書題銘則更少。若以左手分期,無一方為高氏親自用隸書銘硯并刻之。《硯史》中第五十八“夔龍池”,是高鳳翰病痿后,左手銘刻的第一方硯臺。硯堂、硯背皆為行草,而且非常生拗澀拙,此時他并沒有熟練運用左手,故而略顯生澀。1737年2月高鳳翰曾復(fù)題“紫潭硯”,在硯堂處有“紫潭”隸書二字,但這應(yīng)為乾隆丙辰(1736)時期右手所書。丁巳二月于硯背下方僅用楷書復(fù)題記之。這方硯臺的翻摹為后來吳熙載棗木翻刻本,雖硯臺銘文十分清晰且完整,但硯臺硯堂和硯池的界限已經(jīng)十分模糊,可見棗木翻刻效果極差。“寶月輪硯”有隸書題銘:“云外天香,月中桂子,誰其伴者結(jié)歡喜,君家寒星與秋水。”觀此硯銘,無論從章法、結(jié)字還是點畫上看,都十分接近高鳳翰秀麗古雅的隸書面貌。但這并非為高鳳翰所題,而是其侄子書并刻之,有銘為證:“南阜老人為小玲瓏主人壽。命侄子汝澥書并刻。”[32]
除此之外,其于硯臺僅有一次隸書題銘,據(jù)硯銘所載,此硯雖為高鳳翰所銘,但非其所刻,而是其學(xué)生汪素所刻。不過依舊能看出是高氏“秀麗古雅”一路的風(fēng)格,且銘于硯首。由此可見,高鳳翰右手病痿之后極少用隸書銘硯。
結(jié)語
通過對高鳳翰《硯史》中隸書硯銘的整理,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八分初學(xué)自先生”(早期)、“起作墨池風(fēng)雨聲”(成熟時期)、“抵死仍將左手持”(晚期)。其中,因為早期僅有“冷云硯”一方,以及后期左手時期高鳳翰雖銘但未刻石,難以對風(fēng)格進(jìn)行劃分,所以本文主要是對成熟時期的隸書硯銘進(jìn)行風(fēng)格劃分。秀麗古雅的隸書風(fēng)格在所有硯制中最為常見,位置多見于硯背(硯底)或硯首,取法以漢隸清秀一路為主,源于高鳳翰“天和”的制硯理念和訪碑活動以及與收藏家的交游。方渾拙樸的隸書硯銘多見于澄泥硯、瓦硯等材質(zhì),這得益于硯材本身的拙樸古質(zhì),也源于高鳳翰“古”“拙”“自然”的審美理想。這類隸書硯銘不僅風(fēng)格古樸,其章法也變化莫測、耐人尋味。雄秀奇崛的硯銘風(fēng)格接近鄭簠草隸,飛動跳躍,恢宏大氣。主要有大字和小字兩種:大字見于高鳳翰為《硯史》題款和自己得意的大硯之中,最為精彩;小字隸書多為硯臺旁邊的題注和跋文,多是對硯臺形制、來源、品性的鑒賞等,書風(fēng)更為自由多變,與同時期題畫隸書風(fēng)格一致。
注釋:
[1]高鳳翰.擊林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24.
[2]陳志平.書學(xué)史料學(xué)[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0:35.
[3]高鳳翰.硯史摹本銘跋印識[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69.
[4]高鳳翰.硯史摹本銘跋印識[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171.
[5]蘇易簡.文房四譜[M].孫洪偉,譯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20:183.
[6]高鳳翰.硯史箋釋[M].王相,重摹,田濤,崔世箎,釋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40.
[7]高鳳翰.硯史箋釋[M].王相,重摹,田濤、崔世箎,釋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40.
[8]王曰申.摹刻硯史手牘[M].畢斐,校點.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61.
[9]王曰申.摹刻硯史手牘[M].畢斐,校點.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13—14.
[10]王曰申.摹刻硯史手牘[M].畢斐,校點.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66.
[11]王曰申.摹刻硯史手牘[M].畢斐,校點.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68.
[12]王曰申.摹刻硯史手牘[M].畢斐,校點.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111.
[13]高鳳翰.硯史箋釋[M].王相,重摹,田濤,崔世箎,釋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48.
[14]高鳳翰.鴻雪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228.
[15]高鳳翰.硯史箋釋[M].王相,重摹,田濤,崔世箎,釋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87.
[16]姜棟.高鳳翰書法的審美追求[J].中國書法,2012(09):182.
[17]高鳳翰.硯史箋釋[M].王相,重摹,田濤,崔世箎,釋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322
[18]高鳳翰.湖海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51.
[19]劉鵬.硯銘章法述略[J].書法,2020(05):190.
[20]高鳳翰.鴻雪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167.
[21]馬曰琯(1687—1755),字秋玉,號嶰谷,安徽祁門人,后遷入江蘇揚州。清代著名鹽商、藏家,酷愛古籍,見孤本、珍本、秘本皆重價購買。其收藏極富,書畫、碑版收藏甲于一方,與高鳳翰等人交好。
[22]高鳳翰.高鳳翰文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37.
[23]高鳳翰.鴻雪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191.
[24]高鳳翰.鴻雪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207.
[25]高鳳翰.湖海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82.
[26]張龍慧.楊峴書法研究[J].大學(xué)書法,2020(04):88.
[27]高鳳翰.硯史箋釋[M].王相,重摹,田濤,崔世箎,釋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322.
[28]高鳳翰.鴻雪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272.
[29]高鳳翰.湖海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91.
[30]高鳳翰.鴻雪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157.
[31]高鳳翰.鴻雪集[G]//劉才棟.高鳳翰全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265.
[32]高鳳翰.硯史箋釋[M].王相,重摹,田濤,崔世箎,釋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