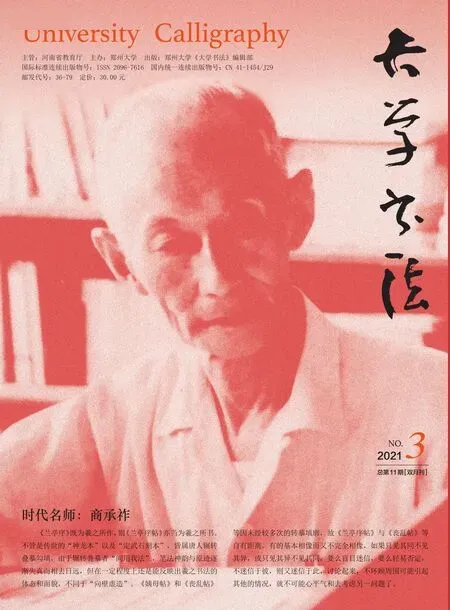論當代書壇的矛盾現象
⊙ 楊曉輝
當代書壇伴隨我國社會文化的繁榮和書法教育的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可以說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由此,當代書壇也出現諸多矛盾現象,這些矛盾現象可以說既是當代書法藝術發展中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也是每位書法藝術工作者不能回避并亟須做出理性選擇的問題。
一、書法概念認知中的矛盾
首先,關于書法概念及其本質的認知問題。這一問題在當代書學界已不是新的話題,雖然討論和研究不斷,但對其爭議也不斷,可以說至今也尚無定論。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書壇就曾有過關于書法本質問題的大討論。書法理論界以劉綱紀、姜澄清、金學智等理論家為代表,圍繞書法的本質問題展開了大討論。當代中國書法的大發展也是在這場書法美學大討論中逐步展開的,其影響直至今天,有學者指出:“這場關于書法本體的討論,時至今日來看其結果是不了了之,自然也沒有得出什么令人誠服的結論。”[1]
在書法概念認知問題的討論中,主要矛盾應該說是圍繞書法是“藝術與非藝術”問題產生的。如主張書法是藝術的學者認為:書法是漢字書寫的藝術。書法是用毛筆書寫出來,能夠成功表現書法家的形式美意識以及精神世界中的性格、氣質、意志、品德、情感等內容的藝術。書法是運用中國傳統的筆墨材質,借助于漢字書寫的藝術。更有人認為中國書法是“純粹的藝術”“最高藝術”“核心藝術”“生命藝術”,等等。上述主張書法是藝術者,通常是將書法放置于“藝術”概念之下,用藝術相關準則來評價和撰寫書法史。當下我國高等書法教育中對于書法學科的設置,除了被列入文學、美學、文藝學、歷史學等學科之外,大部分高校均將書法列入“藝術學”門類的“美術學”一級學科。
而主張書法非藝術者,即針對書法是“藝術”這一命題而提出了中國書法是“文化”之類的說法。這種命題初看似乎過于寬泛,但仔細審察歷史上的諸多所謂書法現象,我們發現書法似乎并不能簡單等同于藝術現象。所以有一部分學者面對日益高漲的“書法是藝術”的熱潮時,卻又冷靜地思考了書法非藝術的一些基本屬性和特征。
如劉守安先生就認為:“當我們把中國書法的‘身份’判定為藝術,用‘藝術學’闡釋處處受阻與遭受尷尬時,我們不得不考慮的是在中國書法研究中我們選錯了理論與方法,還是藝術學學者選了自己把握不了或不該由自己把握的研究對象?”他進一步解釋中國漢字的發源并非一種“藝術”的發源,漢字的書寫也并非當代意義上的“藝術創作”。漢字的創造與書寫都自覺不自覺地求美,但與我們今天“藝術學”中講的“藝術”不是一回事。用今天從西方傳過來又經我們闡釋的“藝術學”的體系“對接”和“推定”中國書法,其結果是在甲骨片上書刻占卜文字,在青銅器上鑄刻文字,在竹木簡牘、帛、紙上書寫的千萬種著述、公文、信札等,在石頭上書刻的碑文、墓志,記人記事文字,儒、釋、道經籍文字等,都被稱為“書法藝術作品”,書刻活動被稱為“書法藝術創作”,各類漢字書寫活動被稱之為“藝術”實踐活動,各類字跡被作為“書法藝術”作品來說解,歷代各類留下字跡或未留下字跡的政治家、軍事家、學者、文學家、宗教人士以及一般能書刻漢字的人群都被當作“書法藝術家”來描述定位,從而把中國人發明和使用漢字的歷史當作“藝術史”去撰寫。這種認識的偏差與錯位是明顯的。[2]當代書壇中主張此類觀點的學者亦不在少數,在此不必一一列舉。當然對于這兩種認知觀念孰是孰非,相互關系等問題,并非本文所討論話題,故不再贅述。
總而言之,當代書壇中對于書法概念認知的差異直接影響書法其他問題的產生。這類從文化史的視角審視書法觀念者就與從藝術的角度理解書法者形成對峙,從而產生諸多問題。因此,可以說對于書法概念及其本質認知中的矛盾問題,是當代書法諸多矛盾現象產生的基礎和前提。
二、當代書法品評中的矛盾
對文藝作品的評論、鑒賞及價值標準評判,是藝術史展開的前提和重要內容。當代書法在品評中的矛盾主要是圍繞中國傳統文藝觀和國外文藝影響的品評觀念之間的差異來展開的。這種對書法作品的品評差異,直接影響書家對作品風格的把握、形式的選擇和價值評判標準的認知,亦由此產生諸多矛盾現象。
一方面,我們知道,在中國書法史上東漢趙壹《非草書》、南朝王僧虔《論書》、袁昂《古今書評》、庾肩吾《書品》,都較早從書法家和書法作品的本質問題出發,建立了中國書法品評的基本框架。再到唐代孫過庭《書譜》等,繼而到宋、元、明、清各家的書論,無不對歷代名家書作給予評價鑒別。繪畫史上又如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中提出的“神、妙、能、逸”四品,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提出的“自然、神、妙、精、謹細”五等說,再到宋代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中列“逸、神、妙、能”四格,等等。
中國歷史上這些傳統的書畫品評,雖然也會因歷代文人觀點差異有所改變,但其基本依循的價值評判標準均是圍繞以儒、道、釋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制定的。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下的書法品評和價值評判,其對作者、作品及創作觀念的衡量尺度在某種程度而言較為清晰。尤其在當代,書法史上的諸多經典作品都可以作為這類傳統品評的標準予以參照。這種中國傳統文化中產生的文藝品評觀念,一直以來被作為中國書法品評的重要標準。
另一方面,中國經歷了近代史上的西學東漸,后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再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及“85”美術思潮等,我國文藝思潮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碰撞。直到當下新的時期,當代中國書壇也受到我國文藝大繁榮的影響,出現了諸多藝術風格迥異的作品,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下的文藝品評和價值評判,也遭遇了前所未有之沖擊。當代中國書壇隨之出現了諸多直接或間接受國外文藝思潮影響的書法品評觀念。這些書法品評觀念,主要來自日本前衛派和西方現代派藝術思潮。
其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書道”藝術也逐步繁榮,書法作品成為“日本美術展”重要部分。伴隨明治維新對文藝思潮的波及,在日本先后產生了詩文書法、少字書法、前衛書法、意象派、墨象派等現代書法流派,日本前衛流派書法對中國書法具有很大影響。這類藝術家在作品風格和創作觀念上都與中國傳統書法有很大不同,在筆墨技巧、視覺形式和展示方式等方面都呈現出新的樣式。他們通常主張書法是線條的藝術,是中心線的構建體,忽略漢字的基本功用,著眼于由借助漢字書寫所完成的造型形式,強化書寫中自然呈現的墨象表達等。當代書法創作,此類影響頗盛,至今依然有諸多書法家對墨色、線條、視覺效果的獨立價值有所追求,裝裱形式也一改傳統卷軸而用現代各類綜合材質,紙張也不局限于傳統的宣紙而廣泛使用各類工具和材料,可謂手法形形色色,形式豐富多彩。可見,日本前衛派書法對中國傳統書法的現代革新產生了深刻影響。
其二,受西方現代派藝術思潮影響。1985年5月,伴隨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的“前進中的中國青年美展”拉開了“85美術運動”的序幕,直到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展”在褒貶不一的爭論中匆匆落幕,這一時期的美術活動亦被稱為“85新潮美術”。而這一運動的起點是“對‘文革’期間美術異化為政治話語工具的反撥,是一次向美術藝術本體回歸的潮流”[3],然其核心思想則主要是受到西方現代派藝術思潮的影響。就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我國改革開放浪潮,西方現代派藝術思潮迅速席卷中國大地,在“85新潮美術”盛行的短短幾年內,中國美術演練了西方藝術從古典主義到后現代主義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幾乎所有的藝術語言形式,隨之在中國吹來一股“西方現代藝術”之風。西方藝術展覽和作品紛紛在我國藝術界獲得追捧,這類藝術家,主張藝術表現不應依靠客體物象本身的因素,而要靠藝術家的再創造。于此同時,許多關注中國書法的藝術家借此也重新闡釋和表現書法藝術,借助于漢字和書法的基本特點,創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總之,不論是日本前衛派書法,還是西方現代派藝術思潮,都對我國當代以來的文藝思潮產生極大的沖擊和影響。當然,對這類作品表達的審美追求等問題我們暫且不論,但此類藝術觀念呈現出的藝術價值品評和評判標準則對中國當代書壇影響深遠,由此也形成當代書壇的矛盾現象之一。
三、書法創作形式中的矛盾
伴隨上述矛盾現象,進而引發了當代書法創作形式中的諸多矛盾。縱觀我國當代書壇,創作形式各不相同,表現方式豐富多樣,視覺感受千差萬別。然細察各類創作形式中的矛盾現象,基本是圍繞尚帖、尊碑、碑帖相融及借鑒國外藝術這幾方面書法創作形式而展開的。因為這幾種不同的書法創作形式,亦由不同的審美觀念所支配,并且各種創作形式均有其獨立且完備的技法和要求,因此幾種創作形式之間隨之也產生種種矛盾。
首先,對于“尚帖”的書法創作形式,其主張學習中國書法史中名家墨跡體系中傳統的法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尚帖”的書法形式在當代書壇尤為活躍風靡一時。因為伴隨我國書法出版事業和展覽繁榮,原本秘藏于宮廷內府的歷代精品書畫都能通過書籍的出版發行和展覽公之于眾,加之當代融媒體時代傳播方式的便捷,當代書法學習者從接觸書法之初就能直接受益于書法精品真跡或影印墨跡,扎根于帖學經典書法的臨摹,直接借鑒或摹仿經典法書的風格形式來創作。觀當代書壇,諸多“尚帖”書家以“二王”一脈法書為宗旨,在尚帖的書法實踐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我國各類書法教育大多也都沿著這一思路取得了豐碩成果,當代書壇也形成了所謂的“帖學書風”或“二王熱”,使帖學書法得到了自清中期以來前所未有的復興。
其次,就是“尊碑”的書法創作形式。此類作者即是沿著清代碑學思路,對傳統帖學以外的文字遺跡給予觀照,直接或間接地將書法的取法對象擴大到了石刻碑碣一類的名家譜系以外的文字遺跡之上。伴隨當代考古學和出土文物的增多,這類尊碑的作者依然堅定碑學思路,其創作形式及審美追求與傳統帖學有了本質區別。以清代主流碑學的學習方法和審美觀念為依據進行書法創作,其以追求“金石氣”“高古”“壯偉”“渾然天成”“神奇渾璞”“不衫不履”之類的審美為旨歸,亦如晚明傅山所認為:“漢隸之妙,拙樸精神。如見一丑人,初見時村野可笑,再視則古怪不俗,細細丁補,風流轉折,不衫不履,似更嫵媚。”[4]通常追求的即是這種“不衫不履”的創作形式和審美體驗。
另外,即是“碑帖相融”的創作形式。當然關于碑帖相融的觀念與主張,并非當代才有的,但碑帖相融或碑帖結合的創作思路,是在碑學及其發展過程中,諸多書家對碑與帖的關系重新審視和反思后所產生的書法認知。有學者認為“碑帖相融”觀念,清代以來的石濤、金農、鄭燮、伊秉綬、包世臣、何紹基、吳讓之、趙之謙、楊守敬等都已經涉及,從“揚州八怪”的以碑破帖,到晚清碑派書家的碑帖融合,可看作是碑帖融合創作模式的發展軌跡。康有為晚年也已經改變自己早年的“尊碑”看法,明確提出了“北碑”與“南帖”融合的理念。[5]直到當代書壇,更有學者認為:“今天和碑學毫無關系的純帖學書法家已經不多見了。自碑學思潮興起以來,碑與帖這兩大傳統之間固然有競爭,但兩者互相磨合與消融的關系一直是主流。”[6]因此,進入20世紀后期以來,諸多書家進一步厘清了碑學和帖學書法在審美及創作中的相互關系,更多書家、學者也逐漸認同和倡導碑帖相融的創作觀念和表現形式。當然,在“碑帖相融”中,書家在對帖學和碑學如何融合、誰主誰輔、誰來融合誰等等這些具體問題上雖然存在著差異,但在對碑學和帖學的相互關系的把握以及審美認知的基本方向上卻是基本一致的。
還有,就是借鑒國外藝術而創作的書法形式。誠如上文所述這類創作形式借鑒日本或西方藝術形式,表達和呈現方式與中國傳統書法截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在全球化進程中,中西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與互動,借鑒國外藝術形式改造創新后的藝術形式,更加有利于廣泛傳播與接受。不可否認,西方現代派、日本前衛派以及國內的“85新潮美術”等諸多因素對當代中國書法影響較大,在傳統書法體系之外又有諸多風格特異、形式鮮明的書法作品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尤其對于中國文化和中國書法的對外傳播產生很大影響,引起眾多參與者在書法面前的不同理解與追求。當然,這種借鑒外國文藝創新中國書法的具有現代性意味的藝術形式,在我國一般大眾面前依然存在諸多爭議,但其對當代中國書壇的影響及其產生的諸多矛盾現象,亦是我們不可回避的。
四、當代書法教育中的矛盾
綜合上述幾方面因素,面對當代書法教育教學,其矛盾主要表現為各類教育教學機構、教育宗旨、教學目標、教學綱要、就業問題等方面不成體系,彼此矛盾的現象,亟須進一步改進與完善。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旨在以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為目標弘揚中華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及把美育納入各級各類學校人才培養全過程。《意見》明確指出學校美育課程以包括書法在內的藝術課程為主體,并且對各個年齡和階段的美育課程提出了具體要求,可以說給當代書法教育指明了方向。
首先,在當代書法教育與教學中,教育宗旨、目標、綱要、就業等方面,既是客觀獨立,又是彼此對應、相互依存的關系。這就要求當代書法教育在具體實踐中要根據教學對象和目標制訂相應的教學計劃,應從全局考慮,環環相扣、貫徹如一,全面規劃、系統運作,切勿顧此失彼。
其次,在教育宗旨、目標、綱要、就業等方面亦需任務明確。對于書法教學宗旨而言,應該踐行《意見》精神。美是純潔道德、豐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審美教育、情操教育、心靈教育,也是豐富想象力和培養創新意識的教育,能提升審美素養、陶冶情操、溫潤心靈、激發創新創造活力。通過書法藝術教育教學達到美育教育的目的,應是當代書法教育的基本宗旨。
另外,當代書法教育如果按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社會教育來劃分,也應該建立與之相應的教學目標、課程綱要等。然而,當代書法教育的一些機構和人員仍然存在教學目標、教學綱要混亂或矛盾的現象。在教學目標上,即對“培養什么樣的人”這一問題存在矛盾。如以培養書法藝術家和書法教育工作者為例,其兩者的目標各不相同。對書法家的培養目標,會有傳統文化學者、傳統書法技藝傳承者、獨立藝術家等差異,對書法教育工作者的培養也會因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的要求而不同。在教學綱要上,即在“如何培養人”這一問題中也有矛盾,如在面向以書法藝術家、書法教育工作者、獨立藝術家這幾種不同方向的培養目標時,應建立與之相應的教學綱要和計劃。
結語
2016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是一個“根本問題”[7]。因此當代書法發展和教育教學同樣應圍繞這一“根本問題”來展開。通過對當代書壇矛盾現象的梳理,筆者從書法概念認知、當代書法品評、書法創作形式和書法教育教學四個方面呈現了當代書壇中存在的矛盾現象,這些現象既是當代書法發展和書法教育繁榮的體現,也是我們必須直面和亟須厘清的問題。
注釋:
[1]李彤.書法藝術的思考與闡釋[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1:11.
[2]劉守安.“意義的世界”與“文化的世界”[J].書畫世界,2008(7):31.
[3]彭修銀,楊愛新.20世紀90年代中國美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J].南開學報(哲學版),2000(5).
[4]傅山.傅山全書:第1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421.
[5]金丹.論康有為的碑帖融合觀[J].榮寶齋,2019(03).
[6]白謙慎.與古為徒和娟娟發屋[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91:11.
[7]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