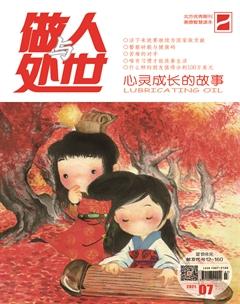張元濟:國家文化之大幸運
馮東
出版家張元濟重視和整理影印古籍叢書,用力最勤、最費神的當屬《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從醞釀到出版,費時7年,張元濟無論是從定書目、選底本、文字校勘,還是工程預估、印刷紙張,都親歷親為,殫精竭慮。他說:“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弛域外。”他訪遍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家,還遠赴日本搜集挑選宋元明善本。他以一人之力,為百年中國苦難歲月的古籍善本安了一個家。
張元濟視《四部叢刊》為自己的孩子,傾注大量心血。在赴日訪書的一個半月里,他飽覽東京、京都等地圖書館的漢籍收藏,一個花甲老人,本應該盡享天倫之樂,但那顆熊熊燃燒的心支撐起他強大的意志力,每天都做筆記直到深夜。夜色闌珊,他奮筆疾書,書心中塊壘,國家的富強靠什么?國之瑰寶被列強占為己有,我泱泱大國任人宰割,培養(yǎng)人才尤為重要。想到這里,他的勁頭更足了,與時間賽跑,為國家付命。他苦苦尋覓,找到46種罕見古籍的攝影底片,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果啊!
面對殘破殘缺、墨跡不清的古書,面對歲月侵蝕的“生命”,張元濟精心修校,用不同的版本對照甄別,斷其是非。不清楚的字跡,經(jīng)他之手,仿佛有了靈性,被描潤清楚,校勘準確。他就是這樣終日伏案,每天工作量100頁,每一頁都校勘到準確無誤為止。直到今天,看過他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嘆為觀止。張元濟有一個觀點,衡量編輯人員水平的重要標準是圖書質(zhì)量。他對古籍編校的精益求精、嚴謹細致的作風就是最好的證明。由他組織編纂的《四部叢刊》《續(xù)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初稿》,在中國文獻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張元濟以“書貴初刻”作為整理古籍選擇善本底本的原則。他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又不拘泥于原則,忠于宋元舊版,但又把不同版本經(jīng)過反復對比,擇善而定。他重視內(nèi)容與形式的和諧統(tǒng)一,不僅要求書籍內(nèi)容精確無誤,而且對裝幀也十分講究。他主張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寬展,否則蹙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他發(fā)現(xiàn)《太平御覽》格子過小,行數(shù)甚密,過于束縛,殊欠生動,于是,要求平版廠重寫,“將格子放大,落筆較為自如”,對其所用紙張,主張“選最為適宜之品,不宜省錢”。這些,都體現(xiàn)了張元濟處處留心、事事留意的治學態(tài)度。
張元濟一生為了中國文化,大力搜求古今圖書,陸續(xù)收購長洲蔣氏、會稽徐氏、太倉頤氏等藏書家藏書,于商務印書館內(nèi)特辟“涵芬樓”為藏書處。不久,又收集藏書家的大部分藏書,所積達10余萬冊。宋,元、明、清善本書極多,外國雜志、報紙、圖書也極完備,藏書質(zhì)量和規(guī)模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
在動蕩的時代里,埋頭于古籍整理,鉆進故紙堆里輯校古書,沒有維系中華文化命脈的責任擔當,沒有傳統(tǒng)文化基因的傳承弘揚,沒有長遠眼光、寬廣胸懷和強大毅力,是根本不能做到的。張元濟一直在尋找富強中國的道路,他以出版推動教育,為中華民族的文明“續(xù)命”,成就了獨特的為民請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