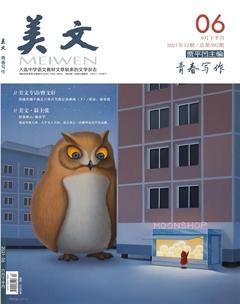麥之語
安黎
北疆之人,誰又不曾接受過麥子的喂養呢?
飽人以腹,壯人以體。一個族群的繁衍生息,一個國家的強盛壯大,皆離不開麥子源源不絕的貢獻。麥子普惠天下,廣濟眾生,卻從不居功自傲,擺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勢。甚至,因其過于尋常,都極少被人正視過,既罕有被詩文吟詠,更未見被碑石銘刻。
承蒙萬物之施舍,人類才得以繁衍生息。萬物之中,恩賜人最多的,就植物而論,首當其沖的就是麥子。
麥子被劃入莊稼之列,為人所耕種,為人所收獲,為人所碾打,為人所粉磨,最終以面粉的形態,為人所食用。當然,麥子與人,是在相互成全:沒有人的耕種,麥子無以生長;沒有麥子的充饑,人無以存續。
麥子并非源于野生,每一株禾苗,皆源于農夫的播種。那些在世俗世界里被輕賤的農夫,盡管皮粗肉糙,面容枯槁,但究其本相,卻是所有人的衣食父母。是他們,以自己近乎于玩命地付出,既為自己的家人,也為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提供著一日三餐的食料。他們生于土,長于土,在土里歌哭,在土里生死。土地,之于他們,既是日夜陪伴的情侶,又是勞損筋骨的寇仇。他們像土地的人質,也像莊稼的奴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身折腰,幾乎把全部的力氣和希冀,不打折扣地交付和托付給了土地。然而,土地能否“種瓜得瓜”地回報他們,他們卻說了不算,還得看天象的臉色。一場噼里啪啦的冰雹,一場突如其來的霜凍,或者一場持續數月的干旱,就能使他們的夢幻,像瓷器店遭到榔頭的打砸那樣,碎成滿地的殘渣。
曾幾何時,在生產力極其原始的狀態里,一年一度的割麥,仿佛煉獄,給夏收的參與者,施之以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酷刑,唯有那些親歷者,才能真正咂摸出“粒粒皆辛苦”所隱匿的悲苦與疼痛。白居易《觀刈麥》中所披露的,不過是夏收的些許端倪,而不是全部的寫真。夏收,是在龍口里奪食,一旦最佳的時機錯失,便顆粒無歸。于是上至耄耋老嫗,下至三歲孩童,甚至哪怕是還在坐月子的虛弱產婦,都不會躲在屋檐下獨享清涼,而是要無一例外地頭頂爆燃的烈陽,急慌慌地奔向麥地和碾場。烈陽似火,人若烤肉,夏收過后,每個歷經者,都仿佛被烤熟的熏肉那般,膚色又黑又紅。從割麥到運輸,從攤場到碾打,從揚場到晾曬,人瘦一圈,牛也瘦一圈,最終黃亮亮的麥粒才脫穎而出,并一分為三地各有歸宿:部分留作口糧,部分交付公糧,部分拿到交易市場去銷售。
一碗面,千顆麥,萬滴汗。麥子是面粉的母親,汗滴是麥子的乳汁。珍惜糧食,致敬農人,不但應成為我們這些面粉享用者的日常習慣,更應成為我們發自內心的精神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