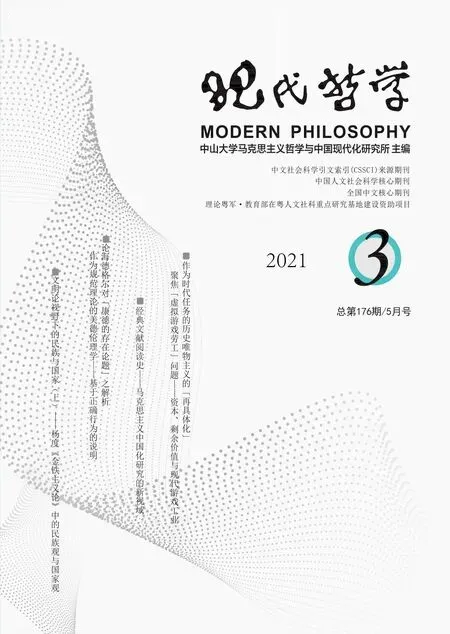論海德格爾對“康德的存在論題”之解析
鄧曉芒
海德格爾的《路標(biāo)》一書收錄了他20世紀(jì)20-60年代的十幾篇有學(xué)術(shù)代表性的文章,時間橫跨其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40年,并且是他所有論文集中在學(xué)術(shù)上最純粹、最具有哲學(xué)史研究風(fēng)格的一本論文集(1)參見[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孫周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0年,“編者后記”。。其中,《康德的存在論題》是《路標(biāo)》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61年的一次講演。為什么將這篇談康德的文章放在最后,似乎并不是按照時間排序這么簡單,至少這客觀上表明海德格爾在哲學(xué)方法上最終是從康德那里受到教益的。不論他談希臘哲學(xué)還是談黑格爾,他的眼光都是康德式的,這導(dǎo)致他對亞里士多德的實體論和黑格爾的辯證法都缺乏同情的理解。顯然,他的存在者和存在本身的區(qū)分就來自康德的現(xiàn)象和自在之物(物自身)的劃分。所以他才會在《康德書》中抱怨說:“在德國唯心論中開始的反對‘物自身’的爭斗,除去意味著對康德所為之奮爭的事業(yè)的越來越多的遺忘之外,還能意味什么呢?”(2)[德]海德格爾:《康德與形而上學(xué)疑難》,王慶節(jié)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第265頁。當(dāng)然,就康德而言,他的存在論(本體論)本身就既包括現(xiàn)象的存在,也包括自在之物的存在。他對自己的“整個形而上學(xué)系統(tǒng)”設(shè)計的第一部分就是存在論(本體論),并稱之為“先驗哲學(xué)”,其中“只考察在一切與一般對象相關(guān)的概念和原理的系統(tǒng)中的知性以及理性本身,而不假定客體會被給予出來”(3)[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38頁,語句有調(diào)整。。雖然不假定客體被給予出來,但也囊括了客體被給予出來的情況,所謂“一般對象”既可以是自在之物,也可以是指被給予的經(jīng)驗對象。這就是使海德格爾不滿的地方,即混淆了存在者和存在本身,或者說一方面把存在者直接當(dāng)作一種存在,另一方面又把存在本身也看作另一種存在者。為了澄清這一點,海德格爾提出“康德的存在論題”。但他是否澄清了這一問題呢?
一
文章一開頭,海德格爾就點明了他所關(guān)注的核心問題:
我們用“存在”(Sein)一詞來命名那個東西。這個名稱所命名的,是我們在說“是”(ist)以及“曾是”(ist gewesen)和“將是”(ist im Kommen)時所指的那個東西。我們所獲得和達(dá)到的一切,都貫穿著這個被說出的或者未被說出的“它是”(es ist)……然而,一旦“存在”這個詞傳到我們的耳朵里,我們還是堅信:人們不能就此詞設(shè)想什么,人們不能就此詞想象什么。(4)[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22頁。
海德格爾對這種情況深感不滿,即人們借口對此沒有什么可說的,于是就“不去深思存在,不去回想一條通往存在的思想道路”(5)同上,第522—523頁。。海德格爾認(rèn)為,盡管人們在“存在”一詞上不能思考什么,“那么,猜度一下思想家的實事,即對何謂‘存在’作出答復(fù),又會怎樣呢?”(6)同上,第523頁。改動處據(jù)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76.這就是海德格爾在這里對康德的發(fā)問。他認(rèn)為康德在這方面“完成了一個具有深遠(yuǎn)意義的步驟”,使傳統(tǒng)“進(jìn)入一道全新的光亮之中”(7)同上,第523頁。。這就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說的一段著名的“有關(guān)存在的論題”:
“是”(Sein)顯然不是什么實在的謂詞,即不是有關(guān)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種東西的一個概念。它只不過是對一物或某些規(guī)定性的自在本身的肯定(Position)。(A598,B626)(8)同上,第513—524頁;[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476頁,譯文有改動。
這兩句話接下來的是海德格爾沒有引的一句:“用在邏輯上,它只是一個判斷的系詞。”但海德格爾這里強調(diào)的是Sein不是實在的謂詞,它不能給某物的概念增添某種實在的內(nèi)容,而僅僅肯定了這個東西“有”。康德這段話是在“上帝的存有(Dasein)之本體論證明的不可能性”這一小節(jié)中說的,他認(rèn)為不能因為既然我說到上帝“是”或“有”,上帝就(像笛卡爾等人所認(rèn)為的那樣)現(xiàn)實地“存有”,這是不能等同的。因為“存有”(Dasein)(9)該詞在海德格爾那里通常譯作“此在”,在黑格爾那里譯作“定在”,在康德這里筆者譯作“存有”。在康德的范疇表中屬于模態(tài)范疇的第二項,相當(dāng)于“現(xiàn)實性”;而“存在”(Sein或“是”)則是一個邏輯上的系詞。前者不能脫離可能經(jīng)驗的范圍而運用,否則就是“空的”;后者則屬于“普遍邏輯”,到處都可以用,但本身沒有經(jīng)驗的實在性。不過,海德格爾揪住這一點來做文章是別有用心的,他并不是為了守住Sein在形式邏輯上的用法(系詞),而恰好是要追問和挖掘該詞在超出經(jīng)驗世界的存在者之外的本體論含義。他表面上好像責(zé)怪康德只是在反駁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時順便提到這個論題,沒有加以認(rèn)真對待,“沒有以合乎其內(nèi)容和意義的方式,把這個論題當(dāng)作一個體系的原命題(Ursatz)提出來,并且沒有把它展開為一個體系”;但又認(rèn)為這“實際上卻有其好處”,即表明這是一種“源始的沉思”,它“決不會誤以為自己是最后封閉的沉思”(10)[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25頁。。就是說,康德這種點到為止的做法倒是讓這一論題得到庇護(hù),仿佛是有意要留給海德格爾這樣超越了形而上學(xué)思維方式的學(xué)者,來打開一片嶄新的思想天地。
在海德格爾看來,康德以順帶的方式提出的這一存在論題雖然在西方思想史中完成了一個“決定性的轉(zhuǎn)折”(11)同上,第526頁。,但康德并不是直接從對存在的追問進(jìn)入這一論題的,而是由對上帝存有的證明中引出來的,這與西方從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xué)開端的存在論所具有的“雙重形態(tài)”有關(guān),就是說存在論既是“第一哲學(xué)”又是“神學(xué)”。縱觀西方哲學(xué)史,“我們可以把關(guān)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問題的雙重形態(tài)概括在‘存在-神-邏輯學(xué)’這個名稱之中”。它所追問的不但是“什么是存在者”,而且是“什么是絕對的或最高的存在者”;前者追問的是“基地意義上的根據(jù)”,后者追問的則是“使一切存在者進(jìn)入存在而產(chǎn)生出來的那個東西意義上的根據(jù)”(12)同上,第527頁。。顯然,只有后者才涉及到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問題,前者則只涉及到哪個存在者是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根據(jù)的問題。所以,康德只有在對上帝存有的追問中才觸及到對存在本身的追問,這是不難理解的。這已經(jīng)展示了一種超出傳統(tǒng)的、局限于用一個存在者的存有解釋其他存在者的存有的做法的新的可能性。于是,海德格爾說:
在本體神學(xué)的(ontotheologisch)追問的歷史進(jìn)程中,產(chǎn)生出這樣一項任務(wù):不僅要證明什么是最高存在者,而且要證明存在者的這個最在者(Seiendeste)存在,即證明上帝實存。實存(Existenz)、存有(Dasein)、現(xiàn)實性(Wirklichkeit)這些詞都稱之為某種存在方式。(13)[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28頁,譯文有改動。孫譯Dasein為“定在”。
可以看出,從亞里士多德開始的這個“本體神學(xué)”的歷史,在證明上帝的存在時,不論是本體論證明、宇宙論證明還是目的論的證明,都將這一問題等同于證明上帝的實存、存有和現(xiàn)實性。在這方面,康德有一點是與眾不同的——他第一個看出來,追問上帝的“存有”和追問上帝的“存在”還不是一回事。不過,這是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才達(dá)到的認(rèn)識。在此之前,在前批判時期的《證明上帝存有唯一可能的證據(jù)》中,他還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把“存有”(Dasein)和“存在(是)”(Sein)嚴(yán)格區(qū)分開來,甚至把兩者看作就是一回事。康德在那里說“存有(Dasein)根本不是某一個事物的謂詞或者規(guī)定性”,“存有是對一個事物的絕對肯定……肯定或設(shè)定的概念是非常簡單的,與‘是’(Sein)的概念完全是一回事”,而“是”(Sein)“不外乎就是一個判斷中的聯(lián)結(jié)的概念”(14)同上,第528頁;[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76、80頁。李秋零在這里把Dasein譯作“存在”、Sein譯作“是”,兩者似乎相安無事;但這與后面《純粹理性批判》的譯法混淆不清,他在那里常把Sein譯作“存在”,但兩個“存在”含義和性質(zhì)完全不同。([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第391—392頁。)。奇怪的是,海德格爾在引證康德這篇早期著作時,竟然沒有指出其中的表述與《純粹理性批判》的表述之差異,反而說這兩種表述是“一致的”(15)[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28頁。。按照海德格爾自己的Dasein(屬于“存在者”,中譯作“此在”)和Sein(“存在”)的區(qū)分(所謂“存在論差異”),這兩者也不可能是“一致的”。康德在前批判時期混淆了作為存在者的Dasein和作為存在的Sein(“是”),而到了批判時期,他已經(jīng)把Dasein列入自己的范疇表,再說該詞不是“某一個事物的謂詞”(即“實在的謂詞”)就說不過去。所以他把表述改成:“是”(而非“存有”)顯然不是一個實在的謂詞。當(dāng)然,理由還只是因為“是”是一個邏輯上的系詞,它并沒有被列入范疇表中,這與海德格爾的理由還不是一回事。但至少我們可以將此看作是康德從存在者向存在本身的一個過渡,也就是讓“存在”或“是”首先擺脫一切有關(guān)存在者的謂詞或規(guī)定,以便使存在本身作為一個“問題”呈現(xiàn)出來。海德格爾的轉(zhuǎn)述卻是“康德的論題說,實存、存有(Dasein)、亦即存在(Sein),‘顯然不是一個實在的謂詞’”,這個否定陳述句的意思是“存在(Sein)不是什么實在的東西”(16)同上,第529頁,譯文有改動。。這種轉(zhuǎn)述沒有把康德的“存在論題”中這種前、后期的差異展示出來,而是混在一起。一個極好的從康德的存在論題引出他自己的存在論題的機會,被海德格爾錯過了。但也許他是有意這樣做的,因為他可能并不屑于從邏輯系詞中引出他對存在本身的追問,他要的是撇開邏輯陳述而直接面對存在本身。
所以,他對上述康德的存在論題所引的最后一句——“是”這個詞“只不過是對一物或某些規(guī)定性的自在本身的肯定”也作了澄清,也就是把它和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表述區(qū)別開來,表明這里說的只是對某些存在者本身的邏輯上的肯定(而非否定),還沒有直指物自身。他說“‘自在的本身’這一表述并不是指:‘自在的’某物,無關(guān)乎某種意識而實存的某物”(17)同上,第530頁,譯文有改動。;它也不能把我們直接引到自在之物,而是通過對存在者的自在本身的肯定這樣一個“反面規(guī)定”,來表明“存在決不能根據(jù)一個存在者當(dāng)下所是的東西來說明”,從而依靠這種反彈指引存在到另外一個“它唯一才能從中得到純粹標(biāo)明的領(lǐng)域”(18)同上,第531頁,譯文有改動。,這才是作為自在之物的存在領(lǐng)域。因此,“是”作為系詞的邏輯運用,對于提示存在本身并沒有積極的意義,只有消極暗示的意義,康德說它“并非又是一個另外的謂詞,而只是把謂詞設(shè)定在與主詞的關(guān)系中的東西”(19)[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32頁;[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476頁,譯文有改動。。在海德格爾看來,這種邏輯的運用“讓人猜測還有另外一種對存在的運用。同時,我們在這個地方也已經(jīng)經(jīng)驗到了有關(guān)存在的本質(zhì)性的東西。它被‘運用’是在被使用的意義上說的。由知性、思想來實行這種運用”(20)同上,譯文有改動。。就是說,所謂“邏輯的運用”意味著存在可以有各種運用,是我們的思想把“它”用到這里那里;這也就暗示了它的這種運用還不等于它本身,另有一種運用于它本身的用法是可以把它本身揭示出來的。“在這里,有別于邏輯的用法,存在是著眼于存在著的客體而本身自在地被使用的。因此,我們就可以談?wù)摯嬖诘拇嬖谡郀顟B(tài)上的(ontisch)用法,更好地講,存在的客觀的用法。”(21)同上,第533頁。這里幾乎就要把康德的存在論引回到海德格爾自己的存在論。可惜的是,康德認(rèn)為“是(存在)”除了邏輯系詞的運用之外,剩下的只有對存在者的肯定(或斷言)。“如果不僅僅是這種關(guān)系[亦即命題主詞與謂詞之關(guān)系],而是實事(Sache)自在地且由自己本身設(shè)定起來而被考察,那么,這種存在就等于存有(Dasein)。”(22)同上,譯文有改動。存在一旦不用于邏輯系詞,而用于實指,那就只能是作為存在者的存在,其實就是亞里士多德說的“實體”。康德所謂“存有乃是對于某個事物的絕對肯定”,有別于對該事物的相對肯定,這無非是說實體是“既不述說一個主體,也不存在一個主體之中”的“這一個”(23)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工具論(上)》,秦典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6頁。。相對肯定是例如說,一個東西A是白的(而不是黑的);絕對肯定則是說,有A(而不是無A)。
二
海德格爾認(rèn)為,“‘有上帝’這個命題是否、如何以及在何種界限中才可能作為絕對肯定,這個問題是一種隱秘的激勵,它驅(qū)使著《純粹理性批判》的全部思想,并且推動著康德此后的主要著作”(24)[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34頁,譯文有改動。。當(dāng)然,這是海德格爾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及其他主要著作的看法,他曾經(jīng)認(rèn)為“《純粹理性批判》與‘認(rèn)識論’毫無關(guān)系……所建立的只有作為一般形而上學(xué),即作為整個形而上學(xué)之主干的本體論,并且在這里,本體論才首次達(dá)到了自覺”(25)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3. S.17;[德]海德格爾:《康德與形而上學(xué)疑難》,第25頁。。換言之,是本體論的“存在”,而不是邏輯學(xué)的“是”和認(rèn)識論上的“肯定”,才是康德哲學(xué)的“主干”。海德格爾就是要把邏輯學(xué)和認(rèn)識論都從本體論上剝離下來,只盯著一個赤裸裸的“存在”,以免它受到“遮蔽”。但他也發(fā)現(xiàn)這種邏輯學(xué)和認(rèn)識論的關(guān)系在康德這里是清除不干凈的,“即使在這里,也有一種關(guān)系被設(shè)定起來,而且‘是(存在)’因此獲得了一個謂詞的特性——盡管不是一個實在的謂詞”(26)[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34頁。。這種關(guān)系既是邏輯上的主謂詞關(guān)系,也是認(rèn)識論上的主體-客體關(guān)系。早在前批判時期,康德就認(rèn)為存有或存在(當(dāng)時這在他看來是一回事)雖然本身不可說,但“與我們的知性能力相關(guān)的對象的本性”已經(jīng)達(dá)到最高的清晰度(27)同上,第535頁。。所以,康德力圖從“先驗邏輯”,也就是認(rèn)識論和邏輯學(xué)一體的邏輯中來闡明這種主體-客體關(guān)系,并認(rèn)為這種關(guān)系“不同于純粹邏輯的意義,且比后者更為豐富”(28)同上,第534頁。但海德格爾接下來說,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之前的第一版中還沒有看到這一點(即“是”的邏輯系詞意義不如認(rèn)識論的客觀意義豐富),這是不對的。他大概是指的第二版§19對邏輯系詞的質(zhì)疑。但這一節(jié)的第一句話(海德格爾在后面也引了)說“我從來都不能(niemals)對邏輯學(xué)家們關(guān)于一般判斷所給予的解釋感到滿意”(黑體為筆者所加),正說明這個意思是《純粹理性批判》的基本前提,從他劃分“普遍邏輯”和“先驗邏輯”、邏輯判斷表和知性范疇表時就不言而喻地包含著,不可能只是第二版才出來的“洞識”。。最典型的就是他的范疇表中的三個模態(tài)范疇——可能性、存有、必然性,海德格爾表達(dá)為“可能是(M?glichsein)、現(xiàn)實是(Wirklichsein)、必然是(Notwendigsein)”(29)這種表達(dá)雖然不是康德本人的術(shù)語,但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康德的四類范疇按照判斷的形式來看,量的范疇著眼于主詞,質(zhì)的范疇著眼于賓詞,關(guān)系范疇著眼于主詞和賓詞的關(guān)系,模態(tài)范疇著眼于系詞“是”(ist)。此外,“康德說模態(tài)判斷的特點在于它對其內(nèi)容‘毫無貢獻(xiàn)’,而只涉及系詞與主觀思維的關(guān)系……因此,模態(tài)判斷所包含的模態(tài)范疇也有這樣的特點,它們不像量、質(zhì)范疇那樣規(guī)定經(jīng)驗對象,也不像關(guān)系范疇那樣規(guī)定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而只是規(guī)定經(jīng)驗對象和認(rèn)識該對象的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模態(tài)范疇只是在其他范疇已對判斷的內(nèi)容作了客觀的綜合之后,再將它們與知性的認(rèn)識能力作主觀的綜合。”(參見楊祖陶、鄧曉芒:《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5—126頁。)。
11月13日,由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指導(dǎo),環(huán)球家電網(wǎng)、《家用電器》雜志主辦,蘇寧易購集團(tuán)股份有限公司戰(zhàn)略合作的“2018年中國電冰箱行業(yè)高峰論壇”在重慶隆重召開。大會以“鮮贏天下·智創(chuàng)未來”為主題,匯聚業(yè)內(nèi)專家、企業(yè)精英,共同探討冰箱行業(yè)的持續(xù)健康發(fā)展之道。

盡管如此,海德格爾還是盡可能地想把康德的這種認(rèn)識論和他自己的(筆者稱為“赤裸裸的”)存在論掛起勾來。康德在§15中曾說,統(tǒng)覺的本源的綜合統(tǒng)一是何以可能的,“我們必須到更高的地方去尋求這種統(tǒng)一性……亦即在那本身就包含著判斷中不同概念之統(tǒng)一性根據(jù)的東西中,因而在包含著知性的可能性根據(jù)、甚至知性在其邏輯運用中的可能性根據(jù)的東西里面,去尋求這種統(tǒng)一性”(35)同上,第88—89頁。。這個東西在康德那里就是“我思”,即先驗的自我意識或者說自我主體。海德格爾據(jù)此斷言,這就是在根據(jù)存在論題與知性的關(guān)系來“規(guī)定存在及其方式”,并且還“為一種變化了的、更豐富的存在解釋提供了保證”;這樣,“對存在者之存在的規(guī)定便得以進(jìn)行了”(36)[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40頁。。這似乎是說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就已經(jīng)通過“我思”在進(jìn)行“存在解釋”,更不用說康德的先驗自我本身暗中也已經(jīng)是一種對存在的追問。

據(jù)此,康德的先驗哲學(xué)其實無非是“依照純粹理性批判而變化了的存在論(或本體論),它把存在者之存在當(dāng)作經(jīng)驗的對象之對象性來追思”(38)[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42頁,譯文有改動。。當(dāng)然,海德格爾也許自己都覺得這樣說有點勉強。笛卡爾也好,康德也好,都只是在尋求“什么是存在”,卻并未特意去探討“存在是什么”,更沒有追問“存在本身如何是”。所以,海德格爾接著便指出康德的兩個局限,一是讓存在論植根于(先驗的)邏輯,二是讓它和經(jīng)驗對象捆在一起,兩者都是讓存在取決于它與知性使用的關(guān)系,其實只能被理解為“存在者”。即使康德把存在劃分為現(xiàn)象中的客體的存在和自在之“物”(Ding an sich selbst)的存在,也只是在談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照理說,對于這種用存在者遮蔽和取代存在本身的陳舊做法,海德格爾通常都會毫不留情地痛批一頓,更何況在這種做法中,人類學(xué)的主體性和科學(xué)主義的工具性都達(dá)到前所未有的極致。奇怪的是,海德格爾在康德這里傾注了在其他哲學(xué)家身上少見的溫情。按照他的描述,康德的這些遮蔽存在本身的表述其實都是對存在之思的變體。他網(wǎng)開一面,說“只要在康德語言中的‘對-象’和‘客-體’等詞語中回響著那種與思維著的自我-主體的關(guān)系,而從這種關(guān)系中作為肯定的存在獲得了它的意義,那么,我們最好也在字面上來理解這些詞語”(39)同上,第544頁,譯文有改動。。就是說,我們不必計較康德的主客體的對立以及主體主義的形而上學(xué)語言,而可以從這些詞語中去揭示對存在的肯定,甚至就連從中發(fā)展出來的,經(jīng)過費希特、謝林到黑格爾的“邏輯科學(xué)”和“辯證法”的運動,其實也可以看作不過是“存在的絕對性”在那里運動(40)同上,第544—545頁。。整個德國觀念論都應(yīng)該感謝康德,使他們逃脫了、至少是減輕了海德格爾攻擊的火力。
至于如何從康德有關(guān)“存在者”的那些立法的原理中提取出有關(guān)“存在”的思想,海德格爾也打算做一些示范。但看來看去,他從康德的四大原理體系中也只挑中模態(tài)原理,即“一般經(jīng)驗思維的公設(shè)”。“我們現(xiàn)在不得不局限于對第四組、即諸‘公設(shè)’的描述,而且是帶著唯一的意圖,就是要讓人們看到作為肯定的存在這個主導(dǎo)概念是如何顯露出來的。”(41)同上,第545頁。為什么“不得不”局限于對公設(shè)(Postulate)的描述,海德格爾沒有說。其實道理很簡單,如前所述,只有在這三條原理即可能性、存有(現(xiàn)實性)和必然性的公設(shè)中,所針對的才是系詞ist本身,其他的原理都沒有。海德格爾順便還扯到實踐理性的Postulate(在那里筆者譯作“懸設(shè)”(42)參見[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頁腳注中的譯者說明。),但只是為了證明該詞包含有“要求”的意思,并且屬于“康德真正的形而上學(xué)的最高點”,以增加其權(quán)威性;其他方面的意思則小心地避開了,因為他對于《實踐理性批判》并沒有研究。總之,“公設(shè)”就是“要求”,但這里不是實踐理性的要求,而是知性本質(zhì)的要求。要求什么?要求這三個范疇與存在本身發(fā)生關(guān)系,所以它們實際上表達(dá)的是存在,海德格爾寫成“可能存在(是)、現(xiàn)實存在(是)和必然存在(是)”。這就挑明了康德的“存在論題”即“存在顯然不是一個實在的謂詞”的更深層次含義,就是這三種“存在”既然都“并非關(guān)于對象(客體)是什么的陳述,而是關(guān)于客體與主體的關(guān)系之如何(Wie)的陳述”,所以它們都不是“實在的謂詞”;但也不像前批判時期所說的“根本不是一個謂詞”,而是一些“先驗的(存在論上的)謂詞”(43)參見[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46—547頁。。
但以這種方式把康德的范疇和“存在(是)本身”掛起勾來而與“實在的謂詞”脫離關(guān)系,顯然很不靠譜。實際上,康德說的是“存在(是)不是一個實在的謂詞”,卻沒有說“諸范疇都不是實在的謂詞”。相反,熟悉康德哲學(xué)的人都知道,范疇在康德那里不但具有“先驗的觀念性”,而且具有“經(jīng)驗性的實在性”,缺一不可。范疇只能運用于可能經(jīng)驗的范圍,不能用于作為自在之物的先驗對象,即使是模態(tài)范疇也不例外。海德格爾所引的康德三條“公設(shè)”的原文都說明,它們無一離得開經(jīng)驗的“形式條件”“質(zhì)料條件”“普遍條件”(44)同上,第546頁。。盡管海德格爾利用三條公設(shè)與系詞“是”的特殊關(guān)系而把它們稱為“可能是、現(xiàn)實是和必然是”,也不足以讓它們與存在(是)本身直接捆綁在一起,因而被“是”帶離“實在的謂詞”。在康德那里,所有的十二范疇都是“實在的謂詞”,而不是脫離經(jīng)驗的“先驗的(存在論上的)謂詞”。所謂“存在論上的”(本體論上的)謂詞在康德看來只能是形式邏輯的邏輯謂詞,所以他才提出對“上帝存有(Dasein)的本體論(ontologische)證明”的反駁,也就是對上帝現(xiàn)實存在的邏輯證明的反駁。康德不說對“上帝存在(Sein)的證明”的反駁,因為這用不著反駁,它只是一種純邏輯的命題。如果現(xiàn)實中“沒有上帝”,則上帝是否“是”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說什么都不會自相矛盾。所以,要反駁的是上帝是否現(xiàn)實地存在即“存有”(Dasein)。海德格爾連這一點都沒有搞清楚,居然把前批判時期的命題“存有根本不是一個謂詞”不假思索地改寫成“存在‘根本不是一個謂詞’”(45)參見[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47頁。,繼而又把批判時期的命題“存在不是一個實在的謂詞”等同于“存有不是一個實在的謂詞”,并把“存有”說成一個“先驗的(存在論上的)謂詞”,也就是一個有關(guān)“自在之物”的謂詞。根據(jù)這樣的糊涂觀念,海德格爾重溫康德的“存在論題”中有關(guān)“存在……只不過是對一物或某些規(guī)定性自在的本身的肯定”一語,恍然大悟道:“按照《純粹理性批判》的語言,‘物’(Ding)現(xiàn)在是指客體或?qū)ο蟆?腕w作為認(rèn)識的客體,它的‘某些’規(guī)定是并非實在的規(guī)定,是存在的模態(tài)。”(46)同上,第547頁,譯文有改動。就是說,原來康德所說的“存在(是)”就是指的模態(tài)范疇,特別是其中的“現(xiàn)實存在”范疇,即“存有”(Dasein)!
但光是這樣說是不夠的,還必須把模態(tài)范疇形式化、抽象化或“非實在化”,以便把它們與赤裸裸的“存在本身”捆在一起。海德格爾采取的辦法就是忽略掉這些范疇對經(jīng)驗條件的依賴,而單把這些依賴關(guān)系本身的形式提取出來。于是,三個公設(shè)就成了“可能性是:與……相一致;現(xiàn)實性是:與……相聯(lián)系;必然性是:與……相聯(lián)結(jié)”(47)同上,第548頁。。被省略掉的都是經(jīng)驗性的條件,這就使這些范疇不再像是“實在的謂詞”、因而和“存在(是)”本身接近。但這樣理解的范疇還是康德的范疇嗎?這只是一些形式邏輯的技術(shù)規(guī)則而已。康德在《邏輯學(xué)講義》中曾對這些知性規(guī)則作了這樣的定位:
既然知性是規(guī)則的源泉,它自己按照什么規(guī)則行事呢?
因為毫無疑問:除非按照某些規(guī)則,我們就不能思維,或者就不能使用我們的知性。但是,我們又能夠單獨地思維這些規(guī)則,也就是說,我們能夠離開它們的運用或者抽象地思維它們……
但是,如果我們現(xiàn)在把我們必須僅僅從對象借來的一切知識放在一邊,僅僅對一般而言的知性應(yīng)用進(jìn)行反思,那么,我們就發(fā)現(xiàn)了知性應(yīng)用的這樣一些規(guī)則,它們在所有方面并且不考慮一切特別的思維客體,絕對是必然的,因為沒有它們,我們就根本不會思維。因此,這些規(guī)則也能夠先天地,亦即不依賴于一切經(jīng)驗而被看出,因為它們不分對象,僅僅包含著知性應(yīng)用的條件,不管這應(yīng)用是純粹的還是經(jīng)驗性的。(48)[德]康德:《邏輯學(xué)》,《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第11頁。
海德格爾本應(yīng)該從康德的這一定位中尋求自己的根據(jù),這當(dāng)然是順理成章的,而且里面還談到必然性、偶然性(客體性)和可能性這些規(guī)則。可惜不行。因為這里談的并不是海德格爾所希望談的“本體論(存在論)”,而是邏輯學(xué),即形式邏輯。如果把這樣一些規(guī)則看得比范疇更高,那將導(dǎo)致康德好不容易才從形式邏輯提升到先驗邏輯的哲學(xué)變革全部白費,形而上學(xué)將倒退到沃爾夫的邏輯主義的存在論,這正是海德格爾自己要避免的,他曾經(jīng)把邏輯學(xué)形容為“把邏各斯配制成為工具”(49)參見[德]海德格爾:《形而上學(xué)導(dǎo)論》,熊偉、王慶節(jié)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第188頁。。但他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風(fēng)險,他努力使模態(tài)范疇退回到純粹知性本身的(也就是邏輯上的)法則,認(rèn)為這些公設(shè)作為“要求”不但是“從作為思想之源泉的知性中產(chǎn)生的”,而且還是“為了思想的”;此外,他還力圖擴(kuò)大戰(zhàn)果,說“公設(shè)在純粹知性的原理表上雖然只是在第四位即最后一位才被提到的;但按照等級卻是第一位的,因為每個關(guān)于經(jīng)驗對象的判斷事先都必須滿足這些公設(shè)”,由此他列出的遞進(jìn)關(guān)系是“公設(shè)指稱存在;存在歸屬于存在者的存有;存在者作為現(xiàn)象乃是對認(rèn)識主體而言的客體”(50)[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48頁,譯文有改動。。就是說,公設(shè)指稱的存在是“先驗的(存在論的)謂詞”(據(jù)前面的分析,應(yīng)該是邏輯的謂詞);它屬于每個存在者的存有(當(dāng)然,因為每個存在者都含有邏輯形式);而存在者則是“對認(rèn)識主體而言的客體”(這是由邏輯謂詞去建構(gòu)現(xiàn)象的對象的結(jié)果,知性為自然立法,這時邏輯謂詞才成為了實在的謂詞);而再進(jìn)一步就涉及到主體本身,即通過“客體之客體性與人類認(rèn)識之主體性的純粹關(guān)系”,最終追溯到“先驗統(tǒng)覺的純粹綜合”,因而模態(tài)范疇作為“存在謂詞”“必然在主體性中有其淵源”。海德格爾由此而認(rèn)定“在康德的存在論題中,未曾道破地回蕩著一個指導(dǎo)詞語:存在與思想”(51)[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49頁。。顯然,這完全是康德的思路,但方向是倒過來的。康德是用形式邏輯的判斷分類作為“引線”而一步步引出范疇和先驗統(tǒng)覺,越走越高;海德格爾卻是從公設(shè)原理所指稱的最高的“存在”(邏輯系詞“是”)“下降”到現(xiàn)實的存有,再下降到主客體關(guān)系,最后降到先驗自我的主體性淵源。所以,他說的“存在與思想”其實應(yīng)該理解為“邏輯系詞”與“我思”(52)如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xué)的克服》一文中說的:“惟在這種cogitare[思想]在其本質(zhì)中被把捉為‘先驗統(tǒng)覺的原始綜合的統(tǒng)一性’的地方,惟在‘邏輯學(xué)’的極點被達(dá)到(在作為‘我思’之確信的真理中),才有客體意義上的對象。”(參見[德]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第85頁。)。
海德格爾當(dāng)然不會承認(rèn)筆者的這個結(jié)論。他在把存有范疇形式化為邏輯系詞的同時,又把邏輯系詞本身賦予更加“豐富”的內(nèi)涵,就是說,“是”(ist)本質(zhì)上就是“聚集”(邏各斯),而聚集才是康德所說的本源的統(tǒng)覺的綜合。換言之,康德的自我意識的先天綜合通過對系詞“是”的一種另類的解釋,變身為“存在”本身的綻出方式,這相當(dāng)于“此在”在綻出中對存在本身的去蔽。所以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指出:


然而,海德格爾由此而使自己化險為夷了嗎?他真地通過邏輯系詞而過渡到他自己一直在追問的存在本身了嗎?顯然還沒有。他的“是”的四種含義所揭示的還只是“在場”、“實體”即存在者本身,而且看不出比康德的四范疇構(gòu)架高明多少。如果他有興趣,他所能做到的極致頂多也就是像黑格爾的《邏輯學(xué)》那樣,推演出更加多得多的(存在著的)范疇(56)黑格爾早就說過:“系詞‘是’出自概念的本性,即概念在其外化中是與自身同一的。”他由此建立起來的四類判斷,也可以看作脫胎于康德的四類范疇,尤其是“概念的判斷”與康德的模態(tài)范疇有所吻合。(參見[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1年,第338頁,譯文有改動。)。但他寫《形而上學(xué)導(dǎo)論》的時候(1935年),對黑格爾還不是很熟(他1938年才開始認(rèn)真研讀黑格爾的《邏輯學(xué)》和《精神現(xiàn)象學(xué)》),而且即使他能夠做出一個范疇體系,也仍然沒有跳出“形而上學(xué)”的既定框架,即所謂用存在者遮蔽存在。所以,他必須另想辦法。這樣,在他看出康德的模態(tài)范疇仍然沒有能夠解決“可能是和現(xiàn)實是的區(qū)分的根據(jù)何在”的問題之后,受到謝林的提醒,就注意到康德在《判斷力批判》§76中的一段話(57)參見[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49頁。。在這段話中,康德特別把“可能性”和“現(xiàn)實性”這對范疇歸結(jié)于人的認(rèn)識能力的本性,即知性概念提供了知識的可能性,感性直觀則提供了知識的現(xiàn)實性;而由于人的認(rèn)識能力不可能達(dá)到知性直觀或直觀的知性,所以才有必要把這兩方面區(qū)分開來;但也正因此,這種區(qū)分完全是主觀上有效的,而不適合于自在之物(58)同上,第550頁。在本頁的那段對康德的關(guān)于可能之物和現(xiàn)實之物的區(qū)分的引文中,孫周興的譯文“后者(現(xiàn)實之物)則意味著對自在之物本身(在這一概念之外)的設(shè)定”易引起誤解。雖然按照字面“die Setzung des Dinges an sich selbst”,這樣譯也沒錯,但康德這里的意思并非指他的不可認(rèn)識的自在之物,而是指在概念之外所經(jīng)驗到的現(xiàn)實事物本身,所以應(yīng)按筆者的譯法:“后者卻意味著對該物自在的本身(在這概念之外)所作的設(shè)定。”(參見[德]海德格爾:《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5頁。)。海德格爾由此得出:“在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質(zhì)中,在肯定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有關(guān)可能性和現(xiàn)實性的必要區(qū)分的構(gòu)造。由于看出了存在構(gòu)造的這一根據(jù),就顯得是達(dá)到了康德關(guān)于存在所可能道出的最極端的東西。”(59)[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51頁,譯文有改動。就是說,在這里,康德對存在的揭示看起來是到頂了。海德格爾又指出,“但是,康德在存在規(guī)定方面還邁出了更遠(yuǎn)的步伐,而且這一步又只是預(yù)測性的,以至于它并沒有達(dá)到對存在作為肯定(Position)的一種系統(tǒng)性的描述”(60)同上,第551頁,譯文有改動。。什么“更遠(yuǎn)的步伐”?答案是:“就他把存在規(guī)定為‘只是肯定’而言,他是從一個被限定的方位、也就是從設(shè)定來理解存在的,這種設(shè)定作為人類主體性的行動,就是依賴于被給予者的那種人類知性的行動。”(61)同上,第551頁,譯文有改動。現(xiàn)在,我們都被海德格爾耍了,他誘使我們跟著他去追溯康德的思路,說關(guān)于存在(“是”)還有更豐富、更頂尖、更遠(yuǎn)的風(fēng)景在前面;到頭來卻發(fā)現(xiàn),我們回到出發(fā)點,就是“人類知性的主體性行動”——這不就是“我思”嗎?他說“向這一方位(Ort)的返回我們叫做探討(Er?rterung)”(62)同上,第551頁,譯文有改動。,他所謂的“探討”就是領(lǐng)著我們轉(zhuǎn)圈子。
三
不過,海德格爾還有最后一招,現(xiàn)在是亮出來的時候了。這就是他從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分析論”結(jié)束、但還沒有進(jìn)入到“先驗辯證論”之前的“附錄”即“反思概念的歧義”中所看出的某種“玄機”。他說:“這個‘附錄’包含著一種對已經(jīng)實行的思想步驟和此間所經(jīng)歷的維度的回顧性沉思。這種回顧性沉思本身乃是一個新的步驟,是康德在存在解釋方面實行的最后一步”;而這一步是為了“牢靠地規(guī)定和確保知性的界限。”(63)同上,第552頁。他替康德解釋說,對于“作為肯定的存在”也就是對于“作為系詞”的“是”的解釋既然涉及的是主客體的關(guān)系(如前所述),所以對象一定是在和認(rèn)識能力的反向關(guān)系、也就是在反思(Reflexion)中來解釋的。比如,“在對作為肯定的可能是的解說中,與經(jīng)驗之形式條件的關(guān)系、因而形式的概念起作用了。在對現(xiàn)實是的解說中,經(jīng)驗的質(zhì)料條件、因而質(zhì)料的概念被表達(dá)出來了。這樣,著眼于質(zhì)料和形式的區(qū)別,作為肯定的是的諸模態(tài)也就實現(xiàn)了解說”,由此而為“是”的方位(Ort)編織出一個定位網(wǎng)(Ortsnetz)(64)同上,第553頁,譯文有改動。。質(zhì)料和形式這樣一些概念(以及后面的同一與差異、一致和沖突、外部和內(nèi)部)由于是通過與“是”相關(guān)的模態(tài)范疇對經(jīng)驗條件的反思而建立起來的,所以叫做“反思概念”。但海德格爾認(rèn)為,“這些反思概念借以得到規(guī)定的方式方法本身又是一種反思。在康德看來,對作為肯定的是的終極規(guī)定是在一種關(guān)于反思的反思中——因而是在某種卓越的(ausgezeichnet)思維方式中實現(xiàn)出來的”(65)同上,第553頁,譯文有改動。“卓越的”意為更高層次的,而不是“別具一格的”(參見孫譯)。。他認(rèn)為這使我們更有理由把康德對存在的思考提升到“存在與思”的層次,而不只是存在者的層次。所以,這種更高層次的“對反思的反思”就是“先驗的反思”。
然而,這套對康德“反思概念的歧義”的解釋完全是不著邊際的,是海德格爾囫圇吞棗地大致讀了康德的這段文字以后,自己想當(dāng)然杜撰出來的。康德自己從來沒有使用過“對反思的反思”這種說法,他的“先驗反思”并不是由對一般反思再加反思而提升起來的,而是一種完全不同性質(zhì)的反思,它區(qū)別于萊布尼茨的“邏輯的反思”和洛克的“經(jīng)驗的反思”。康德的意思是要像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xué)的《正位論》一樣,理清各種反思在人類認(rèn)識能力中所處的先驗的方位(der transzendentale Ort),建立起一種“先驗的正位論”(die transzendentale Topik),以避免理性派依靠概念的邏輯比較和經(jīng)驗派依靠經(jīng)驗的反省(如洛克的“反省的經(jīng)驗”)而混淆不同的認(rèn)識能力,來對客觀知識加以獨斷的斷言(66)參見[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241—243頁。。可見,海德格爾對什么是康德的“反思概念的歧義”,以及為什么要區(qū)分和澄清反思概念的歧義,都完全沒有弄懂,就在那里自說自話(67)對這個問題在此無法展開,參見楊祖陶、鄧曉芒:《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第230—235頁。。海德格爾始終只字不提康德該注釋所針對的對象(主要是萊布尼茨,順便帶上洛克),不知道到底是指誰和誰的“歧義”(Amphibol)(68)該詞孫周興譯作“模棱兩可”,字面上沒錯,但未能表達(dá)出“混淆知性和感性”的含義。,說明他根本沒有搞清康德的“歧義”的意思,他的不厭其煩甚至東拉西扯(連“西班牙語”都扯進(jìn)來)的說明,只能使這個詞變得更加神秘莫測。他所說的系詞“是”的“方位”和“定位網(wǎng)”則不論是與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正位論,還是康德的先驗的正位論都沒有關(guān)系。至于他引進(jìn)來作為主導(dǎo)線索的“可能是”和“現(xiàn)實是”的“模態(tài)”范疇,在康德對這些反思概念的分析中也完全看不出起了什么樣的主導(dǎo)作用。例如,他所提到的康德的第四個反思概念“質(zhì)料與形式”,雖然它們是“其他一切反思的基礎(chǔ)”,但我們很難斷定其中何者是可能性、何者是現(xiàn)實性。我們可以把質(zhì)料看作可能性,而形式則是使它實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實性(如唯實論和理性派認(rèn)為的);也可以把形式看作可能性,而質(zhì)料則是用來填充形式使之成為現(xiàn)實的(如唯名論和經(jīng)驗派認(rèn)為的),康德則是用先驗自我意識及其范疇形式能動把握感性質(zhì)料的過程統(tǒng)一了雙方,使它們無法分離。所以,我們不必把這些反思概念捆綁在可能性和現(xiàn)實性這對范疇身上,倒不如把它們視為某一類特殊的范疇,如黑格爾說的,康德自己認(rèn)識到他的十二范疇“是怎樣的不完全”,“所以他才對先驗邏輯或知性學(xué)說再添上一個關(guān)于反思概念的研討作為附錄”(69)[德]黑格爾:《邏輯學(xué)》下卷,楊一之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1年,第250頁。。換言之,所有這些概念其實都是范疇,它們無一例外地被納入黑格爾《邏輯學(xué)》的范疇體系之中。

這是因為康德在“存在與思想”這一“主導(dǎo)名稱”中,用“肯定”取代了“存在”,用“反思之反思”取代了“思想”,從而使這一主導(dǎo)名稱變成“系詞與我思”。比起巴門尼德的“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命題,康德的進(jìn)步在于“作為肯定的存在是由對知性的經(jīng)驗性運用來規(guī)定的。主導(dǎo)名稱中的‘與’指的就是這種關(guān)系,在康德看來這種關(guān)系在思想中、也就是在人類主體的一個行動中有其立足點”(75)同上,第557頁,譯文有改動。。巴門尼德的“思想”只是“反思”的思想,只建立起客觀性;康德的“思想”則是對反思的反思,它建立起主體性。“作為反思的思想指的是視界(Horizont),而作為反思之反思的思想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釋的方法(Organon)。在‘存在與思想’這個主導(dǎo)名稱中,思想在我們已經(jīng)指明的根本意義上是模棱兩可的,而且這一點貫穿著西方思想的整個歷史。”(76)同上,第558頁。但康德的不足之處在于,他停留于思想的這種模棱兩可之中,而不思更進(jìn)一層。于是海德格爾問:


這毫不顯眼的“是”中隱含著存在的一切值得思的東西。但其中最值得思的東西仍然是我們所考慮的:“存在”(Sein)是否能存在,“是”(ist)本身是否能存在,或者存在是否從來都不“是”,以及,盡管如此,“有存在”(Es gibt Sein)仍然是真的。(78)同上,第559頁,譯文有改動。
這簡直是陷入了魔咒。我們可以從存在者追溯到后面的存在,從系詞的存在(“是”)追溯到名詞(或動詞)的存在,又從名詞的存在追溯到es gibt(“有”);但“‘有’(Es gibt)中的贈予(Gabe)是從何而來的?從何者開始?以何種給出(Geben)方式?”(79)同上,第559—560頁。試想,即使回答了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后追問啊!這樣的追溯又何時是個頭呢?難道不需要一個上帝出來終止這種無窮追問嗎?這里的那個Es除了指上帝,還能指誰呢?《使徒行傳》(17:25)說神“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gibt,見德譯本)萬人”,說的不就是這回事嗎?我們不能再追問上帝是從何而來的,甚至不能說上帝“存在”,因為上帝就是存在本身,我們不能再用存在來描述祂。所以,“存在(Sein)不能存在(sein)。倘若存在存在,則它就不再是存在,而是一個存在者了”(80)參見[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第560頁。,道理就在這里。巴門尼德還沒有上帝概念,所以他能夠說“存在就是存在”;但其中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存在就是那“給出在場狀態(tài)者”。所以它看起來似乎是同義反復(fù),其實“于自身中包含著未曾被道說的東西,未曾被思的東西,未曾被追問的東西。‘在場在場著’”(81)同上,第560頁。。一個是名詞,一個是動詞;并非是動詞“假裝”成了名詞,而是你只有從名詞才能追溯后面的動詞,才能追問那沒有被道說出來的行動者,才能追問是“誰”使得存在者存在、讓在場者在場。而這一“使”,這一“讓”,中間有個時間差。所以“何謂存在”的問題最終就與時間的本質(zhì)聯(lián)系起來,“存在與思想”的主導(dǎo)名稱就變成“存在與時間”(82)同上,第561頁。。海德格爾的新招已經(jīng)用完了,他只好帶我們從這個最后的“路標(biāo)”又返回到他的克服形而上學(xué)之路的最初的“路標(biāo)”處。